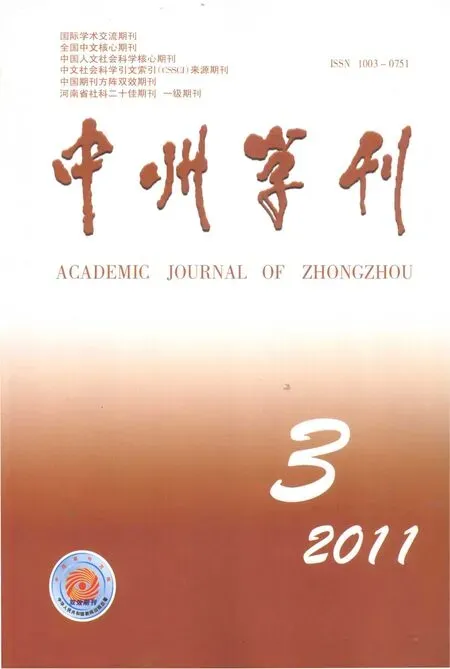20世紀(jì)初領(lǐng)海主權(quán)理論的傳播及清政府的認(rèn)識
劉利民
20世紀(jì)初領(lǐng)海主權(quán)理論的傳播及清政府的認(rèn)識
劉利民
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的真正勃發(fā)當(dāng)是在20世紀(jì)初年,當(dāng)時的留日學(xué)生是促進(jìn)這一過程的主要力量。他們大量翻譯和介紹了日本國際法學(xué)者的著作,同時還對領(lǐng)海理論進(jìn)行了一定研究。正是隨著新一輪國際法知識的傳輸,領(lǐng)海理論也隨之得到廣泛傳播。20世紀(jì)初年,清政府對領(lǐng)海問題有了進(jìn)一步的了解。在一些交涉事件中,清政府已經(jīng)能夠自覺地運(yùn)用這一理論來維護(hù)自己的權(quán)利,在最后幾年里接受了從日本傳來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理論,其認(rèn)識水平已經(jīng)走出了19世紀(jì)時的朦朧狀態(tài),甚至發(fā)展到了準(zhǔn)備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程度。
領(lǐng)海觀念;國際法;領(lǐng)海制度
19世紀(jì)中后期,隨著國際法的傳輸,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逐漸被中國人所熟悉。但是,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的真正勃發(fā)當(dāng)是在20世紀(jì)初年。本文擬對20世紀(jì)初期領(lǐng)海理論的傳播和清政府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的發(fā)展進(jìn)行探討。
一、留日學(xué)生與20世紀(jì)初領(lǐng)海理論的傳播
20世紀(jì)初年,由于受民族危機(jī)的刺激,加之清政府推行新政,政法知識的學(xué)習(xí)與研究成為當(dāng)時的熱門,其中就包括國際法知識。就國際法的傳播情況來看,留日學(xué)生是促進(jìn)這一過程的主要力量。他們大量翻譯和介紹了日本國際法學(xué)者的著作,同時還對其進(jìn)行了一定研究。正是隨著新一輪國際法知識的傳輸,領(lǐng)海理論也隨之得到廣泛傳播。與19世紀(jì)相比,這一輪傳播具有明顯不同的特點(diǎn):
首先,第一次采用了準(zhǔn)確的國際法專業(yè)術(shù)語,把領(lǐng)海概念第一次介紹給中國人。20世紀(jì)以前,外國傳教士翻譯國際法時還沒有找到準(zhǔn)確表達(dá)領(lǐng)海概念的中文詞語,中國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領(lǐng)海,只知道沿岸附近水域?qū)儆诒緡茌牎V劣谟檬裁磥肀磉_(dá)這一意思,一直也沒有找到適合的詞語。這種情況到20世紀(jì)初年才改變,留日學(xué)生從日本人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詞。此后,“領(lǐng)海”、“領(lǐng)海主權(quán)”、“海灣”、“公海”、“海里”、“中立”等一系列新名詞紛紛傳入,一直沿用至今。據(jù)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領(lǐng)海”一詞最遲在1902年就已經(jīng)傳入。該年9月16日和21日的《外交報》連續(xù)登載《紀(jì)各國會議領(lǐng)海事》。①這是筆者所見最早以“領(lǐng)海”一詞為標(biāo)題的文章,可能也是“領(lǐng)海”一詞出現(xiàn)在中國報刊的開始。該文還對“領(lǐng)海”一詞進(jìn)行了注解,“于海面立一定界限,由濱海之國管轄,謂之領(lǐng)海。”這即使不是最早的領(lǐng)海概念說明,也應(yīng)該是較早的定義。除領(lǐng)海一詞外,該文還使用了“領(lǐng)海界限”、“中立”、“海里”、“海灣”等新詞語。就詞語輸入來說,這些詞語的出現(xiàn)應(yīng)是較早的。它們的出現(xiàn)結(jié)束了中國人對所管轄水域模糊不清的狀況。從此,“內(nèi)洋”、“外洋”、“中國洋面”等一些模糊的概念成為了歷史。以準(zhǔn)確的國際法專業(yè)術(shù)語代替模糊的詞語,這是當(dāng)時留日學(xué)生對國際法翻譯事業(yè)作出的貢獻(xiàn)。它有利于促進(jìn)國際法的傳播,特別有利于中國人領(lǐng)海理論的理解與接受,也有利于在與列強(qiáng)的交涉中捍衛(wèi)本國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
其次,就傳播途徑來說,這一輪的國際法傳輸途徑更加廣泛。除著作翻譯外,報紙雜志也進(jìn)行了大量宣傳和介紹。
就著作翻譯來說,此次翻譯的版本大部分是日本學(xué)者的著作或者講義,翻譯的主體不再是外國傳教士,而是中國留學(xué)生。由于日本曾有過與中國相似的經(jīng)歷,而歐美國際法著作中的觀點(diǎn)對于東方世界是不公正的,因此日本學(xué)者對這些觀點(diǎn)進(jìn)行了批駁,這更符合中國的實(shí)際。因此,新一輪的國際法著作翻譯是對前一輪翻譯的反思。留學(xué)生的翻譯工作大概開始于1902年前后。1901年7月《譯書匯編》第7期已譯待刊書目中就列有《國際法論》,但具體情況不詳,是否出版也不得而知。1902年楊廷棟翻譯的《公法論綱》應(yīng)該算是現(xiàn)在可以找到的此類譯著中最早的代表作。此后,大量國際法著作被翻譯到中國。據(jù)研究,20世紀(jì)前十年,留日學(xué)生翻譯介紹的國際法著作大約有50種以上。②這些譯著采用新詞語翻譯,一直沿用至今。在這些著作中,領(lǐng)海理論當(dāng)然得到了更新。可以說,每一本國際法譯著都對領(lǐng)海理論進(jìn)行了與以前不同的介紹。隨著如此之多國際法譯著的傳播,中國人對于領(lǐng)海理論有了更新、更詳細(xì)的了解。
新式報紙雜志對領(lǐng)海理論的傳播也作出了貢獻(xiàn)。它們使這一輪的國際法知識傳播更加廣泛。接受國際法的主體不再單單是官員,更大程度上是在新式知識分子中間進(jìn)行,有利于國際法知識向大眾開放。這一特點(diǎn)在領(lǐng)海理論的傳播過程中尤為明顯。在19世紀(jì)中后期,領(lǐng)海理論的傳播只限于在少數(shù)官員中進(jìn)行,大部分人特別是普通知識分子對于這一理論根本沒有聽說過。但在20世紀(jì)初年,由于報紙雜志的涌現(xiàn)改變了這種局面,使普通知識分子得以接受外界新鮮的知識信息。領(lǐng)海理論成了普通知識分子經(jīng)常能夠接觸的東西。新式報紙雜志中對領(lǐng)海理論傳播作出較大貢獻(xiàn)的主要有《外交報》、《法政學(xué)報》、《廣益叢報》、《東方雜志》等,其中《外交報》是當(dāng)時熱衷于領(lǐng)海理論傳播的最重要報紙雜志之一。從1902年9月16日第21期開始,至1910年12月6日第296期止,該報翻譯、介紹、研究及報道有關(guān)領(lǐng)海問題的文章相當(dāng)多,既有理論的介紹,也有理論的具體適用;既有外國人文章的翻譯,也有中國人的論說。《外交報》還開辟了時事介紹欄目,其中許多涉及領(lǐng)海問題,如軍艦駐泊、漁業(yè)交涉、水道測量、航權(quán)交涉、海灣租借等。對于研究20世紀(jì)前十年領(lǐng)海理論的傳播情況和中國領(lǐng)海主權(quán)狀況來說,這些是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
最后,領(lǐng)海理論在國際法傳播過程中的地位明顯提高。在第一輪傳播過程中,領(lǐng)海理論只是國際法知識中的小部分,并沒有單獨(dú)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容也較簡單。與之相比,這一輪國際法傳播更強(qiáng)調(diào)領(lǐng)海法的介紹。由于是中國人自己翻譯和傳播國際法,因此更注重現(xiàn)實(shí)服務(wù)功能,注重國際法與國內(nèi)實(shí)踐相結(jié)合,體現(xiàn)了實(shí)用的特點(diǎn)。這就決定了領(lǐng)海理論在國際法介紹過程中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此時中國的領(lǐng)海糾紛問題特多。從日俄戰(zhàn)爭所帶來的領(lǐng)海中立糾紛,到外艦任意游弋內(nèi)河內(nèi)湖,再到澳門水界糾紛,還有沿海漁業(yè)問題等,這些都需要中國人自己來思考解答。現(xiàn)實(shí)的需要使人們把目光轉(zhuǎn)向了領(lǐng)海理論。除了國際法譯著介紹更加詳細(xì)、更加深入的領(lǐng)海理論外,報紙雜志上也出現(xiàn)了大量專門介紹領(lǐng)海理論的文章,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具體研究中國領(lǐng)海問題的文章。報紙雜志大量翻譯、介紹與研究領(lǐng)海問題,說明領(lǐng)海理論已經(jīng)受到了中國人的關(guān)注。相對于國際法的其他知識來說,領(lǐng)海法受關(guān)注的程度更高。總體看來,這次國際法宣傳重點(diǎn)突出了領(lǐng)海理論部分的介紹。
此外,就領(lǐng)海理論本身而言,這一次的介紹更深入具體。19世紀(jì)的國際法介紹是為翻譯而翻譯,因此沒有重點(diǎn)與非重點(diǎn)之分。領(lǐng)海法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部分,而且很簡單。但是,20世紀(jì)初年的國際法翻譯與宣傳介紹情況大不相同。國際法著作中對領(lǐng)海法方面的介紹可能還不能明顯體現(xiàn)這種差別。但由于報紙雜志的參與,對領(lǐng)海理論的介紹很明顯出現(xiàn)了深入具體的特點(diǎn)。領(lǐng)海理論的介紹已有相當(dāng)?shù)纳疃龋劝I(lǐng)海的概念介紹及其界限劃分,也包括領(lǐng)海管轄權(quán)的具體內(nèi)容說明;既有領(lǐng)海理論的歷史溯源,也有領(lǐng)海理論發(fā)展的現(xiàn)狀介紹;既有理論本身的闡述,也有相關(guān)實(shí)例的說明;既論述了領(lǐng)海問題,也述及了內(nèi)水問題。可以說,此次領(lǐng)海理論翻譯和介紹是較全面而深入的,對中國人準(zhǔn)確而系統(tǒng)地掌握領(lǐng)海理論起了重要作用。就當(dāng)時報紙雜志所介紹的領(lǐng)海理論內(nèi)容來說,主要涉及:領(lǐng)海概念及其歷史溯源、外艦、商船管轄、海灣、漁業(yè)權(quán)等問題。此外,還有文章涉及海島占領(lǐng)、內(nèi)湖被侵、緝私權(quán)利、沿岸貿(mào)易等方面。總之,此次宣傳已經(jīng)深入到了領(lǐng)海主權(quán)的各方面,某些方面還比較詳細(xì)。
留日學(xué)生所進(jìn)行的國際法傳播事業(yè)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就領(lǐng)海理論而言,這一點(diǎn)尤其明顯。此次宣傳,不僅使新式知識分子掌握了較系統(tǒng)的領(lǐng)海理論,而且使清政府原有的有限領(lǐng)海主權(quán)意識得以發(fā)展。清政府真正開始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擺脫了原來的朦朧狀態(tài),在對外交涉中多次運(yùn)用這種理論捍衛(wèi)領(lǐng)海主權(quán),甚至因此而萌發(fā)了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想法。
二、20世紀(jì)初清政府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的發(fā)展
20世紀(jì)初年,清政府對領(lǐng)海問題有了進(jìn)一步的了解。在一些交涉中,能夠較自覺地運(yùn)用該理論維護(hù)自己的權(quán)利。日俄戰(zhàn)爭中的領(lǐng)海中立權(quán)交涉、澳門水界交涉、中日二辰丸案交涉、渤海灣漁業(yè)交涉以及東沙島交涉都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可以認(rèn)為,此時清政府具備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大大超過了19世紀(jì)中后期的水平。
第一,頒布了有關(guān)領(lǐng)海中立權(quán)的法律條規(guī)。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后,清政府頒布了《局外中立條規(guī)》。③條規(guī)在維護(hù)中國領(lǐng)海有限中立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一定作用。就國際法的實(shí)施來說,中立條規(guī)的頒布也有其意義。它是清政府頒布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有關(guān)領(lǐng)海主權(quán)問題的法律。它當(dāng)然是清政府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意識上升到國家法律高度的反映,表明清政府具有了比以前更高層次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這一條規(guī)對當(dāng)時留學(xué)生們宣傳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理論也有一定的反映,其中明顯的是采用了24小時制度。當(dāng)然,它所反映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如沒有采用當(dāng)時已經(jīng)傳入的“領(lǐng)海”概念,只是使用“中國海口”或“中國管轄江海屬境”字樣,至于海口的寬度更沒有說明。
第二,明確采用了領(lǐng)海的說法。《東方雜志》第一卷第九號刊登了張謇咨呈兩江總督議創(chuàng)南洋漁業(yè)公司的呈文,提到領(lǐng)海界限問題:“各國領(lǐng)海界大約以近海遠(yuǎn)洋為分別,近海為本國自有之權(quán),遠(yuǎn)洋為各國公共之地。”④因此,至少在1904年兩江總督就已經(jīng)知道了“領(lǐng)海”一詞。在中央機(jī)構(gòu)中,商部應(yīng)該是采用領(lǐng)海說法較早的部門。它可能在1904年接觸過該詞,因為張謇創(chuàng)辦漁業(yè)公司不可能不向其提出申請。當(dāng)然,筆者的資料只能證明商部是在1905年了解領(lǐng)海一詞的。是年3月,意大利邀請中國參加1906年米蘭漁業(yè)賽會。商部要求南北洋大臣查照辦理。周馥就此咨詢張謇,張謇在呈文中提到了“領(lǐng)海主權(quán)”一詞,指出:“七省漁業(yè)公司之名宜及此表明于世界是有二義:一則正領(lǐng)海主權(quán)之名。”按照其意見,中國正好利用此次漁業(yè)賽會向外界宣布自己固有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他說:“今趁此會場,得據(jù)英國海軍第三次海圖官局之圖表明漁界,即所以表明領(lǐng)海主權(quán)。說非己出,事屬有因,在人可視為尋常,在我可分明主客。”除答復(fù)周馥咨詢外,張謇還專門向商部遞送了內(nèi)容大致相同的呈文。商部認(rèn)為“張修撰所陳一切不為無見”。可見,商部已經(jīng)能夠理解領(lǐng)海及領(lǐng)海主權(quán)的含義了。張謇的報告還被轉(zhuǎn)發(fā)給各省督撫,因此至少在1905年該詞已經(jīng)在官員中傳開。⑤此后,特別是1908年后,該詞在官方文書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
第三,在維護(hù)海權(quán)的過程中運(yùn)用領(lǐng)海法進(jìn)行交涉。二辰丸交涉案就反映了當(dāng)時官員的領(lǐng)海觀念狀態(tài)。1908年2月,日船二辰丸號偷運(yùn)軍火,在路環(huán)島附近海面卸貨,被中國海關(guān)查獲。船主承認(rèn)了犯罪事實(shí),但日本無理取鬧,反以查獲地點(diǎn)不在中國領(lǐng)海范圍為詞提出抗議。葡萄牙也趁機(jī)渾水摸魚,聲稱該案發(fā)生地為葡屬領(lǐng)海,中國“侵犯”了其領(lǐng)海主權(quán)。兩廣總督張人駿對此多次予以反駁,指出:當(dāng)時向船主“指經(jīng)緯度證解,系中國領(lǐng)海,該船主無詞。”“是巡弁關(guān)員等所測之經(jīng)緯度數(shù),已為該船主承認(rèn)無疑。”⑥按照國際法,當(dāng)時公認(rèn)的領(lǐng)海寬度多為三海里,惠頓指出“離岸十里之遙,依常例亦歸其管轄也。”⑦日本明白,若不能證明過路灣一帶為葡所有,則中國有權(quán)在這一帶領(lǐng)海內(nèi)行使管轄權(quán)。但如果日本能證明二辰丸停泊地點(diǎn)在離過路環(huán)島海岸三海里之外,則日本亦能理直氣壯地宣稱中國無權(quán)管轄。按照日本“所測”經(jīng)緯度計算,自然就擺脫了中國領(lǐng)海范圍內(nèi)的管轄。但是,按照中國所測經(jīng)緯度計算,二辰丸停泊地在中國領(lǐng)海內(nèi)⑧,而中國的測算是準(zhǔn)確的,已被船主承認(rèn)。當(dāng)中國外務(wù)部向日本指駁其經(jīng)緯度錯誤后,日本只好承認(rèn)是在“過路灣東二邁余(相當(dāng)于二海里)的地方停泊”。此后,日本又提出路環(huán)島附近水面“屬中屬葡”未定論。葡萄牙也稱:“系葡國的領(lǐng)海,距中國最近之地有三邁半有余之遠(yuǎn),有礙本國屬地,無羈商務(wù)之權(quán)。”⑨對此,張人駿駁斥道:“喀啰灣即過路灣之轉(zhuǎn)音,本系中國土地”,葡萄牙對過路灣的侵占是非法的,“中國迄未認(rèn)為葡屬”,且葡萄牙當(dāng)局僅占據(jù)“過路灣西角一隅”,而日船“系在過路灣迄東扣住,據(jù)海關(guān)洋圖距葡迄西之地相隔太遠(yuǎn),其為中國領(lǐng)海無疑”⑩。根據(jù)粵督意見,外務(wù)部在致日本照會中指出:此案“與葡界并無牽涉”,而且該船停泊處是否中國領(lǐng)海“不能由日本武斷”。日本只好稱“其是否屬于貴國領(lǐng)海,殊非我方交涉目的”,甚至表示“與該領(lǐng)海問題并無關(guān)系”?。從該案來看,中方官員能較準(zhǔn)確地運(yùn)用領(lǐng)海法進(jìn)行交涉,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列強(qiáng)承認(rèn)中國的領(lǐng)海。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時中方官員似乎承認(rèn)了三海里領(lǐng)海范圍學(xué)說,只不過出自地方官之口,在以后的交涉事件中再也沒有過類似的表示,中央政府也沒有正式宣布領(lǐng)海界限。因此只能說三海里界限說影響了當(dāng)時部分官員,并不能推斷清政府承認(rèn)三海里規(guī)則。
第四,為建立領(lǐng)海制度進(jìn)行準(zhǔn)備。清政府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領(lǐng)海制度,但在其最后幾年里確實(shí)有過這種打算,并為此作過一定努力。清政府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想法主要源于列強(qiáng)的刺激。1908年春,英國駐江寧領(lǐng)事就海洋管轄方面的事情向兩江總督端方提出疑問,要求中方答復(fù),但中方無法答復(fù)。?這使中方感到尷尬,因為中國沒有頒布專門法律,端方只好含糊作答。端方為此事專門詢問過外務(wù)部及海軍提督薩鎮(zhèn)冰。薩鎮(zhèn)冰的回答是“嗣后凡遇此等問題,擬照英國海律辦理。”外務(wù)部則遲遲未見答復(fù)。?這件事情對清政府來說應(yīng)是個刺激因素。
更大的刺激來自于三件交涉案:一是二辰丸案,二是渤海灣漁業(yè)糾紛案,三是列強(qiáng)侵占中國島嶼案。二辰丸案對于清政府領(lǐng)海觀念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在該案交涉中,盡管中方官員堅持案發(fā)地點(diǎn)屬于中國領(lǐng)海,但畢竟沒有宣布過領(lǐng)海界限,這就使其交涉缺乏法律依據(jù)。因此,他們認(rèn)識到問題的嚴(yán)重性。加上該案交涉失敗引起了輿論的不滿,民眾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中國沒有宣布領(lǐng)海界限,要求迅速制定海圖,劃定領(lǐng)海界線:“使政府早日勘定界線,明定領(lǐng)海之權(quán)限,則日政府亦何敢謂非我國領(lǐng)海,而葡國亦不敢妄指為己國領(lǐng)海。”外務(wù)部也認(rèn)識到領(lǐng)海界限的重要性。交涉案結(jié)束后,外務(wù)部當(dāng)即照會各國駐華公使,宣布:“粵海三洲、七洲、九洲各洋均在中國領(lǐng)海權(quán)力范圍內(nèi),可以實(shí)施中國之海界禁例,不得指為公海。”同時外務(wù)部要求:“嗣后各國兵商輪船在該海線內(nèi),如有私運(yùn)軍火違犯禁例之事,中國當(dāng)實(shí)行干涉,為正當(dāng)之處置。”除了籠統(tǒng)地宣布廣東海界之外,外務(wù)部還決定將對沿海七省的海界進(jìn)行測量繪圖,“作為中國領(lǐng)海定線,即向各國宣布,一律公認(rèn)。”?二辰丸案對清政府領(lǐng)海觀念的發(fā)展具有直接的刺激作用,甚至使其產(chǎn)生了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想法。此次宣布的領(lǐng)海界限盡管是局部的甚至是籠統(tǒng)的,但畢竟是中國最早宣布的領(lǐng)海界限,也是中國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初步嘗試。二辰丸案議結(jié)不久,中日之間又為東沙島問題發(fā)生了糾紛,“且自東沙島交涉議結(jié)后,又有日人寄棲渤海東南面之劉公島,德人測繪東海道要塞之田橫島……”?對于列強(qiáng)窺伺沿海島嶼的問題,清政府不得不考慮對策,這加深了其對領(lǐng)海重要性的看法。清政府決定對沿海七省島嶼進(jìn)行測繪,“嗣后我國勘定各島,無論何國均不準(zhǔn)以無名荒島任意侵占……并咨沿海各省督撫,隨時飭派軍艦巡視,以免損失海權(quán)。”?可見,島嶼糾紛也是引起清政府關(guān)注領(lǐng)海問題的重要因素。渤海灣漁業(yè)交涉同樣不可忽視。自接租旅大之后,日本又窺伺渤海灣漁業(yè)。中方多次抗議,但日方“藐視我國行政官員不知國際法規(guī)定海灣之先例,遂強(qiáng)詞巧辯”,根據(jù)所謂“三海里原則”聲稱日船是在公海之上捕漁,意即不承認(rèn)該灣屬于中國領(lǐng)灣。?該灣一直屬于中國管轄,歷史上也沒有遇到過任何挑戰(zhàn)。現(xiàn)在日本人橫插一杠,使清政府遭受當(dāng)頭棒喝。清政府決定采取措施:“外部以渤海灣交涉迄未議結(jié),此系我國領(lǐng)海,豈可任人侵略,亟應(yīng)派委精于測繪人員實(shí)地勘測。凡中國領(lǐng)海權(quán)內(nèi),所有華僑殖民各島及大小荒島均須繪具圖說,標(biāo)立石址,咨部核定,以便照會各使,嗣后凡中國勘定各島不得任意侵占,并咨沿海各該督撫隨時飭派軍艦巡視情形,俾免損失海權(quán),以維護(hù)邦交而資保護(hù)。”?可見,渤海灣問題也是促使清政府準(zhǔn)備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重要因素。
清政府亦為建立領(lǐng)海制度作了一些準(zhǔn)備。除宣布廣東海界外,還著手討論全國領(lǐng)海界線問題。關(guān)于領(lǐng)海界限,張謇曾于1904年向兩江總督提及過,但似乎沒有引起注意。二辰丸案之后,清政府才正式注意海界問題。當(dāng)時北洋大臣專門作過批示,反映了清政府的觀念:
查海圖為國家領(lǐng)海主權(quán)所系,而界線尤關(guān)緊要。遇海戰(zhàn)時,凡中立國應(yīng)守之權(quán)利、責(zé)任,全視界線以為衡。至于沿海島嶼形式區(qū)域,尤須有確切地名而后一覽了然,于扼要設(shè)防方可以籌布置。漁業(yè),特其一端耳!然兩國交界之地,設(shè)無正確之海圖界線劃分域限,往往因漁業(yè)而啟爭端,所關(guān)亦即匪細(xì)。但必先有國防軍用之海圖,而后漁業(yè)海圖有所從出。中國海疆遼闊,島嶼港汊紛羅錯出,因向無精確海圖,不獨(dú)于形勢地理上無可考見,即所在地名亦茫于所向。間有其地為外人所垂涎,并且外人所指索,而中國曾不知其地究歸何屬者,此其為害,殆不可言。現(xiàn)當(dāng)籌議擴(kuò)張海軍之際,而中國海軍所用海圖,猶藉英國海軍所繪之圖以為底本,殊不足以慎重。即將地名訪詢確實(shí),詳為更正。而島嶼有無遺落,汊港有無混淆,非自行實(shí)測勘量,繪圖列說,將何以資校核而訂謬訛。所稟請設(shè)海圖局測繪研究編撰圖志,洵為目前當(dāng)務(wù)之急。?
從這一批文可以看出,清政府已經(jīng)認(rèn)識到領(lǐng)海界線的重要性,只不過限于條件一時無法進(jìn)行劃分,只能首先對島嶼進(jìn)行測量繪圖。至于海界劃分,1909年才被提到中央層面討論,《海軍》雜志記載:
中國應(yīng)繪完全領(lǐng)海全圖,前由江督倡議,擬行聯(lián)合劃一辦法,已由陸軍部核準(zhǔn)定議,并咨商各省籌辦一切。現(xiàn)部中提議,領(lǐng)海界線關(guān)系國家主權(quán),現(xiàn)值擴(kuò)張海軍,振興漁業(yè),應(yīng)將界線劃清,繪列精確詳圖,宣布中外,共相遵守。惟查中國沿邊領(lǐng)海,由奉直起,計中經(jīng)魯、蘇、浙、閩以至極點(diǎn)之廣東,綿長三千余里,欲行詳繪全圖,自應(yīng)從測量、研究、編撰入手。惟與其由各省分辦,散漫遲延,而不能統(tǒng)一,仍不若在適中地方專設(shè)局所,由一處承任,分途測繪辦理。?這是筆者能找到的有關(guān)清政府正式會議全國領(lǐng)海界限劃分方面的最早記載。這說明當(dāng)時清政府有了主動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考慮,表明其領(lǐng)海主權(quán)觀念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相當(dāng)水平。
清政府還啟動了海洋立法工作。“又自日本二辰丸案議結(jié),而政府以我國向無捕獲裁判之法律,遂至外交失敗。于是外務(wù)部、憲政編查館、稅務(wù)處會同核議,查照各國成法,簽訂內(nèi)地及領(lǐng)海以內(nèi)捕獲裁判專律,擬俟脫稿,先牒各使,俟其認(rèn)可,即當(dāng)奏請宣布辦法通行。”?由此可見,清政府受二辰丸案刺激開始了捕獲法的立法工作,此外其他海洋立法也在考慮中。?
從上述情況來看,在留日學(xué)生的影響下,清政府在最后幾年里接受了從日本傳來的領(lǐng)海主權(quán)理論,其認(rèn)識水平已經(jīng)走出了19世紀(jì)時的朦朧狀態(tài),甚至發(fā)展到了準(zhǔn)備建立領(lǐng)海制度的程度。盡管一直沒有宣布領(lǐng)海寬度,領(lǐng)海制度建設(shè)也處于準(zhǔn)備階段,劃界、立法等工作都未完成,但考慮到這是中國第一次進(jìn)行這方面的努力和清政府所剩時日無多等因素,沒有必要過多苛求前人。就領(lǐng)海觀念和制度建設(shè)來說,此時清政府的表現(xiàn)還是比較積極的。
注釋
①《紀(jì)各國會議領(lǐng)海事》,《外交報》第21、22期,1902年9月16日、21日。②田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濟(jì)南出版社,2001年,第141頁。③遼寧省檔案館:《日俄戰(zhàn)爭檔案史料》,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0—112頁。④張謇:《商部頭等顧問官張殿撰謇咨呈兩江總督魏議創(chuàng)南洋漁業(yè)公司文》,《東方雜志》第1卷第9號,1904年11月2日。⑤《商部為義國漁業(yè)賽會咨各省督撫文》、《商部頭等顧問官翰林院修撰張為義國漁業(yè)賽會事咨呈兩江總督周文》,《外交報》第125期,1905年1月23日。⑥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210卷,(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1932年,第4頁。⑦惠頓著、丁韙良譯《萬國公法》,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3頁。⑧梁淑英:《中國領(lǐng)海制度》,《政法論壇》1994年第3期。⑨?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212卷,(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1932年,第2—4、14頁。⑩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211卷,(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1932年,第1 頁。?《交涉錄要》,《外交報》第206期,1908年4月25 日。?《答復(fù)英領(lǐng)事詢問關(guān)于海洋事》,《現(xiàn)世史》第1號,1908年6月23日。?《交涉錄要》,《外交報》第 217 期,1908 年 8 月 11 日。??《劃清海權(quán)之籌備》,《外交報》第276期,1910年5月23日。?《外務(wù)部測繪領(lǐng)海荒島之計劃》,《外交報》第240期,1909年5月4日。?邵羲:《論渤海灣漁業(yè)權(quán)》,《外交報》第283 期,1910年7 月31日。?《外務(wù)部測繪領(lǐng)海荒島》,《申報》1910 年 8 月 2 日。?甘厚慈輯《北洋公牘類纂續(xù)編》卷廿一,宣統(tǒng)二年刊本,第14頁。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86輯第860號,文海出版社影印,總第1602頁。?海軍編譯社:《詳商合辦七省領(lǐng)海全圖之法》,《海軍》第1號,1909年6月1日。?《訴訟交涉》,《外交報》第 210期,1908年6月3日。
K257.9
A
1003—0751(2011)03—0182—05
2010—12—25
劉利民,男,湖南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副教授,歷史學(xué)博士(長沙 410081)。
責(zé)任編輯:殳 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