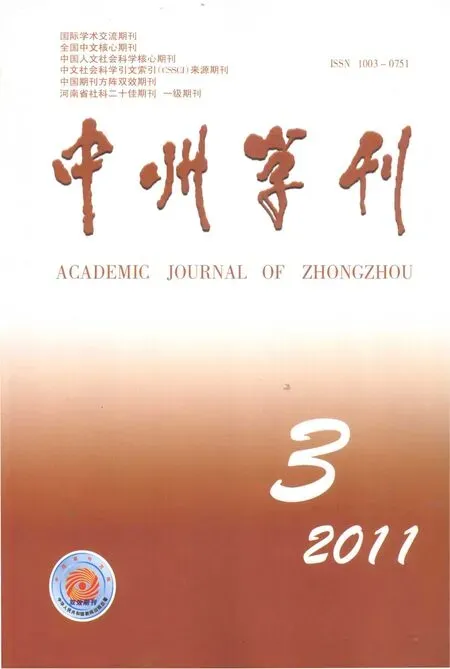制度視野中唐高宗時期詩歌發展之路向
王新榮
制度視野中唐高宗時期詩歌發展之路向
王新榮
與貞觀朝相比,唐高宗時期選舉制度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如科舉考試重文辭、輕德行等。這些變化與士族體系的解構和庶族士人群體的崛起相表里,大大激發了士子特別是廣大下層士子的進取欲望和功名心,從而對一代“浮躁淺露”士風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士風在政治境遇不同的文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概言之,在上層文人身上主要表現為重文輕德、以文自矜,在下層文人身上主要表現為露才揚己、憤激不平、自媒躁進。士風必然要影響到詩風,并對其時上層文人多重藝術形式的雕琢、下層文人多重言志抒情的詩歌路向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選舉制度;浮躁淺露;士風與詩風;詩歌路向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650—683)是唐詩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的詩歌是沿著兩個不同路向交錯發展演進的:以初唐四杰為代表的下層文人才高位下,仕進生涯中多漂流輾轉之艱辛,故其詩歌多以借他鄉山水以抒發心中不平之氣為主;以文館學士為代表的上層文人多生活在宮廷廟堂之內,其詩歌多借奉和應制以炫耀詩才,走的是鍛煉詩藝的路子。在唐詩發軔之際,前者賦予其以實質的內容,后者賦予其以精致的形式。兩條道路交錯發展,共同指向盛唐的詩歌高峰。進一步考察高宗詩壇后我們又發現,兩條詩歌發展路向的形成與其時文人命運的窮達密切相關,而文人命運的窮達又與其時選舉制度的某些重要變化緊相關連。事實上,某個時期的詩歌風尚若要持久而廣泛地產生影響,就必然要以某種制度的形式來保障。本文即旨在從制度的視角來探討這一時期的兩條詩歌發展路向成因及其詩學追求。
選舉制度的變化及其影響
貞觀朝選舉制度以士人德行學識為本,不以文詞為貴。太宗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行,數年之后惡跡始張,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矣”;“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①。永徽六年,武則天奪宮成功并開始實際地參預朝政,“帝自顯慶后,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后決之”②。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她開始著手對貞觀政治體制進行解構,科舉和選官制度亦相應地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選舉制度的變化,首先表現為科舉考試重文辭,輕德行。從本體意義上講,文辭和德行并非完全對立的兩個概念。唐初科舉考試中之所以有重德行與文辭之分,根源還在于選舉方面士、庶觀念的差異。“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③士族子弟重經學,以“通經義、勵名行為仕宦之途徑,而致身通顯也”,故其強調德行,強調通經致用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而唐高宗時期,士族觀念從制度層面上已開始漸被解構,其突出的標志就是顯慶《姓氏錄》的修訂。庶族力量開始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庶族力量以新進進士為主,而其時的進士科考試以文辭為清流仕進之正途,故其時選舉觀念在文辭、德行上的分野實質上是士、庶政治勢力斗爭之外顯。
進士科加試雜文是科舉重文辭的突出表征。進士科加試雜文并制度化始于永隆二年劉思立知貢舉時。其實,在永隆二年以前,進士科加試雜文即偶有之。如顯慶四年,進士試即有《關內父老迎駕表》、《貢士箴》之題目。唐代科舉之法又分常科和制科,制科對文辭的重視尤勝常科。高宗所開制科幾乎每科都有關于文學的科目,如乾封二年有“辭贍文華科”等。皇帝求賢的詔書中也經常有對于文學之材的要求,如顯慶五年詔文武百官薦舉“藻思清華,辭鋒秀逸者”④等。新進進士多以文辭取勝自然就形成一股潮流。另外,武后“頗好文史”,為了政治需要,“其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獎進”⑤,于是遂促成“國家以吏部為取士之門,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于才藝,不矜于德行”⑥的局面。制舉方面,高宗在下詔征召“德行光俗,邦邑崇仰者”的同時,又征召“婆娑鄉曲,負才傲俗,為譏議所斥,陷于跅馳之流者”⑦,亦足見其時士人品行已不足為重。
變化之二是科舉及第和選官人數的大幅度增加。據徐松《登科記考》,貞觀朝23年間共取進士205人,年均9人;而高宗在位33年間取468人。明經科考試及第人數更是十倍于進士,“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⑧。關于制舉,《通典·選舉》卷三云:“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高宗朝開制科非常頻繁,應制人數和門類大大增加,開有“洞曉章程科”、“學綜古今科”等⑨,可謂轟轟烈烈,風頭直壓常科。
進士及第人數的增加自然會導致選官數量的增加。而其時士人入仕還可以通過朝廷擴大流外官的銓選數量等。唐朝每年所放流外出身有千余人甚至二千人,且這些流外出身者每年入流內敘品的數量不遜于科舉入仕。顯慶三年,黃門侍郎劉祥道上奏:“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之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⑩另外,高宗朝的選官范圍也逐漸全國化。上元二年,朝廷開“南選”之途,把選官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嶺南、黔中等蠻荒之地,即為顯例。
實際上,選舉制度變化的最重要意義是它極大地激發起廣大下層士子久被壓抑的勃勃欲望和進取心,從而對唐代士人政治理想的轉型產生了極強的催化作用。
首先,選舉制度的新變使廣大下層知識分子看到了在門閥士族統治時代不可能看到的致身顯貴之機會,使得他們普遍懷有一種朝為寒士,暮登朝堂的急功近利的躁進心態。當其久滯下位時,他們一方面自媒求進,炫耀文采,四處干謁,一方面又不掩飾自己心中懷才不遇的哀怨與憤懣。由此形成一種逞才放浪之風習,以浮華相競勝,遂形成一代“浮躁淺露”之士風。其次,這種變化還在客觀上促進了唐代知識分子政治理想的轉型。傳統儒家思想原則上強調每一個士人都必須拋卻自己的功名利益而提倡“兼濟”和“窮且益堅”,但高宗時期的選舉制度大大激發了文人的個人欲望,使得他們建功立業的政治理想突破了封建名教的韁索。楊炯明言:“丈夫皆有志,會要立功勛”;李嶠高呼:“倚天圖報國,畫地取雄名”。這表明他們的政治理想已由“高遠的、無私的‘致君堯舜’和‘濟世安民’式”向“近期的、現實的個人功名、利祿式”的轉變?。
“浮躁淺露”的文人及其詩歌創作活動
據《舊唐書·王勃傳》載:“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王勃等四人,謂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勃等雖有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余得令終為幸。’后果如其言。”這則材料指出當時新興之文人階層存在一種“浮躁淺露”的風氣則是符合實際的。“浮躁淺露”的時代士風又因文人政治地位的變化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從而影響到他們詩歌創作活動重心的差異。
對于上層文人而言,“浮躁淺露”表現為一方面以文自矜、目空一切而實乏吏能,一方面又操守不謹、諂媚阿諛。許敬宗、李義府這兩位老資格的弘文館學士,其操守卑污已書入史書,廣為人知,固無須贅言。而薛元超為高宗朝“朝右文宗”,銜匡主之遺命,負薦士之重荷,高宗倚之為心臀,士子奉之若北斗,然亦因交構李義府而遭貶,卒成其人生玷玉之瑕,令后人于唏噓之余,不能不慨嘆其時士風之澆薄。
這類文人的文學創作活動多限于宮廷應制和館閣唱和,因為只有這樣的創作活動才能給他們提供媚上和逞才的機會。《全唐詩》收有高宗李治的《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劉一之、胡元范、郭正一、任希古、元萬頃、裴守真等人均應制作《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這是比較大的一次唱和活動。這些唱和詩多詠帝王家事,詞采還是一樣的華麗,但內容和格調上卻是越發的柔靡,這又恰是文臣“浮躁淺露”的一個絕好注腳。
沉淪下僚、羈縻幕府,甚至流落民間的下層文人的數量要遠比上層文館學士多。除了眾所周知的“初唐四杰”外,李嶠、宋之問、杜審言、薛華、王公方等大量今天已經不太為我們所知的下層文人群體亦因才高而自負。他們一方面在詩中表現自己的踔厲風發、傲視王公,另一方面在行為上卻又不得不時時委屈自己而自媒求進。他們因仕進坎坷而大量作詩,高呼要嘯傲煙霞,卻又不甘自我埋沒,時時因干謁或轉任而飄零沉浮于滾滾紅塵。他們的浮躁淺露表現為愈久滯下僚愈躁進,愈壓抑愈狷介刻薄,終生在個人功名的追求與失落中痛苦地掙扎。
王勃于麟德年間作《上劉右相書》,大言自己:“未嘗降身摧氣,逡巡與列相之門;竊譽干時,匍匐于群公之室。所以托慷慨于君侯者,有氣存于心耳!實以四海兄弟,齊遠契于蕭韓;千載風云,托神知于管鮑。不然,則荷裳桂楫,拂衣于東海之東;菌閣松盈,高枕于北山之北。復區區屑屑,踐名利之門哉!”但現實生活中的他,卻甘心在王府中陪貴介公子們斗雞走狗。這類文人的詩歌創作活動多集中于干謁和祖餞。在那個時代,下層文人、新進進士、流外入流者若要順利釋褐、選調,離不開高級官員的提攜,這就使得其時干謁之風甚熾。高宗時期以文干謁的資料現存較多,《全唐文》中“四杰”及同時文人中有許多“上某某書”式的文章可證。王勃《上從舅侍郎啟》中記曾上《憲臺詩十首》,《再上皇甫常伯啟》記上《乾元殿頌》一首。與干謁詩相比,祖餞贈答詩數量和質量都要高得多。如盧照鄰、王勃、楊炯都參加過大量的迎來送往的詩酒活動,創作了大量送別詩,其詩也大多真情婉轉、凄惻感人。
兩種詩歌路向的斗爭與發展
人生際遇和士林風氣會對文人的創作活動和創作心態產生重要影響,而不同的創作心態和客觀環境又必然會導致不同的詩學追求。綜觀高宗時期的詩壇格局,其基本特征就是兩類不同命運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兩種詩歌路向的斗爭與發展:龍朔新變與對龍朔新變之批判。
高宗時期,以弘文館學士為代表的上層文人的主要創作活動是對貞觀朝文館體制和宮廷文學活動的繼承和延續,高宗朝文人以文自矜,游戲于聲律偶對而回避尖銳復雜的現實斗爭,使得詩歌創作在重藝術的路子上變本加厲。龍朔變體即應運而生。
楊炯《王勃集序》指出:“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后世學者多以“龍朔變體”概括這一時期的詩風,又因上官儀“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地位既高,文名亦盛,“上官體”也就成了龍朔新變詩體的代表。許敬宗、李義府在“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方面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薛元超,其奉和詩也是“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而其拔擢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徹、孟利貞等入弘文館,對于龍朔變體的推波助瀾才真正使得這一重藝術的詩歌新風得以成為時代潮流,且能夠持續發展。
上層文人對于聲律、對偶等詩藝的重視還表現在詩格和類書的編撰上。上官儀于高宗朝初年曾著《筆札華梁》一書,其主要內容是探討詩歌的對偶和聲律藝術的。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一部詩格著作是元兢的《詩髓腦》。但是元氏比上官儀更明確地提出了四聲二元化的原則,對于律詩篇制定型有著奠基作用。高宗朝所編撰類書主要有《文館詞林》、《瑤山玉彩》、《芳林要覽》等。這些動輒千卷的“詩歌樣本”,為宮廷制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貞觀朝類書編撰的主要目的在于文學普及,而高宗乃至稍后的武后朝類書的編撰目的,則更多地是從鍛煉詩藝的角度出發了。
駱賓王倡言“非敢希聲刻鵠,竊譽雕蟲”,“體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這一時期的下層文人已沒有了貞觀文人那樣雍容風雅的情懷以詠歌王政。澗底寒松、深谷青苔、江邊孤鳧是這些人真實生存狀態的寫照,他們心中都充溢著一股悲憤不平之氣。他們要借詩以抒發這股不平之氣,這就導致他們的詩歌創作向小雅中的“怨刺”精神靠攏。王勃稱自己有“耿介不平之氣”,楊炯“心中自不平”,盧照鄰明言“仆本多悲淚,沾裳不待猿”。這些人之所以心中多悲憤不平之氣,是因為他們“志遠而心屈”、“才高而位下”?,“有其志,無其時”,是因為他們身處窮途,心中“事有切而不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遣”?。所以在他們看來,詩歌的功能就在于發抒心中郁怏不平之情思,應該借江山以“宣其氣”,借琴酒以“泄其情”?。正如李嶠明確指出的那樣:“人稟性情,是生哀樂,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所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顰之野,斯見不平之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人的詩歌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泣窮途于白首”、“嗟歧路于他鄉”?,是哭出來的,是嘆出來的。關于這一點,王勃的《別薛華》最具代表性:“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悲涼千里道,凄寒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來與往,俱是夢中人。”其情深言淺,悲歌當哭,的確是與龍朔新體大異其趣的。
注釋
①《新唐書》卷45。②《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③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④徐松:《登科記考》。⑤《新唐書》卷45。⑥徐松:《登科記考》。⑦李治:《唐大詔令集》。⑧《通典·選舉》卷三。⑨徐松:《登科記考》。⑩劉祥道:《陳銓選六事疏》。?程遂營:《唐代文人政治理想的轉變》,《史學月刊》1994年6期。?《舊唐書·上官儀傳》。?駱賓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啟》。?王勃:《澗底寒松賦并序》。?王勃:《秋夜于綿州群官席別薛升華序》。?王勃:《春日孫學士宅宴序》。?李嶠:《楚望賦序》。?王勃:《越州永興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K242
A
1003—0751(2011)03—0205—03
2011—03—12
王新榮,女,鄭州師范學院副研究館員,圖書館館長(鄭州 450044)。
責任編輯: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