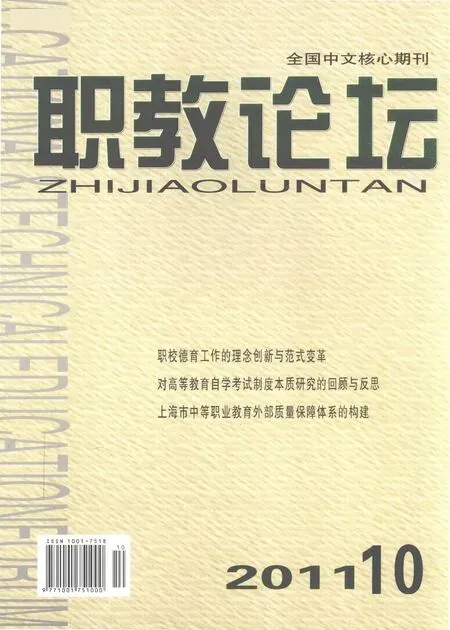職業教育中職業道德教育的困境與抉擇
□王 浪
職業教育中職業道德教育的困境與抉擇
□王 浪
當代職業道德教育在職業教育領域已經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和高度,但仍處于理念迷失、主體性缺失的非理性發展階段。從其內因來看,是在教學上過于封閉,表現為課程內容“皮之不存”;教學過程“去生活化”;教學方法“因循守舊”;評價方式片面單一。未來職業道德教育的發展應該堅持以人為本,倡導“源于生活,回歸生活”,“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材施教,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
職業道德教育;非理性;封閉式;人本化
職業道德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方面,歷來為世人所關注。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就主張“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唾棄“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即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樣,只僅僅有一才一藝就行。君子應以德行為首,具備多種才能與技藝。中華職教社發起人黃炎培也曾告誡青年“職業平等,無高下,無貴賤。茍有益于人群,皆是無上上品”[1],并將“敬業樂群”視為職業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
然而,職業道德教育成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卻是近十年來的事。2001年,教育部在《關于中等職業學校德育課程設置與教學安排的意見》中第一次提出“把職業道德作為一門課程來開設”;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又提出“把學生的職業道德、職業能力和就業率作為考核職業院校教育教學工作的重要指標”;2010年6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進一步提出“職業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會,著力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職業技能和就業創業能力”。雖然職業道德教育在職業教育領域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和高度,但發展形勢和現況卻不容樂觀。對當代職業道德教育進行深刻反思,對未來職業道德教育進行深入思考,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當代職業道德教育的現狀:非理性發展
近十年來,我國職業教育規模迅速擴大,辦學水平逐步提升,服務國計民生的能力不斷增強。職業道德教育作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內涵之一,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合格的技能型人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社會急劇轉型的大背景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思想肆意萌生,這些市場經濟的不良產物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觀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對職業院校的職業道德教育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突出表現為一種自我迷失的非理性發展狀態。
(一)職業道德教育理念迷失
我國教育家葉圣陶先生曾說過:“教育就是培養習慣。”引申而言,職業道德教育應該是要培養學生與之將要從事的特定職業活動相適宜的道德行為規范,包括職業理想、職業紀律、職業態度、職業良心、職業作風等等。然而,事與愿違的是,我國職業道德教育在理念上更多的是強調崇高的職業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忽視了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強調職業道德知識的理論基礎和系統性,忽視人的道德、德行所蘊含的動機、態度、情感諸多主體因素;強調職業道德課程學習和考試,忽視了職業道德在生活中的實踐和應用。職業道德教育理念的迷失,必將導致當代職業道德教育的“低效、甚至無用”。我國多項關于高職學生職業道德素質現狀的調查分析結果也表明,大多數職校生職業道德認知水平較高,而實踐能力較低;有一定的職業道德情感,但缺乏職業品德意志;對職業道德的地位與作用較認同,但對職業道德時效性信心不足;對公共的職業道德知識較為熟悉,而對本行業的具體職業道德規范了解較少。
(二)職業道德教育主體性缺失
人作為職業道德的習得者和踐行者,理應是職業道德教育的主體。然而,當代職業道德教育似乎無視這一基本準則,坐而論道,唯教材和書本至上,唯職業道德知識的灌輸為重。在對人的理解上,將人的本質、價值、需要和人與自然、社會、人際關系客觀化、知識化,將活生生的人抽象、隔離、凝固,導致人的道德精神與靈魂的失落;在指導思想上,將人類美好道德規范以社會宏大價值為中心的價值觀囫圇灌輸給受教育者,而無視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積極性和主觀價值選擇;在教學目標上,突出“精英”和“一元價值”的道德目標,而忽略普通人發展權力和道德發展階段與水平;在教學內容上,將空洞的、先驗的和脫離實際的道德知識作為課本主要素材,而不在乎受教育者生活和工作對職業道德的真實需要;在教學模式上,以教代學,將受教育者視為“道德的容器”,而不考慮受教育者本身對職業道德和職業生活意義的追尋。職業道德教育主體性的缺失,使職業道德教育與受教育者漸行漸遠。
二、當代職業道德教育的癥結:封閉式教學
當代職業道德教育的非理性發展,帶來的是職業道德教育的畸形成長:一方面,職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各種會議和文件中被多次宣告,政治色彩愈來愈濃;另一方面,職業道德教育卻僅僅只是作為一門必修課被老師和學生統一使用,現實價值每況愈下。如果說市場經濟的誘導是當代職業道德教育非理性發展的外因,那么,當代職業道德教育在教學上的“閉關鎖國”和“固步自封”則是其非理性發展的內因和癥結所在。
(一)職業道德教育課程內容“皮之不存”
盡管職業道德教育一再被強調,但在職業院校的課程和教學中,只有學科專業知識才能獲得應有的合法性,價值體系及職業道德觀念已經陷入微不足道的境地。[2]在很大的程度上,職業道德教育只是職業院校課程教學的附帶品和陪襯。一是職業道德教育專門課程較少、內容單一。雖然各職業院校的教學計劃中都列有“思想道德修養”或“職業道德與法律”等課程,但實際上這些課程中普通的思想教育內容較多,職業道德教育方面的內容較少;內容也以職業道德規則或基本規范為重點,而少有情境性的職業道德問題探討。二是專業課程中的技術倫理教育較少、屢被壓縮。專業課程中本來蘊含豐富的技術倫理,通過教學將其潤物無聲地進入課堂,這是專業課程教學的應有之義。但很多職業院校由于對技術倫理教育不夠重視,認為課堂上枯燥的說教對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能沒有實質性幫助,所以淡化甚至舍棄了這部分內容,從而弱化了職業道德教育的防范功能和準入功能。三是日益受到重視的就業指導課程中職業道德的篇幅偏少、內容偏淺。所有職業院校都開設就業指導課程,但就業指導課通常在學生就業前的短時間內開設,內容涉及就業形勢、職場禮儀等等,職業道德教育的內容篇幅很小,而且教師傳授的職業道德多數不涉及具體的職業道德問題,即使有,也相當淺顯和簡單。
(二)職業道德教育過程“去生活化”
作為職業院校德育的一項根本任務,職業道德教育在邊緣化的存在境遇下,習慣性地用一種科學知識的語言去解釋職業道德,并認為真實的、客觀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職業道德就存在于關于職業道德的知識體系中。一方面,學校職業道德教育將職業道德知識的傳授看成是職業道德教育的目標。“在教學中遠離這些道德知識符號得以產生、運行的歷史事實的生活。虛構一個虛幻的職業道德知識世界。熱衷于對這些職業道德知識與符號的記誦和邏輯演繹,使學生學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智慧,而是枯萎的職業道德語言和知識氣泡”。[3]另一方面,學校職業道德教育嚴格遵守教學管理,完成授課、考試等一系列教學任務。像傳授其他自然科學知識一樣,學校把職業道德知識當作客觀的職業世界的真理,要求學生去記憶和掌握一些抽象、僵化的職業道德概念、規范、規則,而對現實的職業道德現象和問題棄而不理。這種知識化、理論化、普遍化后的職業道德知識抽去了具有鮮活職業世界特征和主體生命表征的內容,無視學生的直覺與體驗、情感與態度;只管向學生傳授業已課程化的職業道德知識,而無視這些道德理論與知識能否解決學生現實生活中遭遇的種種道德沖突問題。[4]“去生活化”的結果是學生對職業道德教育的逆反、抵觸,甚至在職業道德教育的課堂內外發生大量的、非職業道德甚至反職業道德行為。
(三)職業道德教育方法“因循守舊”
目前,我國職業院校主要是通過課堂教學、班級生活會、各種宣傳媒體、以職業指導為主的專題講座和實習實訓等途徑開展職業道德教育,教材不分專業和年級統一使用,內容上以一般職業道德教育為主、行業職業道德教育為輔,教學上主要還是采取以教師、教材、課堂為中心的直接灌輸的方法,學生處于被動接受地位,缺乏主動學習精神。“職業道德多是通過課堂教學實現,比較重視職業道德知識的灌輸,重視榜樣的作用,要求言傳身教。課堂上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這種授課形式利于職業道德知識體系的傳授,學生較易掌握課程的內容,但職業道德教育內化的效果不夠理想”。[5]早在2003年,上海一項調查顯示,近九成的職業道德教育主要還是以課堂宣講為主,近八成的學校目前仍以書本為固定教材進行課堂教學,教師授課主要是講解教材。盡管有穿插案例、多媒體演示、請企業人員參與、組織社會調查等嘗試,但所占比重都很小。[6]而近幾年的多項調查表明,這種情況并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觀,這樣的教學方法顯然不能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提高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和選擇能力。教學上的因循守舊與不斷發展變化的職業行業要求以及學生個體發展的需要顯然不相適應,由此不難理解職業道德教育的低效甚至失效的原因。
(四)職業道德教育評價方式片面單一
當前職業院校對職業道德教育的評價,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在評價方式上重視知識考查,忽視責任感、榮譽感、敬業精神、心理素質、道德素質、工作態度、能力和行為評價;重視任課教師個人評價,忽視其他各科教師綜合評價;重視筆試成績,忽視評價的多樣性;重視教師的評價,忽視受教育者的自主評價;重視學校評價,忽視社會評價。據有關專家在上海職業學校的一項調查顯示,學校和企業對學生職業道德的評價出現了明顯的反差:學校教師認為學習、品德優秀的學生,未必是企業最認可的學生;反之,學校教師認為學習、品德一般的學生,企業卻往往肯定了他們的表現。[7]學校與企業在職業道德的評價方式上的錯位和不對稱,致使相當一部分職業院校畢業生的職業道德水平總體上還難以適應社會和企業對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規范要求。
三、當代職業道德教育的大勢:人本化選擇
職業道德教育非理性發展和教學上的封閉,使當代職業道德教育陷入了這樣一個尷尬的境地:學生掌握了大量的職業道德知識,這些空洞的知識卻在職業生活實踐中擔當不起職業道德品行生成和表現的承諾。值得慶幸的是,職業道德教育這一困境已經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和重視,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索和探討。在這個進程中,作為普世教育的重要原則之一,“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進入了職業道德教育者的視野。
(一)職業道德教育應源于生活、回歸生活
生活是職業道德教育的基礎,也是職業道德教育回歸的地方。對當代職業教育而言,職業道德教育要從職業生活中來,也應超越性地回歸職業生活。“生活與德育是一體的,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長的土壤,離開了生活,道德是無法進行的‘無土栽培’”。[8]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學校職業教育的“三位一體”,即“每一門學科,每一種教學方法,學校中的每一個偶發事件都孕育著培養道德的可能性”。[9]一是要注重職業道德教育的基礎性。關注基本的職業道德規范和底線,重視學生良好的職業行為習慣的形成,培養學生獨立的道德判斷能力。通過引導學生對現實生活中身邊的人的職業態度、辦事作風等進行用心感受和判斷,進而培養時時處處認真做事、誠實做人的良好習慣。二是要注重職業道德教育的階段性和層次性。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表明,人的需求有層次性,道德亦有層次性,道德從性質上可以劃分出不道德——“不善”、底線道德——“初善”、一般道德——“善”和高尚道德——“至善”等層次。[10]職業院校必須根據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從適應職業生活的現實需要出發,兼顧學生在不同年級的專業學習情境和不同從業志向,將職業道德教育的目標定位在不同層次。三是要注重職業道德教育的發展性。社會轉型、經濟全球化、職業流動性增強等因素,使得以強調利益導向和競爭效益的經濟倫理和以奉獻利他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倫理發生激烈的碰撞,這必然影響學生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職業道德教育目標要體現職業的要求,吐故納新,增添體現時代精神的新要求,著力培養學生適應未來社會職業的基本素質,如創新進取、公平競爭、誠實守信等,使職業道德教育始終適應社會職業發展和個體職業生涯發展的需要,永保生機與活力。
(二)職業道德教育應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告誡人們,知善不一定行善,善知與善行并不等同。道德品性的生成雖然需要有“知”的因素參與,但更需要在實際生活中訓練。“正如其他技術一樣,我們必須先進行活動,才能獲得這些德性。我們必須制作才能學會。……我們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為公正的,進行節制的才能成為節制的,表現勇敢的才能成為勇敢的”。[11]英國哲學家休謨也指出:“理性的知識既不能單獨成為任何意志活動的動機,也不能指導意志去反對情感,理性不具有道德準則的功能”。[12]先哲們的這些教導在我們的生活中早已被無數經驗所證實。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人生活在職業中不是為了道德而道德,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過上一種道德的職業生活。那么,職業道德教育必須是一種植根于職業生活的主體性、實踐性的教育,在具體的職業情境下,呈現不同的職業道德現象和問題,這樣的職業道德教育才會真正被受教育者內化。因為“一旦體驗者的道德體驗發生的時候,對這一個體驗者來說,道德教育已經實際地存在著了,并在這一個體驗者身上及其所處的導引者與體驗者的關系世界中發生了并繼續發生著道德的感染作用。從一般意義上說,只有以體驗者的道德體驗為出發點和歸宿,由導引者導引體驗者與他一起進入體驗狀態,誘發和喚醒體驗者的切身體驗,道德教育才算真正發生實際存在,對于道德教育的實踐來說,也才有實際的意義”。[13]
(三)職業道德教育應因材施教、教學做合一
職業教育主要是面向各種崗位培養技能型人才,學生學習的專業不同,今后從事的行業就會有所不同,而每個行業的職業道德都多少存在一定的獨特性。這就要求職業院校在開展職業道德教育的時候,要結合專業、特別是專業所對應的行業的特點,在教學內容和方法的選擇上因材施教,堅持專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結合、共性與個性兼顧。和專業技能知識的傳授一樣,職業道德教育知識的習得也應注重教學做合一的原則。日本非常重視員工職業道德的崗前和崗位培訓,培訓內容不僅包括職業認知培訓,還包括情景和與技能相結合的職業道德素養實踐訓練。例如,讓準員工在一些工藝和技術極為簡單的器械上重復性地完成無數次的機械而又枯燥的動作,以訓練準員工的耐心、耐力和認真態度,并對此進行嚴格的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崗。[14]實踐證明,通過教學做合一開展職業道德教育,有助于學生在職業實踐中提高對職業道德的認同,增強道德選擇能力。需要強調的是,教師作為職業道德知識的傳授者,在傳授職業道德知識的同時,也應該成為職業道德的典范,成為相關行業職業道德的率先實踐者,教師要針對學生在職業道德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進行現身說法,通過角色扮演、情景再現、行為演示等方法,與學生共同感知職業道德的內涵。
[1]黃炎培.黃炎培教育文選[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15.
[2]蔣凱.跨越知識與道德的鴻溝[J].現代大學教育,2003(3):12-16.
[3]高德勝.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現代德育困境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128.
[4]陳明利.關于學校道德教育困境的反思[J].教育探索,2006(1):97-99.
[5]曹育南,常小勇.職業道德教育的中外比較研究及啟示[J].職業技術教育,2002(19):61-64.
[6][7]馬樹超.新時期上海職業學校職業道德教育的問題與對策研究[R].2003.
[8]高德勝.生活德育簡論[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2(3):1-5.
[9]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M].趙祥麟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64.
[10]來永寶.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與大學生道德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5):11-12,16.
[11]苗力田.亞里士多德選集:倫理學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31.
[12]王淑芹.近代情感主義倫理學的道德追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4):83-85.
[13]劉驚鐸.道德體驗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60.
[14]王瑛.國外職業道德教育的經驗及啟示[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9(12):75-77.
王浪(1977-),女,湖南長沙人,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專業在讀博士,湖南農業大學科技師范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道德教育、人文教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中等職業教育創新德育模式研究”(課題編號:AJ08240)階段性成果,主持人:匡瑛;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當前中國職業教育若干難點問題研究”(課題編號:DJA080188)階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龐學光。
G710
A
1001-7518(2011)10-0008-04
責任編輯 韓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