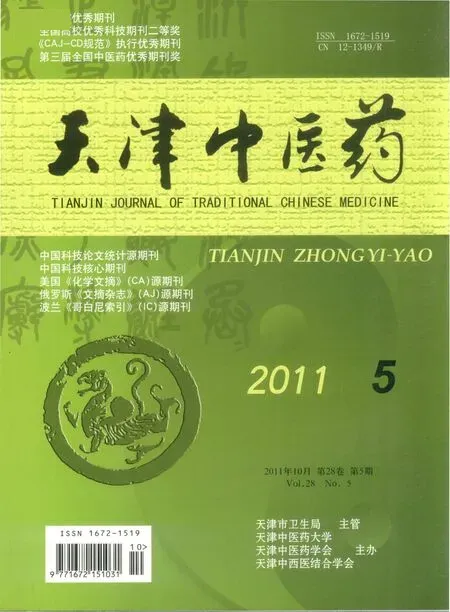兒童多動癥臨床辨證及證候分布規律的研究進展*
李亞平,馬 融,魏小維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天津 300193)
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或稱兒童多動癥,是一種常見于兒童時期的行為障礙,主要表現為注意力渙散、多動不寧、沖動易怒、情緒不穩等癥。多動癥兒童在認知、學習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社會功能出現諸多困難和障礙,患兒學習成績差、不守紀律、與父母、老師及伙伴的關系不和諧,這些不良后果嚴重困擾著患兒、家長以及老師。
“多動癥”由德國醫家Hoffmann在觀察到這一大類癥狀后,于1854年最早命名。兒童多動癥在西醫學領域屬于心理障礙范疇,其在兒童期心理障礙中是發現較早,研究較多的問題之一,是兒童精神科和兒童心理衛生門診中最多見的病種[1]。
1 證候研究及肝腎為主辨證體系的確立
證候是疾病發生、發展和演變過程中,某一個具體階段的本質反映,它是疾病特定階段的主要矛盾,但也受到疾病根本矛盾的制約,其由若干具有內在聯系、可以體現疾病本質的癥狀組成。證候診斷反映了中醫學對疾病認識的層次,它是疾病所處一定階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勢等的病理概括。在疾病所處的進退變化過程中,證候是動態變化的。證候的動態變化體現在兩個層次方面,一是證候的量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在同一證型內部,主癥的加重、減輕、出現或消失等變化;二是證候的質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某一疾病不同證型間的相互轉化,疾病的常規發展都是量變引起質變。因此,疾病的證型間不外乎兩種關系,平行(或并列)的關系;彼此間具有輕重先后,由此及彼的發展關系。不同的研究角度影響和推動某個特定疾病的辨證體系的進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完善,疾病的本質和特征性改變逐漸凸顯,而最終某個疾病的辨證體系是由該疾病的本質變化和證候特點決定。反過來,隨著某疾病的證候研究逐步積累、系統化,其成形的較為完善的辨證體系同樣也可以揭示出疾病的本質改變。
依照此思路,梳理兒童多動癥的臨床研究資料和文獻,將其辨證分型及證候分布規律歸納如下。
兒童多動癥的發現和研究歷史并不長,中醫領域對這個病也很陌生,沒有較明確的古代研究,現代中醫學者們通過大量觀察發現兒童多動癥的主要辨證分型為“腎陰不足,肝陽偏旺證”、“心腎氣虛證”、“心腎不交,水火失濟證”、“心氣陰兩虛證”、“心脾氣虛證”、“痰火擾心證”、“心肝火旺證”、“心肝腎失調證”、“脾氣不足,痰濁內阻證”、“肝脾不和,肝郁脾虛證”、“瘀血內阻證”等十余證型,臨床所占比例最大的證型是“腎陰不足,肝陽偏旺證”,約占各證型總和的三分之一以上[2-9]。從五臟辨證來看主要涉及臟腑為腎、肝、心、脾,最突出的臟腑是腎和肝,而且基本上都是兩臟共病的證型。從虛實辨證來看,最多見的是因虛致實的虛實夾雜證,腎虛的證候在各型中均較顯著。縱觀上述證候研究,似乎顯示出這樣的證候脈絡,五臟辨證中以腎系為主,肝腎同病、心腎同病、脾腎同病三型可能屬于腎系辨證中并列的證候類型,三者均有腎虛證的共同特點,不同點在于共病的另一臟腑出現差異分別為心、肝、脾三臟,三個復合證型在病因起源,證候表現及發展變化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分析現有文獻研究,很難看出在多動癥這個病種的發展變化中,三者之間有相互轉歸的跡象[10-12]。肝腎同病的證候是“腎陰不足,肝陽偏旺證”,心腎同病的證候是“心腎氣虛證”和“心腎不交,水火失濟證”,而脾腎同病的證候是“脾腎兩虛證”等。
此外,在兒童多動癥的臨床中,中醫學者們在辨證診斷時常常無法回避的一個特殊情況就是臨床中大量可見的“無證可辨”型的病例。客觀上講,只要有疾病診斷就一定存在某種證候,但中醫的證候診斷是基于看得見查得出的證候的,由于中醫發展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的限制,中醫辨證很少結合實驗室檢查、功能檢測、心理學量表等現代醫學檢測指標,所以辨證論治中的這些缺陷和不足,讓我們會經常遭遇“無證可辨”型的證候。多動癥作為一種心理、行為障礙性疾病,客觀化指標尤其缺乏,近幾年僅有少量研究報道通過證候量化以區分不同證型[13],而大多數中醫研究的文獻中對其只作辨病治療而不進行辨證的現象可能與此有關。關于“無證可辨”型,需要洞察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在其他疾病中它常常出現于疾病緩解期或恢復期,在多動癥中它是否也提示疾病處于較輕微的病情狀態下,甚或與腎精虛證和腎虛肝旺證有遞進或發展關系,尚未見到相關研究報道[14-15]。
2 證候命名的標準化
兒童多動癥的證候復雜,證型種類繁多,又多見臟腑兼夾同病,證候命名不一致,證候就無法保證標準化,嚴重影響不同研究者對同一病證研究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證候研究的前提是證候命名的標準化,1994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中醫病證診斷進行了規范并發布了標準,在其目錄中雖然列有證候名稱,但對其命名并沒有明確進行標準化規定,更沒有以疾病為綱,在具體疾病內規范證候命名及其內容,這也許會成為將來證候標準化研究的方向之一。目前,相關文獻中,申春悌認為,目前的“四字”證名很難反映疾病的病性、病位、病理,欲明確各證證名的定義及其內涵外延,須按照臟腑病位、病因、病性、病機的原則采用“八個漢字”規范證名,進而建立各證的概念及其定義[16]。一個證所涉及的臟腑(兼證)以不超過兩個為宜,以免增加確定診斷指標的難度[16]。結合安海燕等對于“證”本質的分析和思考[17],及方肇勤對于“辨證標準的基本要素與構成”的探討[18],兒童多動癥的證候中類似“腎精不足,腦髓失養”“腎陰不足,肝陽偏旺”等證的命名就較為規范,值得參考。
3 審證求因,辨識多動癥的病機關鍵
現代醫學認為兒童多動癥為腦功能失調所致,與早產、難產等因素造成的輕微腦損害密切相關。有研究發現本病的遺傳傾向高達80%,與多巴胺(DA)基因的多態性、腦前葉功能發育不良、抑制性神經遞質缺乏等因素有關[19]。李亞平等對ADHD危險因素調查研究發現,遺傳及胎產因素在患兒中所占比例達57.5%[4]。李宜瑞等的分子遺傳學研究顯示中醫辨證屬于腎虛肝亢型的多動癥患兒,其神經遞質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的水平失常,與對照組兒童相比有統計學差異[20]。最近的分子遺傳學研究發現遺傳因素在多動癥的病因方面起主要作用,甚至認為多動癥是一種多基因遺傳病[21]。中醫理論認為遺傳及胎產因素為先天因素,主要責之于先天之本——腎,而腎以腎精為根本,腎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腦,腦為髓海,由此可見現代醫學研究涉及到的神經遞質、腦、遺傳等都與中醫理論的腎關系密切,各種先后天因素導致兒童腎虛精弱髓海不充,腦失精明,就會表現出注意力不能集中、善忘多動、易怒而無法自控等多動癥癥狀。現代醫學研究還發現多動癥兒童體內的抑制性神經遞質缺乏,提示中醫認為“陰陽失調,陽動有余,陰靜不足”的病機理論是成立的。腦電圖及腦電圖的頻率競爭漲落圖研究發現,患兒10 Hz成分較正常兒童明顯減低(P<0.05),α波協同結構左移,優勢頻率存在慢化趨勢,這提示中樞神經的興奮水平低下,皮質覺醒功能不足。而10 Hz成分越少,腦自組織能力越差,認知速度越慢,注意力維持時間越短,反應穩定性越差(P<0.05)[22]。這種腦電波優勢頻率慢化的表現亦與腎精虧虛、陰陽失調的病機特點相符[4,23]。骨齡方面的研究結果同樣顯示多動癥兒童發育落后于正常兒童,支持上述腎虛的病機理論。
結合以上現代中、西醫領域的各項研究結果,可以推斷兒童多動癥病因病機關鍵可能在于五臟中的腎虛,而致其他臟腑功能失調,或可兼挾有痰瘀等病理產物[24]。“無證可辨”的不顯著證候、“腎虛精虧,腦髓失養”證和“腎陰不足,肝陽偏旺”證,三者在病情上是否有遞進或發展轉化關系,值得進一步研究以驗證上述推論。
[1]蘇林雁.兒童多動癥[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4:1.
[2]黎 欣,夏隆江.兒童多動癥證候分布規律的研究[J].陜西中醫,2009 ,30(11):1467-1469.
[3]梅其霞,王敏建,李 燕,等.小兒智力糖漿治療兒童多動癥臨床分析[J].中成藥,2010,32(7):1072-1074.
[4]李亞平,馬 融,魏小維.益智寧神顆粒治療兒童多動癥腎陰不足肝陽偏旺證的臨床分析[J].天津中醫藥,2004,21(5):420.
[5]鐘天平,王 鎧,馮梅珍,等.兒童多動癥針灸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對照研究[J].中國民族醫學,2010,22(13):1661-1663.
[6]馬 融,魏小維,李亞平,等.益腎填精法治療兒童多動癥及其神經生化機制研究[J].天津中醫藥,2007,24(4):309.
[7]李鴻敏,覃耀真,張玉蛟.兒童多動癥的病因及中醫藥防治[J].山西中醫學院學報,2009,10,(2):76-78.
[8]丁正香,朱克儉,劉天舒,等.小兒智力糖漿治療兒童多動癥50例療效觀察[J].湖南中醫雜志,2008,24(5):33-34.
[9]馬 融,張喜蓮.髓海發育遲緩致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病機假說探討[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8,23(8):737-739.
[10]李亞群,韓新民.試從錢乙五臟辨證體系論兒童多動癥的辨證施治[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30(7):7-9.
[11]楊 玲,王 娣.相修平辨治兒童多動癥經驗[J].遼寧中醫雜志,2007,34(10):1367-1368.
[12]馬 融,古今楠.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中醫病機及治法探討[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8,10(12):29-30.
[13]黃敬之,林 過,黃 嫻.Conners量表在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中醫證型診斷中的價值[J].福建中醫藥,2008,39(5):10-11.
[14]何軍鋒.無證可辨淺識及對策[J].醫學與哲學,2006,27(8):76-77.
[15]帥明華,郭春香.論小兒病無證可辨及其中醫對策[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0,6(11):69-70.
[16]申春悌.中醫臨床臟腑辨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探討[J].江蘇中醫,2001,22(4):1-3.
[17]安海燕,蔡紅兵,周迎春,等.關于證本質研究現狀的思考[J].四川中醫,2007,25(6):18-20.
[18]方肇勤.辨證標準的基本要素與構成[J].上海中醫藥雜志,2004,38(1):3-6.
[19]高雪屏,杜亞松,李雪榮,等.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遺傳方式研究[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5,20(1):55-57.
[20]李宜瑞,黃福群,楊京華,等.血兒茶酚胺與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及其中醫辨證的關系初探[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1,8(1):49-50.
[21]錢秋謹,王玉鳳.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與遺傳[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10,25(12):869-871.
[22]孫 黎,王玉鳳,何 華,等.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患兒各亞型α波競爭圖特點[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02,34(6):704-708.
[23]馬 融,李亞平.多動癥兒童的腦電圖變化機制[J].中國臨床康復,2005,9(28):158-159.
[24]冷方南,凌耀星,彭國忱,等.兒童多動癥臨床治療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0:25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