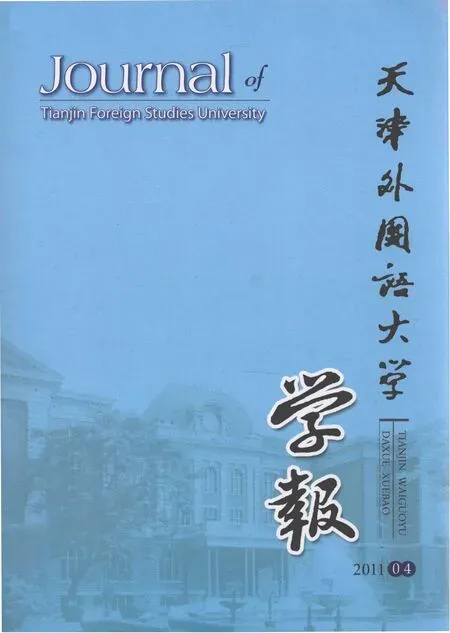談中國外語教育30年
胡壯麟
(北京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北京 100871)
談中國外語教育30年
胡壯麟
(北京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北京 100871)
2009年我曾寫過《我國外語教育六十年有感》①一文。由于時間跨度較大,且前30年中我在1954-1972的19年中不在高校工作,對一些問題不是很有把握。這次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和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聯(lián)合舉辦的“首屆全國語言研究和外語教育研討會”給了我機(jī)會,把有關(guān)話題集中在后30年,即改革開放后的30年,并能對一些問題與參加會議的高校教師和同學(xué)交談商討。
一、第二次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
我在2009年一文中談到建國后我國外語教育在全國范圍內(nèi)出現(xiàn)過兩次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第一次出現(xiàn)在前30年,我國外語教育的主要語種由英語轉(zhuǎn)為俄語;第二次出現(xiàn)在后30年,由俄語轉(zhuǎn)為英語。盡管自1959年后已經(jīng)呈現(xiàn)俄語招生壓縮的苗頭,由于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一些高校和教育部領(lǐng)導(dǎo)無暇顧及這個問題,但從改革開放后,這個從俄語轉(zhuǎn)為英語的形勢已逐步明朗化了。如教育部抓教育大綱的制定工作,一般都是讓英語專業(yè)的專家們先行一步,其他語種隨后跟上;每年英語招生人數(shù)絕對領(lǐng)先;各高等學(xué)校開設(shè)的公共外語(后來改名為大學(xué)外語)也是以英語為主,以至各高校領(lǐng)導(dǎo)最關(guān)心的是本校大學(xué)英語四、六級全國統(tǒng)考的成績,資金的投入和設(shè)備的添置當(dāng)然也是大學(xué)英語得天獨厚;最后,英語也成為中小學(xué)義務(wù)教育的主要外語課程。
英語作為我國外語教育的主要語種是由政治和經(jīng)濟(jì)形勢的變化決定的,這毋庸質(zhì)疑。由于這樣的轉(zhuǎn)移,對其他語種有些特殊安排。從高等院校來說,一些有條件的院校(如北京大學(xué)、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等)都開設(shè)了俄、日、法、德、西班牙等數(shù)十種外語專業(yè)課程。為了支持這些語種的存在和發(fā)展,北京大學(xué)在晉升職稱時多次明確規(guī)定對申報的其他語種的講師和副教授不強求資歷和科研成果。在招生方面,一些其他語種可以提前錄取以保證生源。為了解決這些專業(yè)學(xué)生的就業(yè)困難,有的學(xué)校讓其他語種學(xué)生同時學(xué)習(xí)兩門外語,主要是英語。所有這些,我認(rèn)為都是必要的。
由于我國的義務(wù)教育和高中教育基本上是英語,這就導(dǎo)致高等院校的外語專業(yè)學(xué)生的教學(xué)質(zhì)量不平衡,英語專業(yè)的學(xué)生至少已經(jīng)有十年的中小學(xué)英語打底,可以往專業(yè)方向深入發(fā)展,而其他語種要從頭學(xué)起,難以做到。于是有人提出在中小學(xué)教育中也應(yīng)規(guī)劃進(jìn)行其他語種的教育。顯然,能承擔(dān)此任務(wù)的只能是一些外語學(xué)校或外語大學(xué)附屬中學(xué)。即使如此,我接觸到的一些學(xué)生家長還是有顧慮。他們的孩子學(xué)了其他語種后,雖然可以通過提前錄取升入高等院校的有關(guān)院系,但是萬一未能提前錄取,就要參加全國統(tǒng)考,這時在英語這一科目上就要吃大虧。因此,這是今后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二、五次轉(zhuǎn)向
為了說明外語專業(yè)方向設(shè)置的五次轉(zhuǎn)向,有必要交待一下改革開放前的基本情況。在文革后期國內(nèi)高校開始招收學(xué)制為三年的工農(nóng)兵學(xué)員,在外語技能方面只培養(yǎng)聽、說、讀三項。若干年后,我的老師李賦寧先生曾多次自我檢討,說他很對不起這些工農(nóng)兵學(xué)員,在他們的三年學(xué)習(xí)期間沒有讓他們寫過一篇作文。
(1)亦文亦語。1978年高考恢復(fù),之后又開始實行研究生(先碩士生后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李賦寧先生正式出任北京大學(xué)西語系系主任。就英語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來說有兩個方向:文學(xué)和語言。需要說明的是,所謂語言方向并不只是聽、說、讀、寫,而是學(xué)習(xí)一定的專業(yè)課。我從側(cè)面觀察先生整天忙于動員已經(jīng)年邁的教授和副教授們開設(shè)各種文學(xué)方向和語言方向的專業(yè)課。應(yīng)該說,先生本人和各系的教授們對開設(shè)文學(xué)課程熟門熟路,因為中國高校傳統(tǒng)的教學(xué)路子是文學(xué),但為語言方向?qū)W生安排專業(yè)課程時,先生陷于重重困難,因為即使按當(dāng)時的認(rèn)識,像英語語言史、英語詞匯學(xué)、英語語音學(xué)這類課程,許多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愿意承擔(dān),或者說,有的教師還從來沒有開過這類課程。這時,1980年末剛從英國留學(xué)回來的姜望琪老師臨危授命,挑起了給英語系研究生開設(shè)語言學(xué)課程的重?fù)?dān)。我在1981年5月份從澳大利亞回校后,則為1979級的本科生陸續(xù)開設(shè)英語語言學(xué),以后幾年陸續(xù)開設(shè)應(yīng)用語言學(xué)、英語語體學(xué)、文學(xué)文體學(xué)等課程,同時給研究生開設(shè)英語教學(xué)法、功能語言學(xué)、英語語體學(xué)、話語分析、語言測試等課程。談這些是想說明當(dāng)時的英語系領(lǐng)導(dǎo)心目中的確有兩個專業(yè)方向,我把這個階段叫作“亦文亦語”,文語并重,盡管語言方向的教學(xué)力量稍許薄弱一些。
(2)以“語”擠“亦文亦語”。第一個“語”指有關(guān)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不是語言方向的專業(yè)課。由王佐良、許國璋、李賦寧等老先生精心設(shè)計的“亦文亦語”的專業(yè)方向并不能走得很遠(yuǎn),阻力來自高校外語院系的領(lǐng)導(dǎo)和教師自己。道理很簡單,要按這兩個專業(yè)方向培養(yǎng)學(xué)生,不能說空話,便需要開設(shè)一定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專業(yè)課,而這又需要在授課時間上給以保證。為此,北京大學(xué)和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都開始實行基礎(chǔ)課兩年和專業(yè)課兩年的課程設(shè)置。20世紀(jì)80年代在當(dāng)時的“外語教材編審委員會”領(lǐng)導(dǎo)下制訂英語專業(yè)教學(xué)大綱時,這兩所學(xué)校提出了將人們習(xí)慣的四年精讀課的設(shè)置代之以一、二年級重點以聽、說、讀、寫語言技能教學(xué)為主,三、四年級多安排文學(xué)方向或語言方向的專業(yè)課,只有這樣學(xué)生才有時間接受有關(guān)方向的專業(yè)教育。不料,這個建議遭到多數(shù)委員的反對,他們認(rèn)為,中國英語專業(yè)學(xué)生水平低,四年一貫制的精讀課、聽力課、口語課不能動,這樣,北京大學(xué)和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在會議上成了少數(shù)派,所提方案未獲通過。為了這件事情,王佐良先生一有機(jī)會便費心給一些兄弟院校的英語系、室的領(lǐng)導(dǎo)做工作,并說像文體學(xué)這樣的課程完全可以代替學(xué)生已經(jīng)感到膩煩的高年級精讀課。
(3)非文非語。人們絕對不會預(yù)料到,即使這個“以語言技能為主”的方向也岌岌可危。不久,從教育部領(lǐng)導(dǎo)到人事部領(lǐng)導(dǎo)放出話來,外語不是專業(yè),只是技能,因此應(yīng)該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第二專業(yè),準(zhǔn)備將來就業(yè)。于是各校和所屬外語院系紛紛討論復(fù)合型人才的培養(yǎng)。這具體表現(xiàn)在1987年中國英語教學(xué)研究會換屆時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曾安排了兩個大會報告,吹響了培養(yǎng)復(fù)合型人才的號角。一個報告是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在英語系下設(shè)置了七個方向。討論時我提出這個經(jīng)驗北京大學(xué)很難借鑒,因為北京大學(xué)招生人數(shù)少,按此辦理,每個方向只有六七個學(xué)生,沒法排課。開設(shè)這些專業(yè)課的教師隊伍如何建立?即使開設(shè)了兩三個新方向,只能導(dǎo)致這些學(xué)生將來被限制在這些方向內(nèi)找工作,反而不利于學(xué)生的就業(yè)。會議休息時,作報告的老師特地和我打了招呼,說他的報告是上面授意的。另一個報告是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的經(jīng)驗。這個學(xué)校從英語學(xué)院抽調(diào)一部分教員成立了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國際新聞學(xué)院、國際經(jīng)濟(jì)學(xué)院等新的學(xué)院。我對成立新的學(xué)院是贊同的,但我感興趣的是上外殘存的英語學(xué)院還存在不存在?它的課程設(shè)置和教學(xué)改革如何進(jìn)行?后來,在一些復(fù)合型人才培養(yǎng)的討論會上,一些學(xué)校介紹了開設(shè)第二專業(yè)的經(jīng)驗。有一所西南地區(qū)的大學(xué)匯報時說,他們?nèi)蠟閷W(xué)生開設(shè)旅游專業(yè)的課程,三下開設(shè)經(jīng)濟(jì)專業(yè)的課程,四上開設(shè)xx專業(yè)的課程,四下又開設(shè)xx專業(yè)的課程,令人啼笑皆非。我也曾聽說過,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與清華大學(xué)國際經(jīng)濟(jì)專業(yè)合辦過一個復(fù)合型人才的專業(yè),后來一方認(rèn)為學(xué)生用在學(xué)習(xí)英語課程的時間少了,另一方認(rèn)為用在學(xué)習(xí)國際經(jīng)濟(jì)專業(yè)的課程少了。其實這樣的結(jié)局是可以預(yù)料的,因為學(xué)生每周上課時間就20學(xué)時左右。對此我個人有如下幾點看法:第一,政府部門領(lǐng)導(dǎo)關(guān)心學(xué)生的就業(yè)選擇用心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第二,英語專業(yè)學(xué)生和外語專業(yè)學(xué)生畢業(yè)時找工作的困難有一部分原因與我國擴(kuò)招過快過猛有關(guān),這樣,一方面是讓更多的年輕人有接受大學(xué)教育的機(jī)會,另一方面這個決定多少違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規(guī)律;第三,從外語教育來說,一些中小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學(xué)校還是缺乏外語教師的,但一些畢業(yè)生較多地愿意留在大城市,這需要在政策上有特殊照顧,輔之以思想工作部門的耐心教育。遺憾的是,人們在解決問題時,把罪責(zé)歸因于英語或外語不是一個專業(yè)。如果真是如此,他們應(yīng)該要求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取消英語或外語這些專業(yè)。不管怎樣,我把這個階段稱為“非文非語”的轉(zhuǎn)向,因為不論是語言方向或是文學(xué)方向的專業(yè)教育都被靠邊站了。
(4)以文代文。這里指以“文(化)”方向代“文(學(xué))”方向。自上世紀(jì)80年代末,人們開始認(rèn)識到語言與文化的緊密關(guān)系,我們可以通過學(xué)習(xí)語言來學(xué)習(xí)文化,并通過學(xué)習(xí)文化來學(xué)習(xí)語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學(xué)者專門成立了學(xué)會。在高校方面,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雖然沒有改動原來的中文校名,但英文名稱已從Beiji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改名為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語言大學(xué)一度改名為北京語言文化大學(xué)。就在這個時刻, 1990年前后教育部文科處的領(lǐng)導(dǎo)曾到北京大學(xué)開了一個座談會,其用意是征求北大各外語系系主任的意見,是否同意把語言文學(xué)系改名為語言文化系。在這次座談會上,東語系表示同意,把系名改為東方語言文化系,英語系和俄語系不想改,但最后表態(tài)只要教育部領(lǐng)導(dǎo)覺得一定要改,這三個系是會服從的,把皮球踢回給教育部。之后,就沒有下文了。說一句公道話,教育部這一舉措反映了國際上辦學(xué)的趨勢。我1991年去美國加州大學(xué)圣巴巴拉分校訪學(xué)時,曾就此問題和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商討,他認(rèn)為,國外的大學(xué)除英語系外,許多外語系確實正在這么做,如他所在的中文系的英文名稱就是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因為這樣培養(yǎng)的學(xué)生學(xué)了外語不一定局限于研究有關(guān)國家的文學(xué),也可以研究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5)文、語、翻譯三足鼎立。前幾年,經(jīng)過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批準(zhǔn),在外語院系增設(shè)翻譯的專業(yè)方向。這樣,解決了30年來所沒有解決的大問題,那就是文學(xué)方向和語言學(xué)方向都可以招研究生并有碩士生導(dǎo)師、博士生導(dǎo)師,唯獨翻譯沒有。因此,北京大學(xué)一位專門從事翻譯工作的老學(xué)者為不能招碩士生和博士生而感到不能理解。當(dāng)然,有的學(xué)校采取靈活的辦法,把所招從事翻譯理論研究的學(xué)生掛靠在文學(xué)方向或語言方向。我不是學(xué)位委員會成員,不了解專業(yè)設(shè)置的具體討論情況,但的確聽到過這樣的言論:翻譯只是一門實踐課,不是一門學(xué)科。其實,翻譯學(xué)早就有它的理論,我在國外學(xué)過翻譯理論這門課,對國外的Nida理論、國內(nèi)的“信、達(dá)、雅”理論,以至許淵沖先生的“形美、音美、意美”理論還是知曉一些。從市場效應(yīng)來說,這門新學(xué)科也是見好。早在我在清華上學(xué)時,系主任就跟我們直說:“你們這一級學(xué)生是按將來從事翻譯工作這個目標(biāo)培養(yǎng)的。”我1952年暑假曾被借調(diào)至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參加當(dāng)時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世界和平大會”做翻譯工作,畢業(yè)后分配至總參謀部二部最初任命為翻譯。沒有想到,翻譯正式作為一門專業(yè)方向足足花了60年的時間。不管怎樣,我本人認(rèn)為,與“非文非語”相較,在文學(xué)和語言兩個方向外,增添翻譯方向是一大進(jìn)步。
三、不同風(fēng)格的外語教學(xué)
我首先舉一個我常提到的例子。兩位中學(xué)同學(xué)高考時一個考入北外英語系,一個考入北大英語系。周末時那位北外的學(xué)生來北大看望老同學(xué)。北外的學(xué)生時不時露幾句英語,而且是地道的英國英語,而那位北大的同學(xué)桌子上放著一堆書,時不時問對方這本小說是否讀過?那本小說是否讀過?從兩個同學(xué)的不同表現(xiàn)可以看到兩個學(xué)校的不同風(fēng)格。我認(rèn)為,在外語教育中應(yīng)該讓不同學(xué)校有不同風(fēng)格,不要搞成一個類型。說到不同風(fēng)格,還得插上一件趣事。有次在北京召開的外語教學(xué)國際會議上,有位外國學(xué)者批評北大風(fēng)格只能培養(yǎng)死讀書的聾啞病患者,不利于培養(yǎng)受到社會歡迎的人才,譬如說,創(chuàng)辦新東方這樣的教師。她發(fā)完言后,我不得不舉手告訴她,所謂新東方的俞敏洪、王強、包凡一等都是北大的學(xué)生,而且聽過我的課。這說明不同風(fēng)格的學(xué)校也可以培養(yǎng)出不同風(fēng)格的學(xué)生,不一定都是書呆子。
這一認(rèn)識也反映于對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和專業(yè)課程的設(shè)置上。首先,英語專業(yè)四、八級考試實際上考的是語言技能,未能考察英語專業(yè)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對英語教師的培養(yǎng)也不利。在我擔(dān)任英語系系主任期間,總怕人家說北大的學(xué)生聽說能力不行,因此在一次教研室開會時,我提出專門抽調(diào)幾位教員成立聽說教學(xué)小組的建議,為了使這些教員安心工作,希望教研室在提升職稱時給以特殊安排。這時,老系主任李賦寧先生不表同意,他認(rèn)為,這不利于教師的全面發(fā)展,這個計劃于是沒有實現(xiàn)。現(xiàn)在想想李先生的話是有道理的。如果單純強調(diào)聽說,英國倫敦街頭上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jī)都可以到中國高校做教授,我們中國沒有一個老師在聽說能力上能與他媲美。其次,把語言教學(xué)分成聽、說、讀、寫四個技能受的是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的影響,這個理論把語言切分了,反映在教學(xué)上則把外語課分成聽、說、讀、寫等互相不通氣的課程。其實,這四個技能是可以互補的。在這個問題上,李賦寧先生又給了我?guī)椭N易鳛橛⒄Z系系主任,每年最頭疼的是分配教學(xué)任務(wù)。一般來說,讓老師教聽力課最順當(dāng),沒有人拒絕,我自己也教過聽力課。但如果讓教師擔(dān)任寫作課或翻譯課則就麻煩了,有的教師能推就推,因為這些課要求教師的語言水平高,而且改本子很花時間。當(dāng)我在教研室提出這個困難時,李賦寧先生發(fā)話了。他認(rèn)為,英語技能的培養(yǎng)不能絕對切分,閱讀課老師讓學(xué)生寫作文責(zé)無旁貸,教聽力課的老師應(yīng)當(dāng)讓學(xué)生課后將所聽到的內(nèi)容寫出來,教口語課的教師可以讓學(xué)生將堂上討論的內(nèi)容寫成文章。最后他把他的看法凝結(jié)成一句話:Every course is a writing course.我想,廣外的王初明教授一定會對李賦寧先生這一意見表示贊同,用各種途徑讓學(xué)生動筆寫。同理,每門課老師在堂上用英語授課,用英語討論,既創(chuàng)造了聽英語的機(jī)會,也創(chuàng)造了說英語的機(jī)會,其效果不一定比為說而說的口語課和為聽而聽的聽力課差。
四、新外語教學(xué)理念此消彼長
當(dāng)國外在上世紀(jì)60年代前后大力提倡聽說教學(xué)法、情景教學(xué)法、句型教學(xué)法之時,我國正陷于這樣那樣的政治運動,因此,在改革開放后,我國外語教學(xué)首先補了這堂課。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學(xué)生家長問我這樣一個問題:“聽說學(xué)英語只要掌握50多個句子就可以學(xué)會了。”我因所知不多,無從回答。但從當(dāng)時編的教材,每篇課文的確首先出現(xiàn)一兩個句型,然后是替換練習(xí)。直到后來我從Advanced Learner’ s Dictionary的附錄中才看到英語有25個主要句型,分得細(xì)一些,便成了65個句型。我至今佩服這位家長掌握信息如此靈通。就情景教學(xué)法來說也有不同認(rèn)識。我最初只是認(rèn)為在口語教材中提供各種情景,如教材中有機(jī)場、旅店、郵局、書店、鍛煉等情景。后來才了解這還不是正宗的情景教學(xué)法,因為學(xué)生無法在漢語的環(huán)境中練習(xí)英語,如課堂上可以讓學(xué)生分別扮作郵局管理員和顧客進(jìn)行對話,可是我們的學(xué)生真的到了郵局還得說漢語。據(jù)說真正的情景教學(xué)法是讓學(xué)生在使用外語的實際情景中學(xué)。這使我想起在澳洲進(jìn)修時一位朋友帶我去一家日本餐廳吃飯,鄰座的是一位老師帶著一批中學(xué)生圍桌而坐,不時用日語教同學(xué)說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很難想象我是否也應(yīng)帶同學(xué)去西餐廳用餐呢? 但我回憶起早在1952年我念大學(xué)二年級的時候,和一些同學(xué)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給外賓做生活翻譯,每天還是學(xué)到不少外語。今天這叫作志愿者。問題是當(dāng)不上志愿者的同學(xué)又該如何安排他們的學(xué)習(xí)呢?這幾年有機(jī)會參加教育部義務(wù)教育英語教學(xué)大綱的制定工作,一些有經(jīng)驗的專家提出任務(wù)教學(xué)法的理論,與上述教學(xué)法似乎一脈相承。因此,如何更好地貫徹這個先進(jìn)理念還需要不斷總結(jié),交流經(jīng)驗。
應(yīng)該承認(rèn),從上世紀(jì)80年代末,我國制定的外語教學(xué)大綱,高校的、中小學(xué)的、高職高專的,都采用了最時興的交際教學(xué)法。這個教學(xué)法最引入注目的是強調(diào)teach the language,not teach about the language和fluency over accuracy。這個教學(xué)法有不少優(yōu)勢,但在實際中我也碰到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以“不要教語言知識”為例,這意味著語法教學(xué)要讓路。在實際教學(xué)中,任何一個外語教師都會發(fā)現(xiàn)對幼兒或小學(xué)生可以這么要求,但初高中學(xué)生和大學(xué)生有一定的邏輯思維,讓他們唱山歌一樣學(xué)外語畢竟不是辦法。這些教師也會發(fā)現(xiàn)班上外語學(xué)習(xí)成績好的學(xué)生都是語法概念清楚的。就流利和正確的關(guān)系來說,也有讓人感到有自相矛盾或困惑之處。某人說話滔滔不絕,但意義表達(dá)不確切或錯誤百出,還能達(dá)到預(yù)期的交際效果嗎?如果說的、聽的、寫的是錯誤的,積疾難治,怎么辦?當(dāng)然我們可以強辯說,流利當(dāng)然要求正確條件下的流利,這樣,先流利后正確和先正確后流利的爭論成了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哲學(xué)命題。
近幾年又出現(xiàn)了認(rèn)知教學(xué)法、建構(gòu)主義教學(xué)法、連接主義教學(xué)法等新的教學(xué)理論。認(rèn)知教學(xué)法給人以這是對交際教學(xué)法的反動之感,建構(gòu)主義教學(xué)法不強調(diào)對語法結(jié)構(gòu)的分析,把結(jié)構(gòu)整體接受下來再說,連接主義教學(xué)法似乎介于兩者之間。這些需要我們進(jìn)一步了解和在實踐中檢驗。
我之所以談以上這些理論,是想說明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外語教學(xué)理論與語言學(xué)理論有密切關(guān)系,上述這些教學(xué)理論往往受結(jié)構(gòu)主義、功能主義、生成主義、認(rèn)知主義等語言學(xué)理論的影響發(fā)展起來的。第二,除語言學(xué)理論外,外語教育也要關(guān)注其他學(xué)科的發(fā)展,如哲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學(xué),以至計算語言學(xué)。因此,作為一名外語教師不能只把自己看作一個教書匠,需要一定的語言學(xué)、心理學(xué)、教育學(xué)等學(xué)科的知識武裝自己。第三,對待各種外語教學(xué)法不要像狗熊掰棒子那樣,掰一個丟一個,最好把這些理論看作一種資源,根據(jù)不同教學(xué)目標(biāo)、教學(xué)對象、教學(xué)時間和教學(xué)條件去選擇合適的教學(xué)法或調(diào)整自己的教學(xué)法。第四,同理,與其讓學(xué)生在本科生期間花時間去學(xué)習(xí)旅游、經(jīng)濟(jì)、法律這類課程,不如學(xué)習(xí)哲學(xué)、邏輯學(xué)、西方文化、世界歷史、世界地理、計算機(jī)操作等課程,在素質(zhì)教育上狠下功夫。何況學(xué)生在畢業(yè)后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有一年的見習(xí)期,素質(zhì)提高了,很快就能適應(yīng)新的工作。
五、外語教材建設(shè)
外語教學(xué)的改革和發(fā)展除在培養(yǎng)目標(biāo)和學(xué)制上統(tǒng)一認(rèn)識外,首先要抓教材建設(shè)。因此,恢復(fù)高考和實行研究生培養(yǎng)制度后,教育部首先成立了“外語教材編審委員會”,組織力量編寫各種外語教材,既有關(guān)于聽、說、讀、寫的技能課教材,也有文學(xué)、語言學(xué)、翻譯和文化課程的教材;既有面向本科生的,也有面向高職高專和研究生的教材。至1987年,教育部認(rèn)為教材工作基本完成,這個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應(yīng)轉(zhuǎn)向制定外語教學(xué)大綱和討論外語教學(xué)的全局性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原教材編審委員會解散,另外分別成立“專業(yè)外語教學(xué)指導(dǎo)委員會”和 “大學(xué)外語教學(xué)指導(dǎo)委員會”。機(jī)構(gòu)的變化實際上也反映了編寫外語教材在政策上的變化,那就是從“統(tǒng)編教材”轉(zhuǎn)向“一綱多本”。
(1)統(tǒng)編教材。一般來說,統(tǒng)編教材的優(yōu)勢是集中全國力量,指定最有條件的學(xué)校和專家編寫最急需的教材,往往先制定這門課程的教學(xué)大綱,然后根據(jù)大綱要求編寫教材,教材完成后組織更多的學(xué)校和專家進(jìn)行審查和修訂,以保證質(zhì)量。我曾參加過由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王佐良先生牽頭的英語文體學(xué)大綱制訂和教材審訂的工作。先是1985年在華中師范大學(xué)召開文體學(xué)大綱審訂會,與此同時,還舉行了小型學(xué)術(shù)研討會,我宣讀了論文《語音模式的全應(yīng)效果——試析狄倫·托瑪斯一詩的語音模式》②。同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參加討論丁往道主編的《英語文體學(xué)教程》。最初由我和李延福主編的《語言學(xué)教程》在教材編審委員會立項后也經(jīng)歷過同樣的過程。審稿會主審有山東大學(xué)校長吳富恒、王佐良先生和桂詩春先生,另有來自各校的專家十余人。最后,劉潤清教授也參加主編工作。
(2) 一綱多本。“一綱多本”的模式之所以推廣,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專業(yè)外語教學(xué)指導(dǎo)委員會”的主要任務(wù)不再是教材審定,另一方面一些出版社、學(xué)校和學(xué)者都有積極性,積聚力量自行編寫和出版外語教材。就我個人體會來說,“一綱多本”的最大優(yōu)勢是能夠根據(jù)不同地區(qū)、不同學(xué)校、不同學(xué)生程度編寫和出版適合特定需要的教材。試以我參與主編的《語言學(xué)教程》為例,最難以掌握的是難易度,不是容易了,就是難了。試想,單靠一本教材如何能滿足不同的需要呢?隨著多種教材的出版,各學(xué)校授課教師對教材自主選擇有了保證。
(3)主體教材。近幾年來,教育部對義務(wù)教育階段的各種教材,包括已經(jīng)通過的30種左右的外語教材,進(jìn)行審核,一些不合格的教材將被淘汰,一些優(yōu)秀教材將被推廣。從積極面來看,這一舉措將有助于解決地方保護(hù)主義對教材發(fā)行的不公平競爭,但這一模式是否會有負(fù)面影響有待觀察,至少一些出版社和編者這段時間都在提心吊膽過日子,怕本單位的教材給否了。不管怎樣,這意味著在義務(wù)教育階段的教材工作將從“一綱多本”模式走向“主體教材”模式。目前還不清楚在基礎(chǔ)教育的教材建設(shè)方面將走多遠(yuǎn)。
六、外語教育的大發(fā)展
這30年我國外語教育的大發(fā)展有目共睹。之所以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這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大環(huán)境。從外語教育的發(fā)展看,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恢復(fù)高考。如果把我國外語教育分成兩個階段,顯然前30年以培養(yǎng)三年制的工農(nóng)兵學(xué)員告終,后30年通過高考錄取恢復(fù)了四年制的大學(xué)教育開始。乍看起來,恢復(fù)高考保證了年輕人接受大學(xué)教育的公平。我認(rèn)為,單從學(xué)制的“恢復(fù)”一詞不能完全說明公平的內(nèi)涵,因為前30年大學(xué)也是實行四年制的,但前30年有的中學(xué)生被動員上山下鄉(xiāng)了,有的因家庭出身不好或者不讓報考,或者成績達(dá)標(biāo)了,卻榜上無名。因此,我們今天所談的公平比前30年做得更好一些,是排除政治干擾的公平。最近也談到如何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人才的問題,據(jù)說錢學(xué)森先生提過這樣的意見,我想想也是。按現(xiàn)在的模式,像華羅庚這樣的數(shù)學(xué)家是難以進(jìn)入高校大門的。這樣,像北京大學(xué)獲準(zhǔn)先行一步實行中學(xué)校長推薦制。從制定的有關(guān)條件和程序來看,還是從各科全面成績錄取的,我由此產(chǎn)生如下反應(yīng):這些優(yōu)秀生不被推薦也一定能考上大學(xué)。話說北京大學(xué)先行后,其他重點學(xué)校跟上,這樣又發(fā)展到若干個學(xué)校結(jié)盟提前招生。這讓我回憶起1950年我上大學(xué)時一個暑假考了四次,我考了華東區(qū)的復(fù)旦大學(xué)、華北區(qū)的清華大學(xué)和兩個私立大學(xué)。那個暑假我真是疲于奔命。思念至此,我不禁要同情那些90后的孩子了,當(dāng)然我估計有些教師也不得閑。
(2)實行學(xué)位制。從1978年開始實行研究生培養(yǎng)和學(xué)位制也是一大進(jìn)步,因為我國過去是沒有學(xué)位制的,能招研究生的學(xué)校為數(shù)很少,我知道的是清華大學(xué)。在前30年學(xué)習(xí)前蘇聯(lián)培養(yǎng)相當(dāng)于今天碩士生的“副博士生”的制度,可惜當(dāng)年北京大學(xué)西語系招的副博士研究生據(jù)說不了了之。第二個問題是學(xué)制太長,北京大學(xué)奉行碩士三年、博士四年的學(xué)制,似乎與國際上一至兩年的學(xué)制有些脫軌。再一個問題是有的碩士點和博士點發(fā)展過快,如有所學(xué)校剛評上博士點在第一年就提了十位博士生導(dǎo)師,有的學(xué)校翻譯專業(yè)一年招了100名碩士生。與此同時,更多學(xué)校使勁申請碩士點、博士點,為本校、本專業(yè)爭取榮譽。我看這也太為難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了。
(3)重視大學(xué)英語教學(xué)。這30年中高校的大學(xué)英語教學(xué)受到重視,發(fā)展也快。學(xué)生也很重視,學(xué)英語特別積極,以至于北京大學(xué)召開校學(xué)術(shù)委員會時,文理科系的系主任抱怨他們的學(xué)生進(jìn)校后不好好學(xué)習(xí)自己的專業(yè),整天捧著一本英語書。由于四、六級考試,也由于有的學(xué)校成績優(yōu)異,便出現(xiàn)大學(xué)英語是否一定必修的問題。有次,我遇到一位朋友的孩子,她說清華大學(xué)只讓她每周聽兩個小時的課,她只好花錢去新東方聽課了。對此,有的學(xué)校為程度高的學(xué)生開設(shè)各種外語選修課值得推廣,也能為外語教師開辟英雄用武之地。與此相關(guān)的問題是一些大學(xué)把專業(yè)英語和大學(xué)英語分得太死,教師間相互很少通氣,不利于教師的發(fā)展。在這一點上,教育部讓一些英語專業(yè)的教師參加“大學(xué)英語教學(xué)指導(dǎo)委員會”的工作是英明之舉,盡管這是單向的。話又得說回來,這里需要掌握自愿的原則,畢竟有的專業(yè)英語教師或覺得大材小用,或怕影響自己的科研而不愿教大學(xué)英語,而有的大學(xué)英語教師怕累不愿從事英語專業(yè)的教學(xué)。以我個人為例,1980年末,學(xué)校的副教務(wù)長約我談話,說為了加強大學(xué)英語,希望我重點抓好大學(xué)英語,上大學(xué)英語的課,與大學(xué)英語教師一起“滾打摸爬”。我強調(diào)作為系主任既要管行政工作,還得給研究生上課、做導(dǎo)師,實在顧不過來,而且我的年齡已近60了,無此精力,不能把我當(dāng)部隊的連排長使用。這次會談不歡而散。現(xiàn)在回顧往事,實在有愧。不過,退休后我還是關(guān)心大學(xué)英語的工作,支持他們的教材編寫和培訓(xùn)工作,將功贖罪。
(4)師資隊伍的改造。改革開放初期在教師隊伍力量不足、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教育部執(zhí)行“請進(jìn)來,派出去”的政策解決了很大問題。即使今天外語教育發(fā)展了,仍應(yīng)奉行這個政策。這保證我們能向國外的專家取經(jīng),在人才培養(yǎng)上與國際接軌。除派遣教員出國進(jìn)修外,通過國內(nèi)外高校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養(yǎng)從根本上實現(xiàn)了外語師資隊伍的改造。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許多外語教師只有本科學(xué)歷,教大學(xué)英語的有不少是原來的俄語教師改行教英語。發(fā)展到今天,許多學(xué)校進(jìn)人時,求職者如果沒有博士學(xué)位很難進(jìn)入英語專業(yè),沒有碩士學(xué)位很難接收為大學(xué)英語教師。這里有一個認(rèn)識問題。有的人認(rèn)為有博士學(xué)位的人不一定比無博士學(xué)位的人教得好。這種情況不能說沒有,但從整體來看,一個學(xué)校教師隊伍中有博士、碩士學(xué)位者多還是比少強,這多學(xué)的幾年不是白費的。
(5)教學(xué)與科研相結(jié)合。在前30年有一種傾向使高等學(xué)校走了彎路,那就是學(xué)了前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后,把教學(xué)和科研分家。在我國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大學(xué)主要從事教學(xué),科研基本上單純地讓中國科學(xué)院和隨后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去搞了。以北大為例,像錢鐘書、羅念生、卞之琳、馮至等權(quán)威專家都離開北大了,剩下的教師只是教書。由此又引發(fā)另一個問題。教師中如果科研搞得多成了“一本書主義”和“只專不紅”的典型,要批判,“拔白旗”。我的老師李賦寧先生就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拔過白旗,在文化大革命中進(jìn)了牛棚。回顧這樣一段歷史,我們才能深刻領(lǐng)會今天的教師既搞教學(xué),又搞科研這樣的好日子多么不容易。雖然人們對某些科研成果質(zhì)量不高或抄襲現(xiàn)象有意見,這終究不是主流。
在總結(jié)這30年所取得的成績和對一些問題摸索其解決方案的基礎(chǔ)上,我相信未來的30年中,我國的外語教育將會有更好的發(fā)展。
* 本文為胡壯麟先生在今年4月由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和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聯(lián)合舉辦的“全國首屆語言研究和外語教學(xué)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本次發(fā)表稍作了修改。——本刊編輯部
注釋:
① 《中國外語》2009年第5期5-9頁,收入莊智象主編的 《中國外語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論壇》,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
② 《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1985年第2期14-18頁。
2011-04-21
胡壯麟(1933-),男,教授,博導(dǎo),研究方向:國外語言學(xué)理論、功能語言學(xué)、語用學(xué)、文體學(xué)、語篇分析、語言規(guī)則、英語教學(xué)法、符號學(xué)、認(rèn)知與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