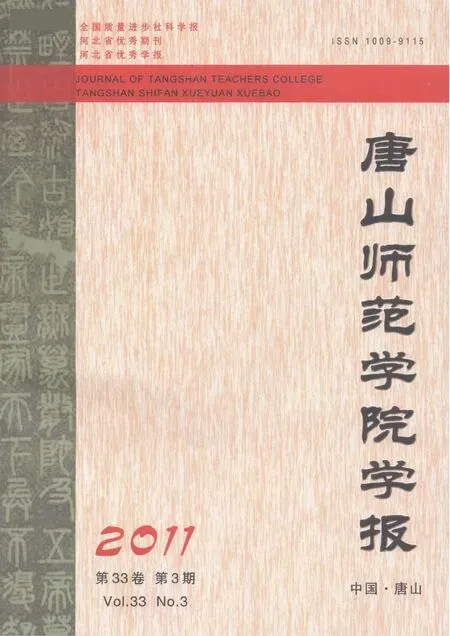張悅然論
喻曉薇
(武漢工業學院 人文系,湖北 武漢 430023)
張悅然論
喻曉薇
(武漢工業學院 人文系,湖北 武漢 430023)
本著對一個有潛力的文學新人負責的態度,細讀其文本,將其置于文學史座標系中來考察,會發現張悅然的小說屬于主觀型創作,詩化小說;其小說存在明顯的唯美主義追求,且充滿魔幻與靈異色彩;從女性文學角度來看,其作品是典型的女性文本,具有女性的陰柔極致之美。
張悅然;詩化小說;唯美主義
一直以來,張悅然作為創作者的意義只被視為歸屬于“80后”、青春文學這樣群體性存在的意義中。而在許多持文學是“成人的事業”[1]的研究者看來,“80后”、“青春文學”只是“流行一季的時令水果”①,其創作就文學價值本身而論相當小兒科,不值一提。于是,張悅然作為創作個體的個性和價值在人們對“80后”、“青春文學”不以為意的態度中被忽略。
且勿論這樣的文學觀是否合理,單就將一個有個性有潛力的創作個體貼上“80后”、青春文學的標簽,淹沒于群體中的做法本身而言就是相當隨意和不負責任的。持這樣觀點者恰恰鮮有對張悅然的小說進行認真研讀,大多先入為主,憑借從一些渠道獲得的印象、觀念,對其文本進行有選擇有針對性的閱讀,由此對張悅然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大加撻伐。如聲討其創作小資情調傾向,將其命名為小小資文學[2]。再如聲討其創作“經驗匱乏”、“病態冷漠”、“無歷史擔當,無現實意義,無理想追求”[3]。
勿庸置疑,張悅然是屬于“80后”這個代群,其創作題材也多是取自于自身的青春經驗,因而其作品也有一些屬于這兩個不同標準劃分的群落的特征。但作為“80后”迄今為止最為優秀和最有前途的代表②,張悅然作為一個創作個體的價值已逸出“80后”寫手的群體性意義層面。如果僅止于從“80后”和“青春文學”的層面來泛泛而論其創作,這樣的研究只能算是相當淺表層次的。
據此,在進入張悅然的文本前,本文將稟承對一個有潛力的文學新人負責的態度,懸置已有的對張悅然創作的種種結論和看法,以還原現象的學理態度,對其全部創作文本進行細致研讀,力圖深度開掘張悅然的小說世界。
一、主觀型創作——詩化小說
一般而言,文學史上有兩類氣質的小說家和與之相對應的創作:一類作家主體自我無限“縮小”,眼光外擴,熱衷于觀察、描述外部客觀世界,講述別人的故事,我們稱之為外向型創作或客觀型創作,比如以社會剖析小說聞名的茅盾就是典型的外向型作家;一類創作主體自我意識強烈,眼光向內,關注自身心靈世界,即使是講述故事,描寫外在于主體的環境氛圍都習慣于將其浸透在主體的情緒、心理中,我們稱之為內省型創作或主觀型創作。這一類作家的代表有創作出了系列“自敘傳抒情”小說的郁達夫,以對故鄉童年往事抒情而著稱的沈從文、廢名等等。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悅然作為創作主體的氣質類型顯然屬于后一種,其小說是典型的主觀型小說。翻閱張悅然的作品,從“新概念”時期的《陶之隕》,到留學新加坡時期的《葵花走失在一八九Ο》、《十愛》、《紅鞋》、《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及至近期的《誓鳥》,我們發現,作者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在反反復復、從不同角度講述一個少女的情緒體驗和經歷(尤其是前者——情緒體驗,而后者——經歷或故事性的成分常常是融化在這種情緒體驗中的)。這個少女在文本中常常是以“我”或“她”的形式出現,有時也會化身為“他”或“它”③,不變的是青春期的女性情緒、心理特質——感性、細膩、敏感,對某些形式細節的酷愛乃至于沉迷,耽于想像,富于夢幻和藝術氣息。不必說《陶之隕》、《黑貓不睡》、《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這樣的故事中有與創作主體身份年齡氣質相仿的少女主人公的小說,即便是在她為數不多的欲突破少女視角的試驗性小說中,我們也能夠找到這種少女心理特質的印痕。短篇小說《船》故事的主體部分是一個中年男性“我”對寶寶講述20年前殺妻然后趨車去海邊毀尸滅跡的經歷。在“我”對自己把尸體運到海邊,載入白木船并推向大海深處的男性視角敘述中,穿插跳躍在情節間并推動情節行進的是對卡車、公路、懸崖和海邊等環境氛圍的相當篇幅的描述,而這種描述浸透了詩性眼光,散發著女性氣質:
雜草在這片熱帶地區異常茂盛,它們從根部就緊緊地糾纏住花朵,像是在求歡[4,p72-74]。
海在一個黃昏的雨水里輾轉反側。這是一片很少被打擾的海,她在多數時候可以隨時進入夢鄉。她進入夢鄉的時候,海潮看來并不強大,可是迂回曲折,零星的夢魘星羅棋布。她非常喜歡在下雨的時候睡過去,她讓她的波浪任由兇悍的狂風雨水擺布,她喜歡她自己看起來更加具有母性的溫情。[4,p101-102]
李子紅色的裙子在海水里像一塊粘稠的血跡一樣氤氳開來。駛向海中央的時候,船忽然像獲得飛行的鴿子一樣快樂。其實礁石有最柔軟的懷抱,你們誰也不知道。[4,p103]
我們有理由將這看作是作者欲突破主觀型敘述視角所做的一次不成功的試驗。張悅然是那樣迷戀這種夢囈似的女性化敘述情調,以至于不惜一次次從男性視角下逃逸,滑向她所熱衷也是最擅長的詩意化的少女視角。這恰恰從反面證明了張悅然無法走出她主觀個我的情緒心理世界。
這誠然是一種局限,但從積極面來看,對于一個青年作家而言能把自己內心世界演繹到極致何嘗不是一種風格。沈從文在創作中始終糾結著湘西情結,郁達夫執著于書寫“于質夫”們的世界,在文學史上都獨樹一幟。
與主觀型創作相伴生的是小說的詩化特質。張悅然小說不以故事情節取勝,亦不以人物取勝,位居小說中心的是夢幻氣息十足的情緒、情感或虛化的意念。有時這種獨白式或傾訴式的抒情縱貫了整個小說,而故事情節則被打散成碎片點綴于其中,并且這些碎片情節也被氤氳在情緒、情感的霧氣中,變得極淡。譬如《領銜的瘋子》、《心愛》、《赤道劃破城市的臉》、《痣愛》、《這些那些》這些紀實性較強的小說根本沒有一個人物或完整的事件貫穿始終,全篇彌漫的皆是對過往的親情友情愛情的緬懷與眷念,從某種角度看就是抒情散文或詩。而在那些有完整情節和縱貫始終的人物的小說中,我們也發現夢囈似的情緒情感或意念占據了突出的位置,并成為推動情節進展的重要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篇小說《誓鳥》。小說構筑在遙遠而龐大的歷史時空背景上——明代大航海時代,從中國大陸跨越南太平洋的幾大島嶼。作者采用倒敘、插敘、多視角手法來講述,力圖構成一種錯綜復雜、磅礴大氣的厚重感。其實細讀文本,情節很單純:中國少女春遲遠嫁南洋,遇海嘯喪失記憶。為了找回記憶和愛情,她走上了搜集貝殼,從中尋找藏有自己記憶的那枚貝殼的艱辛旅程。單憑著找回記憶這個意念,她經歷了身體殘缺、生育以及牢獄之苦,最終成為了一個擁有無數記憶的“最富有的人”。小說情節的根本淵藪來自于一個神話傳說——丟失的記憶可以從貝殼中找回:“在南洋一些土著部落里,人的記憶被視為比生命更可貴的東西,它們可以脫離肉身存在。更有一些傳說,認為貝殼里藏著記憶。”[5]春遲對記憶的執著追尋成為小說主要情節前進的根本動力,主宰著小說的是對一種超離于世俗生活之上的虛化的精神追求。小說骨子里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屬詩的。
二、唯美主義文學——魔幻與靈異因子
他們看到一個稚氣未脫的美貌少女的身邊堆滿了肢解的動物,擰斷脖子的雞,掏干凈五臟的麻雀。還有雞血寫下的字,插滿骨頭的雪堆。她手上還拿著巨大的鏟子,鏟子上有慢慢凝結的動物血液。因為有些冷,她的臉蛋凍紅了,宛如一簇愈加旺盛的小火焰[4,p207]。
這段文字是張悅然作品中引用頻率較高并且得到質疑較多的。質疑焦點集中在以下兩點:其一,這種冷酷血腥的描寫具有非道德化傾向;其二,小說并未揭示少女病態行為的形成根由,仿佛天生如此,所以這種描寫是封閉性的,沒有現實指向性。
暫且懸置對這種描寫傾向的褒貶,筆者認為這種非道德化和沒有現實指向性的封閉性特征正是唯美主義的表征。唯美主義是19世紀中后期風行于西方的一股文學思潮,其重要代表是英國作家王爾德。他信奉藝術至上的純藝術理論,聲稱自然和生活是丑陋的,唯一美只在于藝術,藝術是高于一切的美,并且主張藝術是非功利、超道德且純形式的。《紅鞋》中的女孩的特征是冷和熱的截然對立:一方面對世間一切的冷漠甚至于冷血,冷血到對殺害自己母親又養育自己成人的殺手養父無動于衷,既沒有愛也沒有恨。另一方面,熱衷于美的形式,樂此不疲地制造新奇刺激的行為藝術,諸如將一只白貓拔光牙齒,五花大綁,再刷上花汁,將它變成紫紅色;一次次從養父身邊逃走,制造被人綁架的假相,然后再等養父籌足錢找到她,將悠然沉醉于新的美的場景制造中的她一次次地“贖回”……。這簡直就是托身在中國當代的“莎樂美”。這樣的人物形象在中國新文學中是極其罕見的。
再細讀張悅然的小說,我們發現唯美主義傾向的確非常普遍地存在于張悅然的作品中。幾乎她所有小說都活躍著一些藝術家或具有藝術氣質的人物:他們執著地追求藝術或某種美的理想,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惜自毀或毀掉他人;但是,他們的追求和由此生產的自由精神與世俗生活又是格格不入的:在世人眼里,他們行為怪異,是瘋子。譬如,《水仙已乘鯉魚去》中天才作家叢薇狂熱追求藝術,向往自由生活,但在現實生活中屢屢受挫,失戀、酗酒、吸毒、早產,以至瘋癲,最后縱身大火。《葵花走失在一八九〇》中的文森特是油畫《向日葵》的作者——19世紀的荷蘭畫家梵·高的化身——那個畢生獻身藝術患有精神病的藝術家。《誰殺死了五月》中少年成名的少女作家為追求“文學深處的桃花源”離家出走,在一個江南小鎮邂逅攝影師三卓,兩顆追求藝術的心靈交匯,碰撞出火花,他們迅速相愛并發生關系,然而為了維護各自藝術追求的完整性,女孩再次出走離開男人……張悅然通過這些藝術家或具有藝術家氣質的人物的追求構筑了一個絕少人間煙火氣息的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不指向現實,而指向藝術和美。
對美的追求與倫理道德追求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當在追逐美的道路上走入極端深處時,就往往會置現實社會的倫理道德于不顧,產生非道德化傾向。所以唯美主義與去道德化傾向往往唇齒相依。這也正是人們不明白張悅然小說中何以存在“虐酷”傾向的根源所在。
唯美主義是五四時代隨西方眾多思潮一起涌入中國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產生重大影響。但是由于中西方國情不同,唯美主義傳入中國后產生很大變異,與原盛行于西方的唯美主義有很大區別。學者王光東在《美的誘惑與變異——中國新文學中的唯美主義》一文中指出:“……他們(中國現代作家)接受唯美主義的思想時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誤解中發生了變異,把美與救世救國聯系在一起,極力強調美的社會功用,而不似王爾德那樣主要地把美作為一己的享樂。換句話說,在王爾德那里他所要求的是要生活模仿藝術,而在中國現代作家那里所要求的則是以藝術來改造和美化社會,同時反抗社會對自我的壓抑。”[6,p105]這就使其作品中的唯美追求具有極明顯的現實指向性。而中國現代作家“對現實時代精神的重視,又使他們以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亦即善的力量,凈化了唯美主義作品中所謂‘非道德’的肉體享樂的內容,表現出他們在美的追求過程中對于‘善’的重視。這種轉化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中國濃重的實踐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卻也在無意中淡化了自己的個性強力意志。”[6,p106]事實上,由于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制約和中國人文傳統中的強大實踐理性精神影響,從建國以后一直到80年代,在中國都沒有產生純粹的唯美主義創作。
與前輩作家相比,許多“80后”作家們的成長環境倒是更接近于西方唯美主義思潮產生的土壤。他們生長在改革開放后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城市,物質條件的優裕,更容易導致他們精神追求的純粹性;而全球化的成長背景使他們更易于與西方思想接軌。張悅然毫無疑問就屬于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所以有理由相信,張悅然小說中唯美主義追求是相對比較純粹的,是更接近于西方唯美主義思潮的。這樣的唯美主義文學也使中國文學的唯美主義追求更多地具有了文學自覺的價值。
唯美主義者既然主張最高的美不存在于現實中,只存在于虛擬的藝術中,當然就會用一切非現實主義的手法,如想象夸張變形等虛構手法來構筑這個超凡脫俗的世界,這就是王爾德所謂的“說謊”的藝術。我們看到,有著超凡想像力的張悅然把這“說謊”的藝術操練得那樣的飛揚靈動。在她筆下,幽靈飄忽游蕩,自由來去,去人間尋找他們生前的戀人(《跳舞的人們都已長眠山下》、《二進制》);鬼魂的頭可以從身體上分離,飛行于夜空中,象鳥一樣棲息在樹枝上(《宿水城的鬼事》);記憶吸附在貝殼里,被靈敏的手觸摸閱讀(《誓鳥》);一小女孩心口疼痛,另一小女孩也同時感知(《櫻桃之遠》);一株葵花愛上了畫家,變成一個女子追隨心愛的人直到死(《葵花消失在一八九〇》);小白骨精一根根抽出身上的雪白骨頭奉獻給樂師丈夫創造世界上最偉大的豎琴(《豎琴,白骨精》)……或從經典童話中吸取養分,或從中國民間神話和鬼怪故事中尋找資源,或從靈異電影中激發靈感,加以自己非凡的想像力,整合、創造,所以呈現在張悅然小說中的世界是唯美的,又富于魔幻與靈異色彩的。
三、女性文本——陰柔極致之美
說到當代的女性文學,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在寫作中作家性別意識淡薄,以無性別化的中性姿態存身于文本中,這種女性寫作姿態普遍存在于1990年代私人化寫作、身體寫作出現在文壇前,比如鐵凝、王安憶、方方、池莉等都是以中性化寫作著稱的作家;還有一種是在寫作中,作家慣于從女性獨有的區別于男性的心理特質出發,以女性的眼光描寫女性獨特的經驗、心理,因而其文本呈現為突出的女性化特質,典型代表是林白、陳染。
在一篇訪談中,張悅然曾坦言對林白作品的共鳴:“另外一類作家或許作品并不完美,或許從未被那么多的讀者關注,卻格外地打動我,因為她的作品中有我特別關注或感同身受的成分,比如林白,我對她的作品相當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強烈的畫面感,作品中有許多夢幻般的超現實場景,她的這種‘女性寫作’說出了好多女性感受。”[7]或許是受林白的啟發,或許是兩人寫作氣質不謀而合,總之林白的“女性寫作”對張悅然的影響顯而易見。但比起林白等女性前輩們躲在帳中、關在房中的女性言說方式,張悅然顯然更多了幾分坦然,她在小說中毫無避諱地揮灑著她身為女性寫作者的優勢:長于直覺感悟,善于體察細節,關注內心情感遠超過外部世界,富于夢幻性的傾訴直白式的言說方式,敘述結構上的詩化散文化特征,語言的形象性和畫面感。當然這樣極端女性化的寫作姿態也造成另一面的缺失,譬如論者經常詬病的對駕馭宏大場面的力不從心,小說結構零散化,缺乏邏輯性,視角單一。這也正是女性文本的一體兩面了。
這樣的筆致下繪就的世界,一如張悅然在一篇小說中所寫到的:“我承認我一直生活得很高貴。我在空中建筑我的玫瑰雕花的城堡,生活懸空。我需要一個王子,他的掌心會開出我心愛的細節,那些浪漫的花朵。他喜歡蠟燭勝于燈,他喜歡繪畫勝于籃球,他喜歡咖啡店勝于游戲機房,他喜歡文藝片勝于武打片,他喜歡悲劇勝于喜劇,他喜歡村上春樹勝于王朔。”[8]在這個執拗地將籃球、游戲機房、武打片、喜劇和王朔等堅硬的男性化事物拒之門外的“玫瑰雕花的城堡”中,張悅然精心地構造著她溫柔綿軟潮濕感性的少女世界。這是一個純粹女性化的世界,唯一準入的男子——她心愛的王子,是水草般的陰柔,睫毛上粘著薔薇花粉,干凈得沒有影子(見張悅然小說《毀》,她寫道:影子是人間的塵垢結成的痂)。這也是一個圣潔的靈的世界,少女和她的天使王子因為對藝術對美的共同追求而相愛,她們的愛情是清潔的精神之愛,肉身之欲是令人卻步的。
這個陰柔的世界又具有一種極端偏執的特質。這主要源自于女性主人公身上的一種執著精神追求。這種精神追求往往是愛情。她的許多小說,比如《霓路》、《豎琴,小白骨精》、《葵花消失在一八九〇》……都隱含著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的故事內核:女孩為了心愛的王子,心甘情愿地追隨之,無私付予,甚至可以付出生命。而且這種付出不帶任何勉強,正如珍妮對皮諾曹所說:“皮諾曹,我現在終于懂得愛情的真諦是什么了。是甘愿。人一旦甘愿地去愛一個人,就會萬分投入地去為他做所有的事情,并且感到幸福,永遠也不會后悔。你不覺得這樣的情感很美好嗎?”[8]深入地看,與其說是少女們為她心愛的王子而付予,勿寧說她們為自己的愛而付予。她們享受自己的這種情感,無關乎男性是否同樣施予愛;她們享受為自己的情感無私付出的過程,無關乎結果如何。而她們的生命意義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彰顯。所以一旦她們認定她們生命中的男人時,便義無返顧地奔過去,奔過去,沒有絲毫猶疑……正如一部女性電影所傳達的思想:“我愛你,與你無關。”這樣的主題在張悅然的近作《誓鳥》中得到了更充分地展現。女主人公春遲喪失記憶后,遇到她的王子——駱駝。駱駝只以一個小小的藉口便輕易拋棄了她:“因為你把從前的事都忘了。我待你的好,我們有過的好時光,你都不記得了。這在我看來是不能原諒的事。”于是為了駱駝給出的那個虛無飄渺的承諾——尋找到記憶再來找他,春遲踏上了漫長的追尋記憶之路。她刺瞎了雙眼,鉗掉了指甲蓋,走遍南洋搜尋貝殼尋找記憶,什么也阻擋不了她的腳步。實際上駱駝的愛情、駱駝的承諾只是一個契機,在春遲追尋記憶的過程中,它淡化到幾乎沒有,而彌補缺失的記憶,尋找完整的生命,最終獲得生命的意義,這才是春遲所有極端行為的內在根源。
[注釋]
① 2006年,在《誓鳥》首發會上,張悅然曾宣稱:“希望媒體不要再把我歸類于‘80后’,我的文學已經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學的樊籬,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時令水果,這部作品正是我向青春告別的成年禮。”
② 2005年,張悅然獲得由人民文學社主辦的“春天文學獎”。2006年,她的長篇小說《誓鳥》并被評為“2006年中國小說排行榜最佳長篇小說”,標志著她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由一名“80后”寫手向主流純文學作家的轉型。2007年5月,張悅然簽約北京作協,正式成為一名專業作家。撇開文學以外的因素不計,張悅然已成為“80后”這個群體中走出的成就最斐然、最有潛力的一位。
③ 前者如《船》,后者如《殘食》中的魚妻、《宿水城的鬼事》中的無頭女鬼、《堅琴,白骨精》中的小白骨精。
[1] 張檸.青春小說及其市場背景[J].南方文壇,2004,(6)∶20.
[2] 王長國,葉祝弟.小小資文學的青春地圖[J].名作欣賞, 2006,(6)∶58.
[3] 趙靜.冷眼閱讀張悅然[J].山東文學,2006,(2) ∶72-74.
[4] 張悅然.張悅然文集∶晝若夜房間[M].濟南∶明天出版社, 2007.
[5] 張悅然.誓鳥[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14.
[6] 王光東.東岳論叢[J].1997,( 6).
[7] 張悅然.寫作只為稀釋寂寞[N].中華讀書報2004,(8).
[8] 張悅然.張悅然文集∶霓露[M].濟南∶明天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校對:任海生)
On Zhang Yue-ran
YU Xiao-we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China)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 potential new hand, perusing Zhang’s texts, and studying them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literary history, we will find that Zhang’s novels are subjective writings, poetic novels; there is evident aestheticism pursuing in her novels, and full of magic and super natural colors; from feminist literature, her novels are typical female texts, full of the beauty of extreme of feminine.
ZHANG Yue-ran; poetic novel; aestheticism
2010-12-09
喻曉薇(1974-),女,湖北武漢人,碩士,武漢工業學院人文系講師,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批評。
I210.6
A
1009-9115(2011)03-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