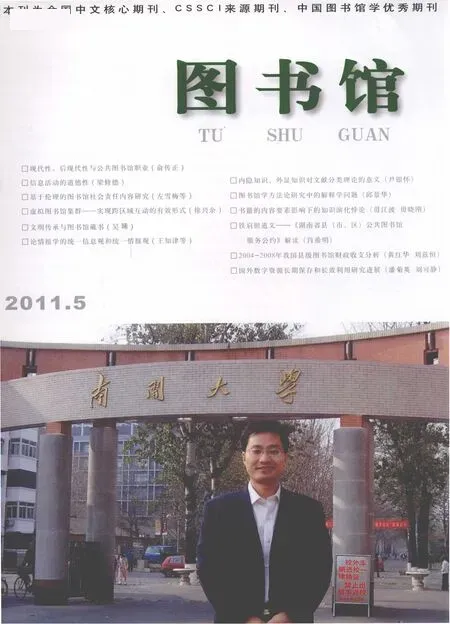大道至簡——也談圖書館的本質
盧士樵 李 萍
(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 廣東珠海 519085)
《圖書館》2010年第6期刊發了山東建設大學圖書館郝朝君等四人的文章《圖書館的本質:科學發展的工具與基本方法——兼與叢全滋同志商榷(以下簡稱“郝文”)》。隨后,本人閱讀了大連工業大學圖書館叢全滋在《圖書館雜志》2009年第2期上發表的論文《圖書館的本質: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兼與馬恒通先生商榷(以下簡稱“叢文”)》,河北師范大學圖書館馬恒通發表于《圖書館》2007年第1期的《知識傳播論 -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以下簡稱“馬文”)》。本人認為“叢文”將圖書館的本質描述為:“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是完全正確的,是對“馬文”的更正和補充,對圖書館本質更具體、更準確的揭示。而“郝文”的觀點卻顯得有些浮躁和寬泛,不切合實際、不準確、不具體、不嚴謹。本文對以上三家觀點談一點自己的認識,與相關作者共同探討。
1 對“叢文”圖書館本質的看法
“叢文”認為圖書館的本質是“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筆者基本認同,并提出下列分析以為補充。
1.1 館藏文獻是圖書館存在的基本物質條件
文獻收藏是圖書館存在的物質基礎。信息環境下知識載體層出不窮,給圖書館館藏增加了新的內容,傳統的紙質文獻和新產生的電子文獻、虛擬文獻共同組成了新型圖書館的館藏,共同服務于讀者,這些館藏文獻就是圖書館服務于讀者的基本條件,也就是圖書館服務的物質基礎。筆者認為,“叢文”將“文獻收藏”作為圖書館本質的第一項,是完全正確的。
由于新型知識載體的層出不窮,大型數據庫的逐漸出現,使得當今獲取文獻的渠道越來越多,獲取速度也越來越快。相形之下,傳統的紙質圖書就顯得有些“落伍”,因此有人預言:在不遠的將來電子圖書將完全取代紙質圖書,同時虛擬圖書館也將完全取代傳統圖書館。這種理論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就有人提出來了。雖然美國計算機應用早于中國20年以上,但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出現以上種種取代痕跡,紙質圖書與傳統圖書館仍然服務于社會,沒有絲毫萎縮。事實上,在世界各國,所有的圖書館都是以紙質圖書為基礎的,紙質圖書不但是圖書館的物質基礎,更重要的,紙質圖書也同時是圖書館(包括實體圖書館和虛擬圖書館)的支柱。因為虛擬圖書館的數據庫是紙質文獻經過電子掃描而組建的,所以虛擬圖書館的存在也是以紙質圖書為支撐的。其實質是文獻載體的轉化過程。而數據庫在網絡的傳播,實際上只是紙質圖書傳播方式和過程的延伸和轉變而已。
從圖書館誕生之日起,圖書的外借和館內閱讀,就是圖書館的主要工作,讀者到館的目的也主要是館內閱讀或借出圖書。因此圖書館讀者服務的方式和圖書館建筑布局也是據此而設。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文獻形態的增加,圖書館閱讀供求形式和方法、手段也隨之發生變化,給傳統圖書館增添了新的活力。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能動搖傳統的紙質圖書在圖書館的基礎作用和支撐職能。
1.2 文獻傳遞是圖書館工作的最終目標
圖書館是為讀者服務的,而讀者到館的目的就是要獲取知識。不論是研究型閱讀、學習型閱讀乃至休閑型閱讀,皆是如此。而讀者獲取知識是通過自己對文獻的“閱讀”來實現的。因而圖書館能夠為讀者所做的工作,就是將具有相關知識的文獻交到讀者手中,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館員將相關文獻交予讀者手中,供讀者閱讀的過程就是文獻傳遞的過程。在文獻傳遞工作中,由于文獻載體和讀者閱讀要求的不同,從而產生了若干個不同的傳遞手段。如:圖書外借,館內閱讀,借助設備(如電腦)閱讀光盤,查閱下載網絡文獻數據,館際互借,定題文獻檢索和文獻原件的傳送,短期講座和文獻檢索培訓,通過電子郵件、電話、QQ、MSN、博客以及其他方式進行的咨詢服務和其他服務,等等。無論采用哪種方式,只要將讀者所需要的文獻交予讀者使用,就實現了文獻傳遞的目標。
1.3 揭示館藏與圖書館工作、圖書館學之關系
揭示館藏是圖書館進行文獻傳遞的前期工作和手段。揭示館藏包括:文獻的有序化,文獻檢索的有序化,揭示文獻內容,揭示文獻位置信息和傳授檢索方式,為讀者提供、印制各項宣傳品等。前面說過,收藏文獻是圖書館存在和工作的物質基礎,文獻傳遞是圖書館工作的最終目標。而揭示館藏就是完成文獻傳遞的前期工作。圖書館所收藏的文獻包羅萬象,囊括所有學科。圖書館要想實現有目的地、有選擇地傳送文獻,就必須將所有館藏文獻有序化,因此圖書館組成了各種部門負責相關工作,充分揭示館藏,以便使讀者查閱文獻有序、使館員向讀者推薦文獻方便快捷。
揭示館藏是圖書館學存在的目的和基礎之一。揭示館藏與圖書館學的關系本來與圖書館本質的討論沒有直接聯系,但是既然“叢文”和“郝文”都提到了這點,所以筆者也談談自己的認識。
有了圖書館,有了圖書館工作,也就產生了圖書館學。所以圖書館學從時間上說,要晚于圖書館出現的年代。圖書館工作給圖書館學奠定了“物質基礎”。沒有圖書館工作的實踐,就不會有圖書館學理論的建立,圖書館學的出現依賴于圖書館工作的實踐,同時,圖書館學的出現也是為提高圖書館工作水平,指導圖書館“理性地”進行工作。如果說圖書館學是“水”,那么,圖書館工作的實踐就是“源”,如果圖書館學是“木”,那么,圖書館工作的實踐就是“根”,是“本”。為了使包羅萬象的圖書有序,因此出現了圖書分類法;為了揭示圖書內容,建立圖書排架,目錄學應運而生;計算機應用于圖書館以后,出現了適用于計算機檢索的機讀目錄。總之,圖書館學是在圖書館工作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是指導圖書館工作的理論基礎,是圖書館工作經驗的理性表達。由此可知揭示館藏是圖書館學建立的基礎和動因之一。
綜上可知,“叢文”對圖書館本質的描述基本是正確的,用詞也基本準確。
2 “郝文”觀點和文辭分析
2.1 對“郝文”標題的看法
“郝文”標題為《圖書館的本質:科學發展的工具與基本方法》,顯然“郝文”把圖書館當成了科學發展的工具和方法。筆者認為:“科學”一詞內容相當寬泛,西方將“科學”定義為“自然學科”,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環境學等,而中國學術界將“科學”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那么“郝文”中的“科學”一詞所指何物不得而知。既然“科學”包含眾多的學科,那么,每一個學科都存在各自不同的研究工具和基本方法,不可能存在共同的工具與方法。如數學研究的知識工具是哲學和邏輯學,歷史學和文學發展的基本工具是文獻資料。如果要尋找科學發展的共同工具,就只有人的大腦了。同理,科學發展也沒有共同的基本方法,簡單說來,數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演算;物理學和化學、生物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和實驗;天文學中的天體物理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包括有實測天體物理、理論天體物理等。所以,科學發展也不可能有共同的方法。
2.2 “郝文”內容分析
2.2.1 “郝文”對“叢文”的否定
“探索圖書館本質必須用科學方法作指導”。“郝文”認為,“叢文”缺乏科學的方法做指導,因而對圖書館的認識只停留在感性直觀階段。這里所謂的“科學方法”指的是:科學的認識論、唯物辯證法和價值判斷原則。因此可以這樣理解:“郝文”認為“叢文”缺乏科學的認識論、沒有唯物辯證法思想作指導、沒有體現價值判斷原則。筆者發現“郝文”此處除一大通哲學形式的語句以外,沒有任何新意和實際內容,只是一些正確的廢話。
“文獻收藏說無法反映圖書館的本質”。“郝文”將館藏分為三個時代,通過分析館藏的時代性,用以證明館藏不是圖書館的本質。“郝文”認為,在知識與信息載體的緊缺時期,圖書館因交通不便而買書難,所以購買圖書是圖書館的主要工作。這是藏重于用的時期。在知識與信息載體的相對豐富時期,收藏并非圖書館所獨有,博物館也有很多的收藏。所以文獻收藏不是圖書館的特征。在知識與信息載體的分離時期,作者認為虛擬圖書館只有知識而沒有載體,所以知識是與載體相脫離而獨立存在的。這一分析表明:圖書館的收藏功能有弱化和被取代的趨勢,這種不穩定性說明,收藏無法擔當圖書館的本質。筆者以為知識與載體可以分離的認識顯然是錯誤的。知識與載體是永遠不能獨立存在的。就文字信息來說,知識是用文字來記載的,所以文字是知識的載體,而且是第一載體。而文字又是負載于紙張上的,所以紙張是文字的載體,是知識的第二載體。所以,知識有雙重載體。就語音信息來說,知識是用語音來記錄的,所以語音是知識的第一載體,而語音又是被負載于光盤(或類似的載體)上的,所以光盤是語音的第一載體,是知識的第二載體。在虛擬圖書館中,知識是負載于多種第一載體上的(文字信息;音、像信息;圖片信息等都各自有各自的載體),而眾多第一載體又負載于第二載體“數據庫硬盤”(服務器)上,所以,虛擬圖書館所傳播的知識仍然沒有、也不可能脫離載體而獨立存在。收藏是服務的基本條件。筆者認為,收藏文獻的難易程度以及收藏與服務工作的重心的轉移,不能動搖館藏文獻在圖書館工作的基礎地位和支柱作用。收藏工作困難時要收藏,收藏工作容易時仍然要收藏,沒有哪一個圖書館不收藏文獻只是個“空殼”。
“文獻傳遞說是對圖書館本質認識的退步”。這里,“郝文”認為“叢文”的“思維方式不科學”。筆者認為“郝文”的指責理論依據不足,其他不談,僅舉“郝文”批評“叢文”原話說明:“其次,文獻傳遞說伴有嚴重的實踐危害。業內人士認為,圖書館是老弱病殘的‘收容所’,這種認識的根源正是來自‘文獻傳遞’的思想……圖書館及其學科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雖然與業內人士對圖書館的本質認識不透徹有直接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圖書館以外人士對圖書館的偏見有關,而對圖書館的偏見往往又是在工作、學習、生活中從關于圖書館性質的耳濡目染及道聽途說開始的。”筆者認為,“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不是同一個事物,雖然它們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但也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圖書館學是一門學科,是為圖書館工作提供理論指導的科學。而圖書館是一個為讀者服務的機構。圖書館是由一項一項的具體工作組成的,圖書館學來源于圖書館工作,是圖書館工作的總結和抽象的結果,是指導圖書館工作的理論基礎。兩者不相等同。其他學科,自然科學學科如數理化、生物、天文以及社會科學學科如文史哲、財經、社會學等是直接研究和服務于社會第一線的學科,權且稱為“一線學科”,圖書館學是研究“文獻”的學科之一,而“文獻”又是“一線學科”的產品,所以圖書館學屬于“二線學科”。但是作為“二線學科”的圖書館學并沒有處在尷尬的境地,也并沒有被其他學科所歧視。至于認為圖書館是“老弱病殘的收容所”,這種偏見的存在,源于用人機制,也與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盡職與否以及能力相關聯,無關其他。
2.2.2 “郝文”有關“圖書館本質”的觀點
“圖書館是科學發展的工具”。“郝文”解釋如下:“圖書館通過文獻獲取方法的傳播,實現人類社會知識交流,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又是館藏充實的有源之水。”顯然“郝文”所說的“科學發展的工具”就是“文獻獲取的方法”。將文獻獲取的方法當成科學發展的工具,這種認識不但筆者不同意,相信大多數業內人士也不會贊同。
“圖書館是科學發展的基本方法”。“郝文”所列舉的內容包括:“圖書館傳播知識索取的方法”、“圖書館研究并不斷改進索取文獻信息的方法”、“圖書館提供科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圖書館的先進程度標志著科學發展的高度”。其中,“圖書館傳播知識索取的方法”和“圖書館研究并不斷改進索取文獻信息的方法”是“郝文”所謂的圖書館是科學發展的“基本方法”,指的就是“索取文獻的方法”,雖然分為兩條來敘述的,但是“知識索取的方法”同“索取文獻信息的方法”沒有原則性的差別。本質差別是他們是不同的事物,這些方法與科學研究的方法是不等同的。顯然。將“索取文獻信息的方法”同“科學研究的方法”混為一談,暴露了“郝文”作者學術常識的缺乏。
“圖書館提供科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郝文”認為:“圖書館提供科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是指讀者與研究工作者通過正確使用圖書館就可以使自己的研究課題得到解決的方法。”筆者認為:“郝文”中“讀者正確地使用圖書館”概指“找到正確、簡捷的檢索文獻方法”。但是無論檢索過程是否簡捷,得到文獻是否順利,文獻都不可能直接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使自己的研究課題得到解決。文獻只是解決科研課題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并不是說有了文獻,研究的課題就解決了。有了可供參考的文獻還必須要經過研究人員的分析、判斷與思辨,才能將文獻內涵轉化為新的知識。否則,文獻仍然只是文獻而已。至于“郝文”將“學科館員與研究人員之間的關系形象比喻為金牌教練員與金牌運動員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學科館員與研究人員之間的關系同金牌教練員與金牌運動員之間的關系是不等同的。只有導師和研究生的關系才同金牌教練員與金牌運動員之間的關系可比。
“圖書館的先進程度標志著科學發展的高度”。“郝文”并未詳加闡述,只講了圖書館對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綜上可知:科學發展沒有固定的、統一的模式,各學科皆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而這些研究方法是科學工作者科學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她們所付出的心血的結晶,與圖書館沒有任何直接的關系(不是說沒有關系)。所以“郝文”所說“圖書館的本質是科學發展的工具與基本方法”與事實不符,且詞意表達寬泛。
3 結語
全面閱讀“郝文”以后,筆者認為,“郝文”與“叢文”的觀點根本性的分歧在于:“叢文”認為圖書館的本質是“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郝文”認為收藏文獻是圖書館的基礎性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服務于讀者是圖書館的歸宿,是圖書館一切工作的目標所在。但是這些都不屬于圖書館的本質。而揭示館藏、給予讀者檢索文獻的方式方法才是圖書館的本質。“郝文”將“科學發展的方法(科學研究的方法)”同“文獻的檢索方法”混為一談,既不正確、也不科學。
此外,圖書館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高校圖書館在學校中的地位取決于圖書館所有工作人員的學術水平的提高、服務效益的提高,絕對不取決于“圖書館的定義”和對圖書館本質的“文字描述”。越是本性的東西,越是深奧的內容,其道理和規則卻往往越簡單,即所謂“大道至簡”。
以上是筆者理論探討的一孔之見,意在拋磚引玉,歡迎業內人士批評指正。
(來稿時間:2011年3月)
1.郝朝軍,圖書館的本質:科學發展的工具與基本方法,2010(6):35-37
2.叢全滋.圖書館的本質: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兼與馬恒通先生商榷.圖書館雜志,2009(2)
3.馬恒通.知識傳播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圖書館,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