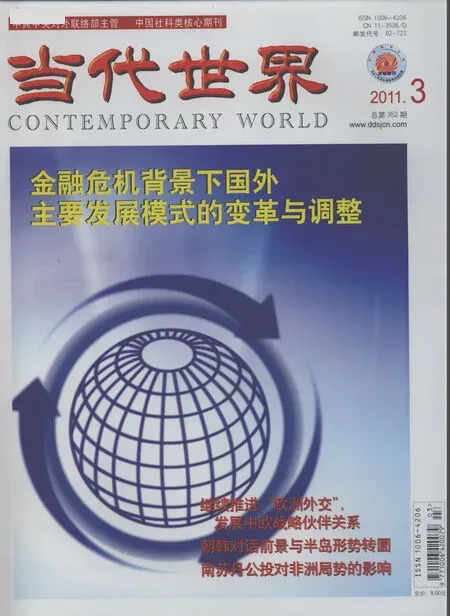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俄美能源政策調整
■ 李 興/文
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俄美能源政策調整
■ 李 興/文
能源是國民經濟的血液,是重要的國際戰略性資源。石油被稱為“黑金”,天然氣被稱為“藍金”。作為世界能源出口大國和世界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俄羅斯和美國對能源政策的調整,必將對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安全產生巨大的影響。
俄羅斯能源政策的新變化
普京在任時期,俄羅斯利用國際市場油價暴漲機會,大搞能源外交,一度獲取了大量財富。2008年,梅德韋杰夫上臺后,延續了普京的做法,空前重視能源外交。
梅德韋杰夫認為,對待能源問題,各方不僅應該從能源消費國的角度思考問題,而且還應該從能源生產和負責運輸國的角度考慮。所有國家,包括能源供應方和消費方,最終都要為能源價格和石油產品價格上漲付出代價,共同承擔責任和風險。能源市場的基本形勢比想象的復雜,對于像俄羅斯這樣的產油國尤其如此。如果俄羅斯只關注發展能源產業,長此以往俄羅斯的經濟將會退化,因此必須從保障經濟發展產業多樣化的角度進行投資規劃。
中亞地區石油天然氣豐富,因此梅德韋杰夫尤其重視對中亞的外交,希望中亞能與俄羅斯組成某種能源供應國的“俱樂部”,充分發揮位于俄境內的、蘇聯時期就已修成的油氣管道的主導作用。梅德韋杰夫還看好北極地區豐富的能源,他認為北極對俄羅斯具有戰略意義,開發北極資源是俄羅斯能源安全的保障,北極應當在本世紀成為俄羅斯原料基地。
除中亞地區之外,梅德韋杰夫還注重發展與中東、北非的能源合作。2009年7月,梅德韋杰夫訪問非洲,旨在通過加強能源合作簽署戰略協議的非洲之行,換來埃及、尼日利亞、納米比亞和安哥拉這些非洲最主要能源出口國的交相許諾。2010年5月,梅德韋杰夫訪問敘利亞和土耳其,簽訂能源合作協議。2010年10月,俄羅斯與阿爾及利亞簽訂深化能源戰略伙伴關系的協議。
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經濟的沖擊很大,尤其是油價下跌對俄能源企業打擊很大。為此,俄羅斯政府對內以多種手段減輕俄油氣公司負擔,維系、培育能源企業的生存力與競爭力,對外根據新的形勢調整能源外交策略,保護俄海外能源利益,提升能源大國地位。首先,協調與歐佩克的關系,提高對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力。其次,加緊醞釀成立“天然氣歐佩克”,謀求對國際天然氣市場發揮決定性影響。再次,借俄烏天然氣之爭凸顯俄“能源大國”的重要性,并推動國際油氣價格回升。2010年4月,梅德韋杰夫與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簽訂協議,俄給予烏方七折的天然氣優惠,以換取位于烏克蘭塞瓦斯多波爾的俄黑海艦隊基地租借期延長到2017年以后。最后,加快對歐油氣管道的建設與布局,減少對能源過境運輸的依賴,并加快開發中國、日本等東北亞市場。2010年中俄原油管道竣工。2011年新年,俄開始向中方供應原油。按照中俄“貸款換石油”協議,今后20年,俄每年向中國輸送1500萬噸原油。同時,俄還擴大與中亞—里海和非洲國家的油氣合作。
面對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的巨大沖擊,俄對于海外能源戰略的調整還是迅速而有效的。2009年1—7月,國際油價逐漸回升,從每桶42美元漲至64美元,2011年1月已經突破90美元。俄羅斯財政赤字低于預期值,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回穩。2009年9月,俄羅斯不僅成為世界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而且成為全球第一大石油出口國。2010年已實現了5%的正增長。這說明俄羅斯經濟雖然遭受巨大打擊,但仍然是世界能源體系中不可忽視的“巨頭”之一。

金融危機爆發后,奧巴馬視可再生能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發動機”。
梅德韋杰夫積極推動了《203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文件的制定,并于2009年在金融危機中通過。俄羅斯《2030年前能源戰略》與五年前通過的《2020年前能源戰略》相比,原戰略中的一系列主要指數都得到了重新審議。《2020年前能源戰略》謀求通過能源外交“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2030年前能源戰略》中劃分階段的主要標記內容都具有從克服危機向強化危機后發展的過渡性特點。《2030年前能源戰略》的戰略目標是,最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能源資源潛力,強化俄羅斯在世界能源市場中的地位,并為國家經濟獲得最大實惠。《2030年前能源戰略》指出,俄羅斯燃料能源部門將按三個階段發展,主要目標是從常規的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轉向非常規的核能、太陽能和風能等。
梅德韋杰夫認為,俄羅斯經濟眼下仍然依靠落后的蘇聯工業基地以及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家的威望和福利不能永遠依靠過去的發展成果”,因此他提出俄羅斯要建設“現代化”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以期減少對能源出口依賴,重點發展節能環保經濟。
美國能源政策的新變化
小布什時期,美國能源、軍工利益集團在國家政治經濟中發揮了重要影響,總統布什、副總統切尼等主要領導人大多與美國著名能源公司有緊密關系。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在中亞—里海—高加索地區大搞“顏色革命”,其中就有能源方面的重要考慮。布什還禁止美國企業在近海開采石油,主張開發北極資源。布什政府在國際上反對俄羅斯的能源外交,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
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任以來,對能源戰略進行調整,大力推行新能源戰略,希望通過發展新能源產業,振興陷入衰退的美國經濟,并把新能源經濟打造成美國未來經濟的新增長點。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奧巴馬意識到,過分依賴進口石油對經濟和國家安全都構成威脅,因此他提出了“新能源計劃”,啟動以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以優勢能源替代稀缺能源、以再生能源替代石化能源的新戰略,大力發展科技,保護環境和能源安全。美國還通過一攬子政策,對生物能源進行補貼,對有利于節能減排的消費行為進行稅收優惠。奧巴馬還積極推動《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該法案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美國對進口石油依賴、勾畫美國綠色能源藍圖。美國眾議院于2009年6月底以微弱多數通過了該法案。該法案的核心是限制碳排放量,通過設定碳排放上限,對美國的發電廠、煉油廠、化學公司等能源密集型企業進行碳排放限量管理。
2010年3月,考慮到油氣資源嚴重依賴進口使能源安全問題日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奧巴馬宣布部分取消在美國近海開采石油的禁令。此舉代表著美國對外能源戰略的變化,從高度依賴進口轉向進口和自產并重。2010年5月,奧巴馬又以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為由,敦促國會通過能源立法,以刺激美國替代能源發展,減少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并宣布美國暫停北極和近海地區的石油鉆探和開采。
奧巴馬的新能源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在未來10年內耗資1500億美元刺激私人投資清潔能源,幫助創造500萬個就業機會;未來10年內節省更多石油,節約石油量要多于目前從中東地區和委內瑞拉進口的石油總量;到2015年前,將有100萬輛美國本土產的充電式混合動力汽車投入使用;到2012年,保證美國人所用電能的10%來自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這個比率將達到25%;實施“總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計劃,到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的基礎上降低80%。
奧巴馬的能源政策有三個關鍵詞:安全、綠色、經濟。根據他的政策構想,美國將在可再生能源、節能汽車、能源供應、天然氣水合物、清潔煤、節能建筑等領域探索出一個利益最大化的創新戰略。美國表示愿意在清潔能源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
奧巴馬的能源政策核心是開發新能源、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他認為這樣可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催生一個全新的能源產業,增強美國的能源安全,“創造一個新的美國能源經濟”。
非洲的石油等礦產資源對美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目前美國進口的石油中有10%以上來自非洲,到2015年,美國從非洲進口石油將占美國進口總量的四分之一。2009年7月奧巴馬訪問加納,說明美國認識到了“非洲的重要性”。 據加納《the Statesman》報道稱,加納的石油儲量將可能超過蘇丹宣稱的50億桶,而與安哥拉并駕齊驅。緊接著,2009年8月希拉里又訪問了安哥拉、剛果和尼日利亞等非洲產油國。目前非洲最大的兩個產油國——安哥拉和尼日利亞,是美國在非洲地區的主要能源進口國。
俄美新能源政策比較分析
比較俄美的能源政策,兩國均重視開源、節能、發展新型能源,如核能,擺脫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并使能源出口與進口多元化,使能源供需平衡、穩定與可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氣候變化、碳排放等問題上兩國立場接近。兩國新能源政策的方向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受國內政治和國際形勢的影響,以及技術和資金的限制,兩國要實現既定的能源戰略目標并非易事。
俄美能源政策的不同點在于,美國是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進口國,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國之一,兩國在能源價格、能源安全、國際能源管道、能源格局等方面存在矛盾。美國支持修建繞開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管道,反對俄羅斯通過能源外交達到政治目的,反對俄羅斯獨自開采北極能源。兩國雖然都主張開源,但俄羅斯的主要目標是北極,而美國則考慮近海開采。俄羅斯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能源資源大搞能源外交,把能源作為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贏得大國地位。而美國能源新政策是以尋找新能源、清潔能源、生物能源為突破口,以獲取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國際道德的制高點。美國能源新政策重在能源質量改進,集約式創新。俄羅斯重在能源數量擴張,粗放式發展。俄美的能源政策可謂兩種不同的類型,在當今世界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相較于布什時期,奧巴馬的能源政策實現了某些超越。主要表現在,一是布什時期的重點在于石油進口地的多樣化和確保運輸通道的順暢,而奧巴馬則把重心放在了開發新能源方面;二是布什政府側重于提高傳統能源的能效,而奧巴馬政府則不僅關注節能問題,同時還注重減少能源污染;三是布什政府將發展新能源視為減少國際依賴的戰術目標,而奧巴馬政府則將其上升到戰略層面,關注新能源對于美國國際競爭力的長遠影響;四是布什政府為了眼前利益屈從于國內壓力而拒不簽署《京都議定書》,奧巴馬政府則表現出積極態度,選擇綠色能源作為突破口,通過“利己不損人”的方式來化解國際壓力,維護美國的國際形象。
相比之下,俄羅斯地域遼闊,能源豐富,在能源外交方面,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搞得有聲有色。俄羅斯現實主義色彩較重,比較傳統。當然,有油總比沒油好,但是,資源過于豐富有時會成為“上帝的魔咒”,獲得了財富的同時養成了不思進取的習慣,影響了創新精神和經濟結構的改革。梅德韋杰夫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發起了建設“現代化”創新型國家的倡議,試圖使俄羅斯擺脫經濟對能源出口的過度依賴,改變粗放型的“賣血經濟”結構,打破靠“油”吃飯的被動局面。然而,要想改變俄羅斯積重難返的能源結構,絕非一日之功,俄羅斯人要走的路還很長。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劉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