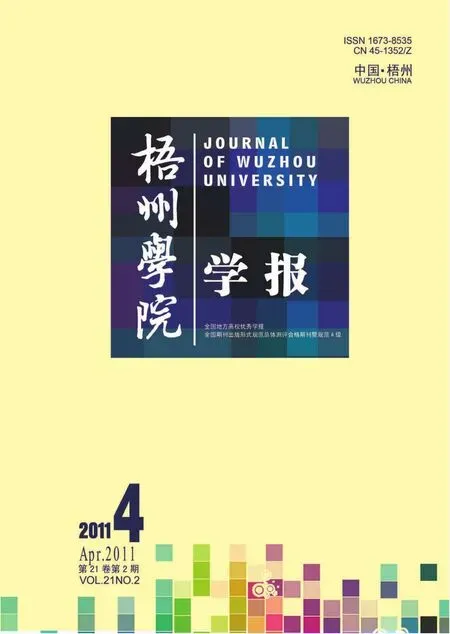論短信文學的后現代文化背景
趙 飛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37)
論短信文學的后現代文化背景
趙 飛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37)
中國當代社會轉型在某種程度上為西方后現代文化因子的飄入提供了深刻的社會現實背景與心理根源。短信文學在后現代文化的影子中是 “邊緣化寫作”所產生的 “隨筆文化”,或稱 “碎片文化”。無線通訊時代的 “無距離”使得短信對人們構成強迫閱讀,也加劇了后現代主義文學對深度模式的消解,成為一種交互性、臨時性、剎那性、偶然性的后現代詩學。短信文學是這一詩學的實踐文本。
短信文學;后現代;碎片文化;無距離
后現代主義作為 “文化生產過程和社會關系中某種深刻的裂變”[1],已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若隱若現的普泛開來。文學與短信發生激烈碰撞,火花激濺,孕育出短信文學這個文化新寵兒。這一文化新寵兒的發生與下述背景有著深刻的契合,即中國當代文化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中經受激烈振蕩,無可避免地發生一系列陣痛、裂變,并逐步滑入后現代文化語境。
一、社會現實與心理根源
可以說,經濟推動下的中國當代社會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為西方后現代文化因子的飄入提供了深刻的社會現實與心理根源。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一個現代人,曾經非常努力、有理想、滿懷激情,在那孤注一擲的奮斗里卻只有一個目標,只有一種單純的生活,在凝聚自己所有精力的過程中也只有一種充實的幸福。因為 “你可以沒有時間做所有的事情,但必須有時間做你最重要的事情”,這類對社會整體而言理性而勵志的格言,是教導人們心無旁騖地朝著目標、欲望的滿足進發,所以人們無暇也忘記應該培育豐滿的人性,課外閱讀、藝術欣賞等自覺的人文課程在緊張的闖蕩、拼打中早已是一種奢侈品。可是自然的性情已在暴虐的壓抑中日漸萎縮,心靈也在蝸牛般的生活殼里掙扎變形。當物質文明發達了,物質生活比較富足、安逸了,世俗的功名利祿滿足了,人們卻突然發現整個精神世界因缺乏必要的塑造、陶冶而只剩下一副干癟的軀干,無從支撐也無從消受那鋪天蓋地的物質消費時代所帶來的壓力。瘋狂享樂的背后是空虛,縱情發泄的背后是寂寞。在機械化的工業社會里,人本身也變成了一臺機器,每天無休止地運轉,停下來時卻越發感到如置身漩渦中般的競爭壓力,而鋼筋林、社會分工與個人空間的喪失造成銅墻鐵壁般的逼仄、壓抑、苦悶、無聊,也像寄生蟲一樣在蔓延,在咬噬著人們的精神。于是,在這個喪失了意義的世界中,“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離破碎的東西……人人都在狂歡,人人都在不顧一切地試圖遺忘、擺脫整一、理性所帶來的鉗制與沉重,玩弄碎片”[2]。這樣的生存狀態反映在藝術中,則是邁克·費瑟斯通所概括的與后現代主義相關的關鍵特征: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層次分明的差異消弭了;人們沉溺于折衷主義與符碼混合之繁雜風格之中;贗品、東拼西湊的大雜燴、反諷、戲謔充斥于市,對文化表面的 “無深度”感到歡欣鼓舞;藝術生產者的原創性特征衰微了;還有,僅存的一個假設:藝術不過是重復[3]。隨 “機”書寫的短信文學就是這樣碎片化、狂歡化地重復著的新興文化形態。
另一方面,作為世代生存于富有悠久農耕歷史下的中國人,卻又因襲著根深蒂固的傳統心理與情感。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中下游地區,沃野千里,灌溉便利,中國人民歷代依靠這優越的農業生產環境,辛勤耕耘,自給自足。歷代統治者奉行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政策,形成社會獨立的、封閉的農業經濟。“溫柔敦厚”、“謙謙君子”的仁義禮訓也讓中國人幾千年遵從著巨大的宗法關系。在農業型的經濟和宗法制的政治所形成的封閉保守體系中,人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對著小橋流水人家,追求著 “天人合一”的自然、內心和諧之境。山水環繞的地理條件和寧靜安謐的生活勞作滋養著中國人內斂、深沉、注重沉思感悟的傳統性情,骨子里透著以文傳情的內傾性。作為一種有距離的書信文體,短信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承載起對遠方他者的傾訴。這個遠方的他者,其實也是內心深處的自我。因為預設了一段距離,心靈反而獲得了空間得以敞開,這和現代生活熙熙攘攘的擁擠之勢是相關的。對個人空間的渴望逼迫壓抑的心靈急于傾訴,遼闊的遠方給這種心理找到了想象性安慰。 《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于是我們便能讀到這樣的短信文本:
我想有自己的生活/與他人的生活沒有牽連的生活/不被人窺視的生活/不是一言一行都被別人了如指掌的生活/我希望在自己的空間生活。
如此強烈的呼喊其實就是心里的聲音,那時候的手機就是一個對象,感應了內心的電波,轉化成屏幕上一行行的字。這樣的短信詩毋寧叫做手機詩,因為它并不一定要發送出去,只是從心里發送到手機上,它就完成了,也完成了自我苦悶的解救。可以說,手機就是現代人內心的一個緩存空間,它接納了人們有時候歇斯底里的呼叫、懶洋洋的自言自語以及不為人知的私密傾訴。倘或拾到一個手機,打開里面的收件箱、發件箱、存檔文件夾等等,總會看到一個繁復得讓人心跳的私密空間。
二、后現代的碎片書寫
短信文學在后現代社會的影子里,是文化身份兼融變動、文化思想與知識呈信息蔓延生長狀態的“感性——理性人”的書寫行為,即“邊緣化寫作”所產生的 “隨筆文化”,或稱 “碎片文化”。所謂 “隨筆文化”,就是指以隨筆話語為主體思考——表述——交際的文化話語場。它以后現代哲學為精神內核,以文化信息場為依托資源,以全球化為時空過程,以多學科知識、多元文化為打通延異的對象,以感性——理性的人文智慧為整合策略,以人人自由參與、直覺表述、率性表演、在過程中思考并獲得文化快感為書寫目的,以電腦并兼融多種媒介特征的書寫方式為其文本媒體,于是無結構主義、雜語并置、離題發揮便成了它的特征,這些也正是后現代的特征。關于后現代,利奧塔規定了兩個定義標準——其一是歷時態標準:后現代主義是不同于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一個歷史時期,它由60年代發生發展,將隨歷史而不斷地向后延伸。其二是共時態標準:后現代是一種精神、一套價值模式。它表征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論、解 “元話語”、解 “元敘事”;不滿現狀、不屈服于權威和專制,不對既定制度發出贊嘆,不對已有成規加以沿襲,不事逢迎,專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視限制打破舊范式,不斷地創新[4]。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又出爾反爾地回避 “天才”、“創造性”甚至 “作者”這樣的概念,宣稱作者、作品都已死亡,代替前者的是非中心化的自我,代替后者的是 “文本”。在后現代主義的詞匯里,“文本”指的是指稱而且能夠以概念化理解的任一藝術或社會的創造物。在這里,到處涌動著大范圍的、席卷性的文學參與。有趣味的、愉快的和民主的,對高級、低級藝術之間的對抗以及學院派的現代主義、精英主義構成了挑戰。他們倡導校園與流行文化和新的藝術形式。文學作品作為一種只能被專業人士理解的符號這一觀念被拒絕了,受到歡迎的是更好理解的、平民主義的寫作風格。他們唾棄精英主義,把 “高雅”和 “低級”的文化形式在美學上的多元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起來。伴隨著反對好戰性的革新和原創性,后現代作家具有諷刺意味地吸納了傳統以及引用拼湊的技術,主張兼容并包主義、詼諧的模仿,隨時抓住已經存在于身邊的材料,用拼圖的方法重新組合這些碎片。他們具有嬉戲心態,主要關注語言的構造和游戲,強調書寫的行為而非書寫出的文學。
貪官不怕喝酒難,千杯萬盞只等閑。
鴛鴦火鍋騰細浪,生猛海鮮加魚丸。
桑拿洗得渾身暖,麻將搓到五更寒。
更喜小姐肌如雪,三陪過后盡開顏。
這則短信改寫了毛澤東的 《七律·長征》,揭露了社會的腐敗現象,對貪官進行了辛辣的諷刺。這和 《詩經》中的 《碩鼠》對統治者的厭惡與揭露有異曲同工之妙,運用的都是充滿譏諷的言辭,譴責之情非常尖利。這種短信文本既是了解民情民愿的一扇窗口,同時也可以看出當下書寫對經典與神圣的顛覆。一首氣勢磅礴、格式高雅的七律 《長征》,被改寫得面目全非。長征中不畏艱難險阻的英雄氣節被轉型期社會的歪風邪氣替換,在一傳十、十傳百的短信閱讀中,受眾擁有的不再是叱咤風云的審美體驗,而是對社會猥瑣現象的心領神會。不過,“舊瓶裝新酒”的 “陌生感”也給讀者帶來了一定的驚奇和閱讀快感。
三、后現代的無距離性與瞬息性
電信時代實現了人類的通訊神話,真正取消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一條真誠的短信創造了“有距離的無距離”之審美距離,營造出物理空間的遐想與心理空間的貼近。民間的心理學認為,人在遠方比較容易得到原諒。千山萬水之隔,隱蔽了人在現實視野中的可視缺點,也促成了人心胸的開闊,造就了一定的距離美。但這距離在現代社會又不是無限而無可觸及的,只需輕輕捻動鍵盤,發送一條短信,瞬間便可抵達天涯海角的一方,在神秘的精神世界里與另一顆心靈發生碰撞。可以說,短信文學完美地實現了美學上的適度距離說。現代高科技使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距離被取消了,無論一個人走到哪里,只要攜帶手機,就可以被其他人找到。在這個時代,“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正在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5]。手機這一媒介,正在改變人類群體的整個生活方式,這種改變甚至是強迫性的。伽達默爾曾區分了后現代社會的三種強迫類型:重復強迫、消費強迫和輿論強迫,他說:“在消費強迫背后還有一種更為深層的強迫,我認為是最嚴重的強迫:輿論強迫。今天所有人都總是處于一種我們不可能避免的信息洪流之中……這種情況的后果就是輿論強迫,因為信息不是直接地,而是借助于其他手段傳遞過來,信息并非由我和你之間的談話傳播,而是通過有選擇的組織:報刊、書籍印刷、廣播電視。”[6]今天,短信也可位列其中。手機短信借助其自身的可復制性、便捷性和商業性對我們進行輪番轟炸的時候也構成了巨大的強迫性。你無法對手機的信息置若罔聞,你也無法判斷這條信息究竟是事務性的還是一條無關利害的文學性短信,它盯著你,敲打著你,迫使你最終作出回應。也許下一分鐘你的計劃、你的生活就將改變—— 一條短信可以在瞬間決定你接下來該去做什么。你無法預測明天將被呼向哪里,被要求做什么。你甚至不愿意拋棄手機——你的心情在那個郵票般大小的屏幕里頓跌谷底,或者突然哈哈大笑。無論是紙媒書籍還是網絡比特,我們都有打開或關閉的自由權,但是手機短信卻不行,我們擔心會錯過一條重要的事務信息。我們被現代科技產品左右了,被某種說不清的力量遙控了。就在這種莫明其妙但必然的遙控里,人人都災難性地走到了生活的前臺,人人無法躲藏,徹底暴露。“在后現代主義那里,人總是無可挽回地處于世界之內;而世界是以局部的、暫時的結構形式組織起來的。”[7]171懷爾德認為,把握事物深層次原理的方式是使自己與它們保持距離,處于能夠洞察的地位。但在后現代主義中,這既不可能也不是希望得到的。后現代主義對深度觀念持懷疑態度,否認在現象后隱藏著神秘普遍的真理原則。既然除了現象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東西,那么同樣不存在人得以觀察現象領域的超脫地位。后現代主義強調 “存于可見事物之中的真理”。因此,在無線通訊時代,人人是可見的、可觸摸到的,是與世界、他人充滿聯系的。但事實是,物理的空間又使這種 “可見”、“可觸摸”并非實實在在的,毋寧說它是一種想象的。后現代主義文學 “追求的既是通過想象性控制結構來使世界抽象化,也不是使自身脫離現實;它只是適度的體驗現實世界,通過對世界的大量認識,克服或糾正現象的無序狀態”[7]171。懷爾德認為,這是贊同的詩學,是一種旨在激活作為整體的意識,在它與世界的關系中實現某種動態、能動、交互的東西,這也是一種 “無距離”的詩學。
在某種程度上,“無距離”既在空間上體現出來,也在時間上體現出來,由此便導向瞬息性。斯潘諾斯提出,后現代詩學的必要性將面對文本的開放臨時性,以便打破傳統詩學的解釋權力意志;那種意志總是從其終極或單一的超時間意義的角度來解釋文本。“但后現代文學不僅使時間成為主題,而且使 ‘媒介’自身成為 ‘信息’。”[7]175對于后現代文學來說,對當下時間的把握與體驗而非對過去時間的大規模想象性考古——如現代主義文學中普魯斯特的 《追憶逝水年華》、艾略特的 《荒原》、喬伊斯的 《尤利西斯》那樣才是重要的。時間是線性的、發展的、不可重復的,注重當前和瞬間,以詩意的心情去感受、理解生活,實現美的生活,這是藝術所能帶來的身心和諧。1924年周作人就在 《生活之藝術》一文中提出:“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8]。這便是由英國批評家瓦爾特·佩特著名的觀點 “藝術給人以最高質量的瞬間”概括而來的“剎那主義”。“剎那主義”強調當前,否定過去及未來,而主體對此刻的體驗強勁有力,神秘且壓抑。這與后現代藝術對瞬間快感的表現有某種巧合。瞬間是被切斷的瞬間,如同對拼湊式電影、無聲音樂片段、新句子詩派毫無聯系的句子組合的欣賞一樣,對于生活瞬間的體驗也是強烈的、碎片式的。手機短信文學記錄的就是當時當地的心情、感覺,是即興文學或被記載下的口頭文學。用心體驗每時每刻,把最新鮮最前沿的信息、最鮮艷最熱烈的感受握在手中,是我們能積極樂觀應對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的能力,也是我們珍惜生命、珍惜分分秒秒的態度。人生短暫的旅途鐫刻于手機上或溫馨、或豪邁的文字里,一瞬即永恒,能真切地投入、真正以在場的方式存在于一剎那,也遠勝于長久無知無覺生存著的麻木狀態:
樹/長成穹廬,撐起/綠色天空/路/長成弓箭,奮力/將我們一一射入
我聽到一個聲音說/射出去了就不要回來/永遠在森林里迷途
萬物皆流,唯有瞬間的詩意感受,才能在某一刻讓我們看到,“路”長成了雄健的弓箭,在某位英雄手中奮力將我們射入那濃密的森林;唯有在藝術的瞬間,才能聽到一個神秘的聲音,透露出我們內心深處的渴望與秘密。想要迷途在森林,是對美好自然的眷戀,也是對現代城市生活的痛苦意識。從城市生活退卻,永遠陷入幽深的森林,意味著徹底的憂郁與拋棄。這一剎那的感受便是主宰,“不要回來”、不要過去、不要未來,永遠的迷途是永恒的,也是幸福的。
曾經被視為在印刷紙頁上供閱讀的藝術品、文學作品、從遠處觀賞的形象、被把握的客體都變成了在時間中讓人聽見的 “口語”,但只有我們身上一個延伸的器官——手機才幫我們實現了“處于時間之中、歷史之中的人的真實的臨時使用的言語”,并上升到文學的美學層面。其他后現代文學理論家按照斯潘諾斯的做法,強調了具體和偶然的文學,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文學。例如在大衛·安坦創作的一本詩集 《調諧》(1984)中,即收集了安坦在各個地方、在不同場合所創作的即興隨想詩。這種文學實踐將作者和受眾帶入一種互動碰撞。短信文學在無形中促成了一場全民文學運動,這是后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片“瘋長的水草”,它呈現了一派鮮翠欲滴的審美圖景。后現代主義文學追求一種不那么拔高、不那么自我中心的敘事與抒情,追求一種善于接受語言和經驗中的松散、偶然、零碎、不完全等諸般樣態的敘事與抒情。與之對應,那樣的文學接受隨意的非文學的言語形式,如信件、雜志、談話、軼事和新聞報道。短信最初也是簡短的書信,發展到后來便越來越成為敘事的或抒情的 “非文學”文學言語,這一矛盾用語也暗示著它與后現代文學的吻合。比如: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涼風冬聽雪/心中若無煩惱事/便是人生好時節/愿你:晨有清逸,暮有閑悠,夢隨心動,心隨夢求。這是一首短信祝福詩,嚴格地講,它沒有傳統文學所謂的意境與縹緲的意象,詩意也并不純正。起始兩句應用起興手法,平鋪直敘了四季的風物特點,以此引出一種優雅舒適的心境,叫人拋開煩憂,享受人生的好時節,結尾的祝語便水到渠成。然而,“百花”、“望月”、“涼風”、“聽雪” 這些自古以來便飽含 “風花雪月”之浪漫的陳舊意象,或許會遵照慣例把人帶入詩意的幻想空間,無論你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還是在夜深人靜的枕頭邊,這些看似 “復制”的文學意象也會隨著短信的祝福深深潛入你的內心。
[1]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唐小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4.
[2]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代理論[M].張志斌,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165.
[3]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0:11.
[4]王岳川,尚水.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8.
[5]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34.
[6]伽達默爾.贊美理論—伽達默爾集[M].上海:三聯書店,1988:131.
[7]史蒂文·康納.后現代主義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8]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精編[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242-245.
I269.7
A
1673-8735(2011)02-0057-05
2011-02-16
趙飛 (1983-),湖南藍山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鐘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