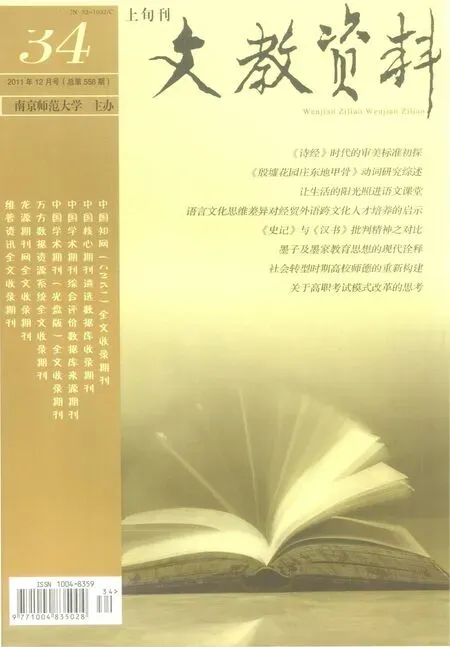《舊制度與大革命》與托克維爾的政治自由思想
徐 蕾
(北京中醫藥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29)
一、舊制度下的貴族自由
托克維爾對自由情有獨鐘,批判舊制度。他認為舊制度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又增加了王權專制的不自由因素。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卻存在某些奇特的自由——貴族自由,使得王權專制并未成為所有人民的主宰。托克維爾以略帶同情的眼光分析這些自由,試圖呈現出舊體制比較美好、比較值得懷念的一面。在貴族的自由下,個人可能保有很大的權利、獨立性和空間活動性,包括貴族的所有上層階級都用此防止國家權力對自身特殊權利的侵害。他認為貴族階級雖然不復擁有權力,卻仍然保持著祖先傳下來的驕傲氣質,“既仇視奴役,也仇視法規。他們毫不關心公民的普遍自由,對政府在公民周圍加強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們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們自己頭上,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必要時甘冒種種危險”①。結果,貴族在王權面前反而展現了某種崇高的精神與品質,成為舊體制下捍衛自由最堅定的一群人。我們可以想象,當大革命爆發后,貴族階層隨著封建制度走入歷史,托克維爾勢必認為人民少了一道防衛中央專制的機制,從而更加懷念昔日貴族制的貢獻。從這一點上可以強烈感受到他對舊體制美好一面的懷念。除了貴族階級之外,教士與法官也同樣得到托克維爾的高度肯定。托克維爾認為教士由于擁有不可剝奪的土地特權,因此在世俗政權面前往往顯得獨立不屈,他們“同第三等級或貴族一樣,仇視專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熱愛政治自由”②,鏟除了教士的土地特權,人民也失去了自由的一個極大成分。至于法官方面,由于法官實行終身制,且不求升遷,這兩點大大有利于司法的獨立,從而多少發揮了保障個人自由的作用。最后,托克維爾認為即使在資產階級和一般人民身上也有某種自由氣質是革命后的人們所欠缺的。舊體制下的資產階級喜歡效法貴族階級,這些“假貴族”因此無意中承襲了真貴族的驕傲與抗拒精神。他們習慣追求一個舞臺,在這個小小的舞臺上捍衛共同的尊嚴與利益。托克維爾雖有美化貴族階級之嫌,但是確實他認為貴族極能反映時代的精神——關心個人權利、社會義務、極力主張發展公共教育,并且和第三等級一樣希望改革徹底、國家強盛。
托克維爾認為舊體制絕不是一個充滿奴役與依附的社會,透過鬻官制、貴族、教士、法官、資產階級,法國人民事實上享有不少政治自由。這些自由有其生命力,使人們心中“培育著自豪感,使熱愛榮譽經常壓倒一切愛好”③。雖然他認為這種政治自由難以幫助法國人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但是他依然固執地認為舊體制下的人“有著比我們今天多得多的自由”。然而同時托克維爾也意識到這種貴族的自由畢竟是封建制度下的產物,是貴族們在契約關系下所獲得的特權,是非正規的、病態的、與階級制度相關聯的,實質是“特權的享受”。正是這種遠比德國、英國之貴族輕微的法國貴族的特權“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原因在于貴族已經變成只享受權利而不盡義務的階級了,因此,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大革命就是要推翻這些令人民難以忍受的貴族及教士,取消他們的封建特權,以建立一個人人地位平等的社會。一旦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就不能奢望舊式自由繼續保存于新的民主社會中。民主社會如何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兼有自由呢?托克維爾認為貴族的自由必然要讓位于民主的自由,這也正是其睿智之處。
二、民主與自由的關系
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后給法國社會帶來了什么?自由還是平等?
托克維爾進一步要思索的是在民主社會的前提下,如何認識民主與自由的關系,從而實現“民主的自由”。他認識到,在新產生的專制帝國里,人們實現了較為徹底的平等,但也較為徹底地喪失了自由。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們那種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無比偉大和神圣:“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④與之相對的是,當人們放棄了自由,重回專制君主懷抱的時候,他又非常遺憾地說法國人“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⑤,這場大革命實際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于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⑥由此可見,托克維爾對自由的熱愛遠遠超過對平等的熱愛。這與法國人執著平等、不尚自由的傳統形成鮮明的對照。
平等本身不會威脅自由,平等不是自由的對抗價值,平等可以與自由兼容,其關鍵是不要盲目服從一個權威的支配。大革命以后,民主社會的身份平等造成人們強勢政府的依附心理,結果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組織形式——民主專制,即平等的專制局面。常識告訴人們,民主與專制是相對立的。在歐洲的君主專制時代,民主的敵人是君主個人的獨裁專政。一旦民主取勝,它還有新的敵人嗎?托克維爾的答案是肯定的,這個敵人就隱藏在民主內部,即多數人的專制。建立在多數同意之上的不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美國民主式的民選政府,而且同樣可能是高高聳立的斷頭臺。民主作為所有人都參與公共事務的政府參與形式帶有多數人暴政的危險,最終帶來泯滅個性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大革命期間,盡管人們需要在自由上的一律平等,但是當做不到這一點時,他們就會放棄對自由的追求,選擇奴役上的平等,他們寧愿忍耐貧困,也容不得貴族。這就是他對大革命前法國人政治心態的寫照。在這種沒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們充其量不過是心滿意足的奴隸,因為民主中孕育著新專制主義,其形式是中央集權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直接參與的多數專制的政治權力。這種民主加劇了自由在社會中的逐步失落。對此,托克維爾表達了強烈的遺憾,并對他心中那種真正的、發自心靈的、毫無功利目的的自由給予了高調的贊揚。托克維爾對多數人的專制擔心絕不是杞人憂天,追求鐵血式平等的法國才會有血腥的大革命和革命后的專制復辟。
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國大革命只是自由與民主的早期爭論的一個歷史記錄。在這場爭論中,焦點是多數的專制。在這一問題上,托克維爾像其他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奮力為個人的權利免受國家的權力,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權力的入侵加以辯護。
三、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實現民主的自由
托克維爾不為貴族制度的消逝而挽歌,也并不指望法國能夠重建貴族制度以獲取自由,同樣也不認同人民主權理論。托克維爾關注的是:在一個不可避免地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時代中,自由在革命后的集權國家如何重建?或者說,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過程中成為可能?這是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本,也是現代政治的核心論題。如同“將巴士底獄片片拆毀,并不能使囚徒變成自由人”,摧毀舊制度不能靠大革命,追求民主,則只能沿著追求自由的路徑才能得到;若放棄自由去追求民主,則只能導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民主應該服從自由,把自由置于社會平等之上。這或許是托克維爾為全人類總結的政治教訓,這也正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價值日久而彌新之所在。與多數統治相比,在托克維爾眼中自由的珍愛有其獨到的魅力:
當人民執意要當奴隸時,誰也無法阻止他們成為奴隸;但我認為,自由制度能使他們在獨立中支持一段時間,而無需他們自助。基于自立的自由是可以培養的,而對自由的真正熱愛則是不可傳授的,因為它來自所有偉大的人類的情欲的神秘處。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于人們只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因為這種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確確,對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總會帶來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在自由中只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⑦
“民主”制打破了貴族制的不平等和特權,實現了平等,是符合社會正義的,但是問題的關鍵是:與“貴族自由”相比,“民主”也存在多數人專制的危險。民主不僅僅是多數人的統治,它更是人民可以撤換統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國內和平的一種有用的工具。民主不僅在于主權者的人數,更在于運用權力的方式。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自由與民主,盡管是同為世人所追求的兩個目標,卻有著各自的內在邏輯。一旦這兩種邏輯互不相容,兩者就會發生沖突。只有自由與平等攜手并進,才有機會擺脫暴政與平等相結合的“民主專制”的危機。
托克維爾從“貴族自由”轉向考察“民主的自由”后,更多地關注這個理論問題本身與法國現實的結合。法國歷史的進程證明,無論過去還是將來,民主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民主的思想和行動已開始逐漸占了上風,但是應該如何抑制民主的弊端呢?那就需要依靠自由。然而鑒于轉型社會中尚無民主運作的基礎,同時民主和自由仍處在相對分離狀態,如何使自由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過程中成為可能?托克維爾最終把目光投向了市民社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社會。他認識到,市民社會是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一項重要領域,他強調,不是公民參與政治,而是積極地參與自愿的結社,否則就難以保證政體的自由性質和公民個人的自由不致失落。市民社會自身就是社會整合和公眾自由的最重要的領域,有助于限制國家政治權力。托克維爾發現法國之所以長期受害于威權傳統,是因為行政上的中央集權把社會原子化為孤立的個人了,即在社會中鏟除了作為中介組織的等級和結社,因而在沒有市民社會的情形下使個人直接地暴露于國家的權力,這樣,個人就無法形成民間的力量,也就難以對國家的權力構成有效的牽制。民主政治建立在介于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獨立組織和社會集團的存在的基礎之上。若是沒有社會中介的存在,就會出現獨裁或集權政權。托克維爾說:“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⑧
托克維爾認為要挖掘社會傳統中一切有助于保持自由和抵御專制的因素,而鄉鎮自治和結社自由這兩條正是為未來重建自由制度的最重要的資源。因為他始終認為國家除了君主(無論是舊君主還是新專制者)和民眾以外,還必須有各種各樣的中間政權機構和中層組織,來限制中央集權,保障公民自由,訓練政治參與,促進公民精神。既然舊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貴族這一天然的中間政權和社團組織,那么地方自治和結社自由就成為新的手段。“在貴族制國家,貴族社團是制止濫用職權的天然社團”,那對于沒有或者鏟平貴族的民主國家而言呢?“結社自由已成為反對多數專制的一項必要保障”,從而形成今天我們所稱的公民社會。這也是他認為政治自由能得到保證的最好制度安排。事實上,法國一直沒有擺脫中央集權和獨尊巴黎的事實。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才開始大規模的地方分權改革,包括把地方官員的任命制逐步改為選舉制,同時賦予地方官員直接選舉產生而使得其具備獨立權力。這已經是大革命爆發兩百年之后了。
托克維爾的卓越見識來源于他對不同國家和社會的親身觀察和分析,來源于他對歷史材料的充分把握,來源于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實踐,更來源于他對國家政治命運的深刻思考。在托克維爾身后,法國革命開啟的革命浪潮風起云涌,并被添加了新的內容,比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
注釋:
①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09-110.
②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50.
③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56.
④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2.
⑤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2.
⑥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201.
⑦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202-203.
⑧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6.
[1]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2]李宏圖.從貴族的自由到民主的自由[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2,(3).
[3]黃艷紅.“自由”的喪失和平等的起源[J].衡陽市師范學院學報,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