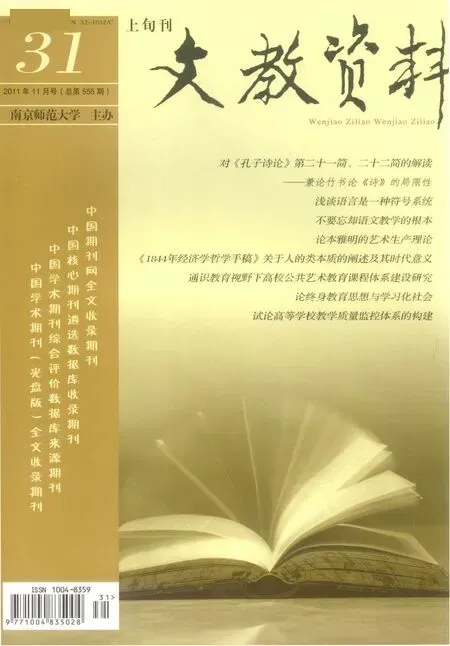日本人微妙心理探微——《飼育》論
雷 芳
(南京師范大學 中北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6)
一、引言
1994 年,大江健三郎成為第二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語作家。評選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在授獎辭中指出:“大江的作品中存在著‘變異的現實主義’這種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全新的見解和充滿凝練形象的詩。”予以大江的作品很高的評價。此后,大江的作品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備受矚目。
《飼育》是大江初登文壇,于1958年在《文學界》上發表的一部短篇小說,并榮獲第39屆芥川文學獎。奧野鍵男這樣評價《飼育》:“這是一部基于異想天開的構思,抒情性濃厚,藝術水平極高的杰作。”①作品描述了戰爭結束前的某個夏天,一架美軍飛機墜落到村莊,一個黑人士兵成為俘虜。村里人很戒備,用鐵索套住黑人士兵,像動物一樣飼養他。但孩子們開始與他交流,并相處得很好。時間久了,村里人戒備心減弱,與黑人士兵相處融洽。夏末,書記命令將黑人士兵交給政府處置,“我”跑去告知,不料黑人士兵反目成仇,把“我”當成人質,父親憤怒之下拿起劈刀砍碎了黑人士兵的頭骨。
《飼育》被收集在大江初期作品集《死者的奢華》中。據我的查閱,專門論述《飼育》的評論甚少,多以論述初期作品為主題。涉及《飼育》的,主要是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作品:①以作品的舞臺——村莊為中心;②以作品的創作意識為中心;③以作品的文體特點為中心;④從政治制度角度;⑤以重新探討作品主題為中心。
本文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作品中人物的情緒反應,行為方式的變化,以期考察日本人的微妙心理,旨在為《飼育》論開辟一個新的研究角度,同時運用心理學的理論,探究深藏于日本人內心的微妙心理。
二、選擇《飼育》
誠然,研究日本人的作品不計其數,研究日本人心理的著作也不在少數。我選擇《飼育》來研究日本人的心理出于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大江健三郎在初期作品集《死者的奢華》后記中寫道:“監禁狀態,在封閉的墻內生存的狀態——這一貫是我的主題。”②《飼育》這部作品的舞臺即是處于監禁狀態下的村落共同體。而日本自古以來就是單一民族、單一語言、單一文化的國家,就整個國家而言,處于四面環海的封閉狀態,就各個地區而言,由于山脈和島嶼的阻隔,也是封閉社會。封閉社會下的單位即為集團,可以說日本社會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集團構成的。作品的舞臺——村落共同體可以說是典型的集團代表,亦是整個日本社會的縮影。
其次,封閉的狀態下必然形成封閉的人際關系。日本自古以來就一直處于這種狀態下,也樂于存在于這種封閉式的人際關系中。在封閉狀態下形成的心理是純粹的、原始的、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可以作為很好的心理研究對象。
最后,變態心理學中的心理應激理論指出:應激是人或有機體在某種環境作用下產生的一種適應環境的反應狀態。如果這個刺激或情境需要人付出較大的努力去適應,甚至超過一個人所能負擔的適應能力,這時就會出現緊張狀態。應激源是指可能引起機體應激反應的各種刺激物。③由飛機墜落事故闖入封閉狀態的村莊的黑人士兵,無疑是一個具有潛在性強烈刺激作用的應激源。村里人在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刺激時所產生的一系列情緒波動、行為方式轉變正是日本人深層心理反應的最好佐證。
三、由“排斥”轉向“接受”
由于飛機墜落,黑人士兵出現在村莊。盡管村里人可以判斷出他是士兵,但仍叫他“獵物”,把他像動物一樣飼養,還給他套上鐵索。對于突然出現的黑人士兵,人們從心理上排斥他。但孩子們不以為然,在給他送食物的時候對他產生了好感,出于同情,還為他解開腳鐐,甚至還帶他去戲水。很顯然,孩子們在心中把他當成人而接受了他。
日本是一個嚴格的等級制社會,孩子處于這個等級制的最底端,當孩子與黑人士兵建立了相對融洽的關系后,大人們也漸漸接受了他,并與黑人士兵有了比較親密的交流,比如他幫書記修理假肢,教村里人做分離作業,等等。
于是,黑人士兵融入了村落共同體這一縱向社會。日本人在與他人交往時,隨著親密度的增加,期望建立如親子關系那樣的人際關系。這也正是村里人在與黑人士兵交流之后內心所想建立的關系。土居健郎把這種心理稱作依賴的心理。閉鎖村莊的人們對黑人士兵從“排斥”到“接受”的變化是這種潛在的依賴心理在起作用。
四、由“恐懼”到“施暴”
村里人在抓住黑人士兵時,用鐵索將他的雙腳緊緊套住,還不停地發出噪音。當“我”看見他時,“這種突如其來的恐懼簡直使我不知所措”。④父親代表村里人想將黑人士兵交給政府處置,卻遭書記拒絕,并被命令看管他。所有人的表現都充滿著對黑人士兵的恐懼。這種恐懼的來源,其一是因為在封閉狀態下村里人對陌生事物無法認知。其二,也是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人的自卑心理。戰爭末期,糧食匱乏,生活困難,但村里人給黑人士兵的食物卻是“幾個大飯團,焦脆的干魚,煮青菜,裝在廣口瓶的山羊奶”。⑤如果是像動物一樣喂養他,就根本沒有必要提供這么豐富的食物。這不如說是村里人強烈地意識到黑人士兵是美國人,是一種強大的存在,對強大力量的自卑心理使他們對黑人士兵驚恐萬分。
在書記決定將黑人士兵交給政府時,“我”提前去告知,黑人士兵一反常態,把“我”當成人質。大人們不知所措,父親舉起劈刀砍碎黑人士兵的頭骨。最終村里人選擇了施暴。由“恐懼”轉向“施暴”,這是一個情緒極端變化的過程。根據前面提到的心理應激理論,黑人士兵是一個潛在性強烈刺激的應激源,在他爆發的那一刻,村里人亦隨之產生應激反應,但這突然又強烈的刺激超越他們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情緒發生極端轉變,轉而施暴。但這種極易發生情緒變化的狀態正是社會心理的體現,同時它也是構成心理學中變態心理的重要因素。
再審視本作品的寫作背景,它寫的是戰爭即將結束時的事情。人們對戰爭的恐懼和焦慮會對人的心理造成一定影響。但無論是作為外接刺激的黑人士兵也好,還是戰爭的因素也好,都屬于外因,歸根結底還是社會文化因素這一內因在起作用。也就是說,潛藏于日本人內心深處的心理通過外界刺激影響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由此,日本人的變態心理傾向暴露無遺。
五、結語
心理是一個極其復雜且難以捉摸的東西,探求群體的普遍社會心理更是不易。本文選擇《飼育》這部文學作品,運用心理學理論分析主體人物——村里人的情緒反應、行為變化和心理變化,分析出日本人具有既依賴又自卑,既易變又帶有變態心理傾向的這一復雜而微妙的心理。
綜上所述,本文從一個新的視角——心理學來研究《飼育》,剖析了日本人的微妙心理。
注釋:
①奧野鍵男.奧野鍵男作家論集.泰留社,1978年7月,筆者譯.
②④⑤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
③劉新民,李建明.變態心理學.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1]中根千枝著.陳成譯.縱向社會的人際關系.商務印書館,1994.
[2]土居健郎著.閻小妹譯.日本人的心理結構.商務印書館,2006.
[3]孫滿緒編著.日語和日本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4]雷芳論《飼育》中大江健三郎對人性的思考.中國知網,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