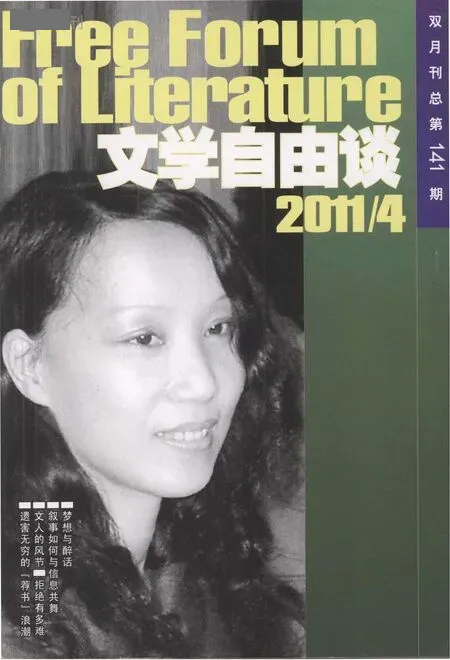『壞女孩』的身份問題及其文學史意義
●文 劉衛東
在描寫現代都市生活的文學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些“壞女孩”:她們受過高等教育、品位上乘、頗具現代意識,但又脫離體制、離經叛道、我行我素。雖然是一小撮,卻銳氣、時尚、拉風。她們的生活究竟是一場痛徹肝腸的“靈魂戰爭”還是基于“個性癖”的走秀?我以為,目前流行的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評論都有道理。那么,她們究竟想堅持什么?她們為什么這樣?她們的命運如何?我想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1 、“壞女孩”的傳統和現在
本文所謂的“壞女孩”是一個人物形象系列。如果定義的話,“壞女孩”是叛逃出體制,用不被世俗認同的生活方式來體驗、感受“墮落”,挑戰審美、道德禁忌,同時又認真執著對待人生“難題”的女性。梅艷芳在《壞女孩》中唱到的“沒有辦法做乖乖,我暗罵我這晚變得太壞”,正是她們內心糾結的表現——在失控中墜落。她們很迷惘,卻又對這種迷惘很清醒。她們是壓抑在我們內心的敏感、活躍的“另一個”。
從精神史上說,我以為“壞女孩”生活方式是波西米亞的當代變形。“波西米亞是一種思想,是一種神話的化身。這個神話包含著罪惡、放縱、大膽的性愛、特立獨行、奇裝異服、懷舊和貧困。”(伊麗莎白·威爾遜著:《波西米亞:迷人的放逐》)。在1991年,麥當娜將自己“金發野心”世界巡回演唱會的片段和花絮推出,以《真實與挑戰》(不知何故中文譯為惡俗不堪的《與麥當娜同床》)為名,演繹了經典的“壞女孩”形象。稍加檢視不難發現,中國“壞女孩”們思想資源直接來自橫掃西方60年代文化的叛逆運動,《北回歸線》、《麥田守望者》乃至影片《發條橙》、《猜火車》等作品中呈現的場景被稍加修改(通常是削弱)后被復制到了新世紀前后的中國。在我國,“壞女孩”的出現還與精神焦灼的整體氛圍和消費文化的迅猛發展關系密切,同時,還有女性主義思想的部分影響。因此,我以為,“壞女孩”不僅僅是西方某類形象的復制,還生成于中國當代現實的精神平臺,帶有中西合璧的印記。
如果追溯,我愿意從現代文學的開端來尋找“壞女孩”的蹤影。“五四”以來,丁玲筆下的莎菲、茅盾筆下的孫舞陽、曹禺筆下的陳白露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的“舞出自我”、不計他人眼光的女性。莎菲女士傾慕凌吉士“那薄薄的小嘴唇”,“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她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新的狂笑中瓦解去,我愿意”。此前的研究者在分析這個特殊的群體時過于簡化,只是用“女性主義”的理論一套,認為書寫了新女性的“苦悶”和“個性解放”,然后了事。有的論者將其指認為“妓女原型”,并且說“妓女原型直接象征著性欲,它以風流、妖艷、下賤、恬不知恥和自甘墮落為外在表現特征”(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這倒符合人們對“壞女孩”的一般看法。我認為,“五四”女性的標新立異包含有覺醒的一代對自身境遇的思考和對自己“肉身”的“處理”的新的方式。“壞女孩”正是以自己的離經叛道沖擊了搖搖欲墜的封建理論大廈,確立了“人”與道德較量的優先地位。我們必須以新的視角打量她們。新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壞女孩”剛開始出現的時候,還是鐵凝《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里的安然,叛逆得曖昧不明、羞羞答答,不過,她們接著就理直氣壯起來,變成了膽大包天、為所欲為的CoCo(衛慧《上海寶貝》)和陶然(廖一梅《悲觀主義的花朵》)。
我想問的是,她們是如何說服自己的?或者說,她們給了自己的生活以怎樣的理論上的正當性?如果分析她們,性,肯定是繞不開的,甚至只能由此入手。“壞女孩”通常都有一部洋洋得意的濫交史,《悲觀主義的花朵》這樣形容主人公:“有一陣子這女孩選中三個男人,分一三五和他們上床,這樣還剩下四天的時間無所事事。關于空閑的這四天時間她當時想出兩種辦法,一種是再找三個男友,或者一星期和他們每人上床兩次,剩下的一天作為休息。這兩種方法都不可行,前一種是因為她心不在焉常常叫錯名字,記錯約會。而后者,則需要他們對她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此輕描淡寫、甚至引以為榮地講述自己的性史,固然有夸張的成分,但是卻直指傳統性道德,高標叛逆和獨立。給人感覺,似乎在性上走得越遠越有革命的效果。以豪放著稱的棉棉曾說過“我擁有18歲的臉和80歲的生殖器”這樣嘩眾取寵的驚人之語。《上海寶貝》更是充滿了露骨描寫,一度還因此被禁止發行,引起軒然大波。問題是:她們為什么非要如此?我注意到,小說中的“壞女孩”們并沒有明確回答,相反,作品屢次寫到用性去填補意義,但是之后卻更迷茫。文本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意義空洞。性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在中國語境下,變為“壞女孩”的一個噱頭。我以為問題在作家,她們錯把性當成了叛逆的工具。性自由和性放縱或許僅有一線之隔。實際上,在不被允許的場合放肆談論禁忌話題,正是“壞女孩”的取勝捷徑,而她們所談論的,多半是為了顯得自己見多識廣而有意夸張。棉棉指責衛慧抄襲的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例——她指責衛慧并沒有這樣的生活經驗。雖然是一場鬧劇,但是足以說明“壞女孩”的生活也被概念化了。
“壞女孩”的標志除了夸張的性,還有畸形的愛。事實上,沒有一個作家愚蠢到試圖將“壞女孩”的生活“延續”下去,她們只能璀璨地綻放在某個生命的瞬間,然后回歸到正常的“過日子”。“壞女孩”都有一個真心相愛的男性,但是注定無法修成正果。《上海寶貝》中的天天是吸毒的性無能,《悲觀主義的花朵》里的陳天是有妻室的——最后的結局都是死亡。“壞女孩”所追求的是瘋狂、極端的愛情體驗。在此,在這里,“壞女孩”與拜金的、物質的女孩分道揚鑣。廖一梅在《悲觀主義的花朵》中談到一種“吸血鬼”一樣的愛情:“吸血鬼的愛情有著愛情中一切吸引我的東西,致死的激情,永恒的欲望,征服和被征服,施虐和受虐,與快感相生相伴的憂傷,在痛楚和迷狂中獲得的永生……”事實上,這樣的愛情幾乎都是以畸形和反道德的形式存在的——否則也不會具有如此強大的反彈力。我以為,這是“壞女孩”乖張行動的動力之源:她們需要得到自己理想中的愛,一定要如此,不能替代。
2 、“壞女孩”的寫作者身份
從伍爾芙《一間自己的屋子》以來,寫作者與女性之間的關系,永遠纏繞而無解,但是,一個事實是,文學作品中以寫作者身份出現的女性越來越多了。在傳統女性批評看來,女性寫作是歇斯底里的“笑聲”,反對的是男性霸權,正如埃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所描繪的:“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寫成它就引起舊性質外殼的大動蕩,那外殼就是男性投資的載體,別無他路可走。假如她不是一個他,就沒有她的位置。假如她是她的她,那就是為了粉碎一切,為了擊碎慣例的框架,為了炸毀法律,為了用笑聲打破那‘真理’。”早期女性主義的斗爭意識頗強的理論顯然“用力過猛”,但是,不能否認,這種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讓人著迷。
寫作意味著展示自我,因此成為“壞女孩”的標簽——或者說,她們不是傳統字面意義上的“壞女孩”,就是因為她們寫作。在“壞女孩”看來,寫作不再像早期女性主義者那樣被指認為“美杜莎的笑聲”,而是成為一個超級秀場,一個獲得自我的秘密通道。在“壞女孩”看來,寫作沒有那么濃烈的“火藥味”,反而充滿魅力。寫作過程高度冒險和刺激,同時人身又很安全。寫作者不僅是一個身份,還是一個符號,它將“壞女孩”的言行“提煉”成文學,成為一種“虛構”。“壞女孩”的“壞”不僅是現實的,還是文本的,二者互文使“壞女孩”具有了更多的戲劇張力。
相當多的都市小說把“壞女孩”的身份界定為作家,不僅出自對她們的“教主”杜拉斯《情人》的模仿,還因為作家職業本身兼具“表露”和“躲藏”的雙重功能。在小說里,“壞女孩”獲得了更多的行動空間和言說權利,她們如魚得水。衛慧在《上海寶貝》中開宗明義,說自己打算做“激動人心的小說家”,“兇兆、陰謀、潰瘍、匕首、情欲、毒藥、瘋狂、月光都是我精心準備的字眼兒”。值得注意的是,在衛慧看來,“激動人心”才是目的,而其他的不過是手段。尤其是最后的“月光”,在暴力、黑暗的情境中夾雜了凄冷的審美意蘊,暗示出衛慧試圖遮掩的小說家的“底牌”。小說的首要目的還是要“好看”,這一點與女性的“愛美”心理不謀而合。所謂“美女作家”,就是她們不但有普通“美女”都有的美麗的外表,還有更為驚艷的、令人難以企及的才華。你有的我都有,你沒有的我也有,服了吧?《上海寶貝》中的CoCo說:“我要成為作家,雖然這個職業現在挺過時的,但我會讓寫作變得很酷很時髦。”當然,這里有潛臺詞。如果你的生活不能“很酷很時髦”,那么你寫不出來;同時,如果你僅是生活“很酷很時髦”而不寫作,你無非是一個混跡歡場、不懂何為“深刻”的行尸走肉。寫作的女性兼具獨立、叛逆、智慧、美貌(即便不是,也要做“美女作家”狀),最美麗。寫作者身份對于“壞女孩”,如同她們出門前化妝一樣不可或缺。當代最知名的美劇之一《欲望都市》就借助了四位“壞女孩”對女性當下問題進行討論,而“敘述者”正是報紙專欄作者凱莉。
陳染《私人生活》、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將女性身體的“秘密花園”全數暴露,但是,她們卻切斷了女性與外界的關聯,一步步退回到房間里的浴缸,除了讓身體在自慰中“飛翔”之外,她們陷入精神的自閉。而“壞女孩”則推進一步,將散發著頹廢、毀滅氣息的“惡之花”引向了“公共領域”。衛慧從來不掩飾目的,赤裸裸。傳統中諱莫如深的話題,衛慧卻百無禁忌。衛慧知道,這是她的王牌。《上海寶貝》開頭就說:“每天早晨睜開眼睛,我就想做點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絢麗的煙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幾乎成了我的一種生活理想,一種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尋找“生活理想”、“活下去的理由”?這個表述很容易被指認為是做作矯情,要知道主人公經常出入高檔消費場所,對國際名牌如數家珍,她們從未發愁過經濟問題,至少在小說中是這樣。衛慧的發現正是從此開始。“壞女孩”們已經沒有了低層次的欲望,而是尋求一種“純粹”精神上的“飛翔”。她們渴望成名、愛情與性,而不是通常作品中的權力與金錢。她們有錯嗎?她們錯就錯在不甘心過平凡生活。就這一點說,當代“壞女孩”是現代意義上的“精神無家可歸者”。我想說,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必須經過寫作的過濾,才可能是有意義的,這就是“壞女孩”出現的意義。作為小說家的CoCo,直接在《上海寶貝》中就完成了對“現實”的模棱兩可的處理,這樣,讓真正的作者衛慧可以游刃有余。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個轉換,CoCo將承受無數的口水和穢語。
“壞女孩”確實難以定位,我以為,她們首先需要的不是支持或者反對,而是理解。《上海寶貝》過于依賴商業炒作,以至于文學上的探索和革命性被嚴重低估了,得不償失。實際上,《上海寶貝》中的CoCo是極具“典型”的前衛女性,她不但引領時尚生活潮流,還有難得的“沉思”。衛慧和她的作品風頭太勁,表面印象太驚世駭俗,所以人信以為真,沒有人認為她的“壞”只是做做樣子而已。我能不能這樣理解:“壞女孩”是用寫作挑戰一種底線,而這是進入到文學史的必由之路,實際上,衛慧、棉棉做到了這一點。現在很少有人如此理解。比如,相比起幾成先鋒話劇經典的《戀愛的犀牛》和《琥珀》,廖一梅的《悲觀主義的花朵》遭到冷遇,遲遲得不到應有的肯定。也許評論家不愿拿自己的聲名去賭博,他們要再等一下,當然這是他們最好的選擇。他們要看:“壞女孩”,你能撐多久?
3 、“壞女孩”去哪里
時間是惟一可以被信賴的。千淘萬瀝,它能讓表面的、冗余的、口是心非的、文過飾非的東西慢慢褪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成。“壞女孩”的生活,終究要被時間檢驗。
既然小說是虛構,為什么不允許“壞女孩”的經歷是虛構?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寶貝》的封面上,印著一行似乎沒有必要的說明:“一部半自傳體的小說。”“半自傳”,還“小說”?在后記中,衛慧繼續說,“這是一本可以說是半自傳的書,在字里行間我總想把自己隱藏得好一點,更好一點,可我發現那很困難,我無法背叛我簡單真實的生活哲學,無法掩飾那種從腳底心升起的戰栗、疼痛和激情”,“所以我寫出所有我想表達的意思,不想設防”。衛慧希望讀者將這部作品看作一部生活實錄,固然有作秀和商業包裝的成分,但是骨子里并非批判這種生活,而是沾沾自喜。理論上講,女性在身體上的堅持和反抗最終是一條不歸路,一次性地消費習慣也注定去尋求更為“刺激”的獵物,而女性的“出賣”也是無法復制的,根本不能源源不斷供給鯨魚般胃口的“求新癖”市場。
“壞女孩”的生活一旦進入文學,就成為被包裝的商品,不再是生活本身。一些奇特、變形、甚至是想象的細節只是為了讓小說“更真實”而出現。這是寫作倫理,毋庸置疑。衛慧在《上海寶貝》中就直言不諱地說:“在小說里我比現實生活中更聰明更能看穿世間萬物、愛欲情仇、斗轉星移的內涵,而一些夢想的種子也悄悄地埋進了字里行間,只等陽光一照耀即能發芽,煉金術般的工作意味著去蕪存精,將消極、空洞的現實冶煉成有本質的有意義的藝術,這樣的藝術還可以冶煉成一件超級商品,出售給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園里尋歡作樂、在世紀末的逆光里醉生夢死的臉蛋漂亮、身體開放,思想前衛的年輕一代。是他們,這些無形地藏匿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新人類,將對我的小說喝彩或扔臭雞蛋,他們無拘無束,無法無天,是所有年輕而想標新立異的小說家的盟友。”我想在這里逗留、引申一下,因為很多誤解可以從中得到澄清。我們應該看到,衛慧是把現實和小說分開的,她知道自己作品必須前衛,主人公也并不等同于自己。問題是,讀者誤以為CoCo生活就是如此,并因此以為“壞女孩”在挑戰某種極限。當然,上述引文也可以理解為衛慧釋放的煙幕彈,她本意是想把自己和小說既分開又混為一談,然后令大家摸不著頭腦——衛慧卻能在其中自由切換。這正是她策略的成功之處。
“壞女孩”出路在哪里?文學就是文學,不得不受到現實的制約,即便是張揚女性權利的學者,也承認現實的障礙過于強大。劉慧英非常樸素而又直截了當地說:“丁玲那種掏心挖肺式的創作對她們自身來說絕對是一條艱險之道,其難度和所受到的世俗壓力不低于現實生活中作為女性所經歷的坎坷,很少有人能在這方面長期堅持不懈并立于不敗之地的。”(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一味的“前衛”不僅在理論上毫無前途,而且在現實中也難免陷入泥沼無法自拔。當年因為《糖》尺度大膽而成名的棉棉,終于華麗轉身:“八年以后的現在,我依然生活在上海,愛情依然在別處,而我依然愛著那些赤誠的才華橫溢的朋友,我有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女兒,并且成為了一個佛教徒。”無疑,這是一種順理成章的解決方式,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文本里。
“壞女孩”走四方,不錯,但是最后還得“回家”。這就是“成長”。令人啞然失笑的是,一大堆的“壞女孩”無論如何折騰,都會回到自己反對的老路上來,就落了個“飽經滄桑”。我每次看到“壞女孩”的結局,都頗覺悵惘:叛逆,只是青春期的一次精神天花?所有的結局或者最好的結局就是舉手投降?廖一梅在《悲觀主義的花朵》中說:“我們從年輕變得成熟的過程,不過是一個對自己欲望、言行的毫無道理與荒唐可笑慢慢習以為常的過程,某一天,當我明白其實我們并不具備獲得幸福的天賦,年輕時長期折磨我的痛苦便消逝了。”“某一天”是哪一天?在《悲觀主義的花朵》中是陳天的死,在《上海寶貝》中是馬克的離去和天天的死。我感到奇怪的是,“壞女孩”不會,也不能自己長大。她們如同庫布里克《發條橙》中的阿里克斯,被強行“抹去”痛苦,最終成為體制中一分子。我不能贊同作家這樣的安排。我想看到瑞典影片《永遠的莉莉亞》里莉莉亞的毫不妥協。但是我也理解,我們的文學中(盡管是虛擬的文學)少有決絕的思想,也少有決絕的人,何況是一個弱女子——我在這里沒有歧視女性的意思。
說到“壞女孩”的文學史意義,不妨先引述一段學者的論述:“女性主義范疇內的身體書寫同時具有了建構和顛覆的雙重意義”,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90年代商業文化語境中,一些女性文本對身體的書寫也越來越背離了其原初的文化目標,滑落為‘被看’的質料。”(喬以鋼、林丹婭:《女性文學教程》)對這個論斷,我的理解是,女性的身體書寫在“女性主義”范疇內是有意義的,但是在“商業文化語境”中,發生了變化。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商榷。“意義”與“背離”,在現實中很難被完全區分開。為什么有的軀體書寫就有意義,有的就“滑落”為“被看”?我以為,內部其實隱含著一個悖論:女性在“書寫”的結構中,同時是“書寫者”和“被看”者,沒有“被看”,書寫也毫無意義。“被看”就是意義,而不必再刻意套上一個外套,以便遮掩住羞處。因此,我的觀點是,“壞女孩”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一次“抵達”,一次觸摸天花板的彈跳,但是,由于缺乏“叛逆”的內在革命性,就迅速被泡沫化。
寫作或者剝掉真實的表皮,或者成為真實的表皮。“壞女孩”既裸露,又遮蔽,因此成也寫作,敗也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