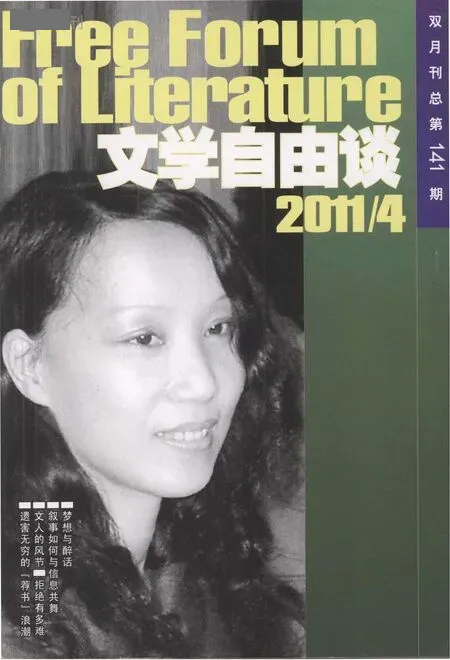『階級斗爭』與『但覺好玩』
●文 顧 農
一
小說《西游記》里有著大量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林庚先生認為乃是一部童話。孫悟空固然大有頑童氣,書中的那些小妖,并不可怕,幾乎都是些很好玩的小朋友。此書老幼咸宜,深得人心,所以“里巷細人樂道之”。(阮葵生《茶余客話》)
由于此書的現存明刻本均不署作者姓名,而到汪象旭的《西游證道書》出來以后,作者開始被署為長春真人邱處機(1148~1235),其人乃是元朝初年道教全真派的領袖,《元史》有傳,李志常記載乃師邱處機西行經歷的那部兩卷本的書名曰《西游記》,小說恰與之同名,于是就很容易混為一談了。
既然小說被看成是邱處機的著作,那么其中必有道教的內容,于是《西游記》也就被看成是論道之書,其中又可分為兩說:一說此書“推衍五行之旨”(陸以恬《冷廬雜識》),一說此書“演金丹奧旨”(紀昀《如是我聞》)。清朝出現的幾部解釋《西游記》的書,如汪象旭《西游證道書》、陳士斌《西游真詮》、張書紳《新說西游記》、劉一明《西游原旨》、張含章《通易西游記正旨》等等,都采取這種追尋原書微言大義的路數,滿紙捕風捉影之談;或用儒家哲學、佛教教義來套釋這部小說的,同樣牽強附會,令讀者墜入五里霧中。
到“五四”時代,胡適研究古代章回小說,將種種舊說一舉推倒,他在著名的《〈西游記〉考證》一文中寫道:
《西游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 《西游記》的大仇敵……這幾百年來讀《西游記》的人們都太聰明了,都不肯領略那極淺極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過紙背去尋那微言大義,遂把一部《西游記》罩上了儒釋道三教的袍子。
胡適痛快淋漓地把強加給小說的這三件袍子統統扒下來,單從小說的文本出發指出其中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自然大有道理;不過此書的主題何在,他卻未作明白的說明。
追尋古代小說的微言大義具有深厚的傳統,于是關于《西游記》的主題在1949年以后又出現了兩種新的結論。
先行出現的一種,是張天翼先生的階級斗爭說。他指出,小說中寫的雖然是神和魔的故事,“但總會或多或少,或隱或顯,或淺或深,或正確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具體地說,《西游記》中的神魔之爭乃是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神是統治階級,是地主,魔是被統治階級,是農民;孫悟空大鬧天宮乃是農民起義,起義失敗被壓在五行山下;后來孫悟空皈依佛教跟著唐僧去西天取經則是受了招安,向統治階級投降。“勝利總是在統治階級的神那一方面,連孫悟空那樣一個有本領的魔頭,終于也投降了神——叫著‘皈依正道’;他保唐僧到西天去取經,一路上同他過去的同類以至同伴惡斗,立了功,結果連自己也成了神——叫著‘成了正果’。”(《〈西游記〉札記》,《人民文學》1954年2月號)
《西游記》里有大量的妖魔,他們阻撓唐僧一行去取經,要吃唐僧的肉讓自己長生不老,這同農民有什么關系呢?各路魔頭明明是壞家伙,白骨精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而先前孫悟空大鬧天宮原是嫌“弼馬溫”這官太小而且稱呼很不好聽,后來雖升格為“齊天大圣”,卻有官無祿,沒有資格參加蟠桃會,只不過得了一個好聽的空名;于是他就鬧騰起來。這與農民起義毫無共同之處。去西天路上的孫悟空同各路妖魔斗爭,智勇雙全,大家都很喜歡他,又怎么會是農民階級的叛徒呢?孫悟空始終樂觀進取、活潑好動,頑皮性急、神通廣大、所向無敵,小朋友最喜歡他了。
《水滸傳》里寫到宋江等人被招安以后,故事毫不精彩,生氣勃勃的情節全在前面,所以七十回的本子看的人最多;而《西游記》里的大鬧天宮只不過是一個序幕,大批好玩的故事還在后面,大家要看的。張天翼先生的分析同普通讀者的意見出入太大了,同兒童的想法相去太遠了,盡管他是一位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張說愿意接受的人很少,學術界也是如此。
給神和魔劃階級成分,在當時就顯得很勉強,現在看去更近于一大笑話。太簡單化地往階級斗爭上靠顯然行不通,于是兩個主題或主題轉化說代之而起。李希凡先生在《〈西游記〉的主題與孫悟空的形象》(《人民文學》1959年7月號)一文中提出,前七回中的孫悟空是一個戰斗的叛逆的英雄,“孫悟空和天上世界的所謂神仙的斗爭,分明是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的升華。神的統治者,神的統治機構,不過是中國的富有特色的封建統治者、封建統治機構的幻化,而孫悟空也恰恰是人的叛逆的英雄和理想化”。這里仍然強調大鬧天宮是階級斗爭,看法略近于張天翼,但他的重點不在這里;接下來他對書中主體部分作出了全新的詮釋,指出到這時候,“不僅是孫悟空的形象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就是《西游記》的神魔斗爭的主題,也不能再從表面上來理解。這里的魔是真正意義上的魔,它們分明是象征著西行路上的自然險阻和重重困難。小說通過唐僧四眾九九八十一難的艱苦奮斗,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征服自然、征服困難的偉大理想,表現了中國許多歷史人物獻身于理想和事業的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信心,而這種精神突出地滲透在孫悟空的形象和性格里”。作品這時已經由“反抗的主題”轉化為“歌頌人的征服困難的主題”了。按照這樣的分析,后大鬧天宮時期的孫悟空不再是一個業已向統治階級投降、專門與本階級同伴惡斗的異己分子,而是一位獻身于理想和事業,勇于克服困難的英雄。這一看法較之張說顯然要合理得多了,曾得到許多人的贊同。
李希凡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重申其兩個主題說,略云“在這種主題轉化的情況下,神魔斗爭的現實性內容,也不再是原來意義上反映封建社會關系的神魔對立、‘正統’與‘邪統’的矛盾,而是神魔英雄孫悟空和阻礙他完成取經偉業的一切惡勢力的矛盾”。(《〈西游記〉的演化及其神話浪漫精神的特色》,《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345期)
這樣的分析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也曾得到局部的修正。王俊年先生在一本專著中寫道:“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總是以生動的藝術形象反映出一定社會的某些本質的東西……《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則以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通過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和歌頌了勞動人民藐視神權、反抗壓迫、堅決向一切邪惡勢力作斗爭的精神,揭露和抨擊了作者所處的封建社會丑惡的現實,同時也表達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征服自然和戰勝困難的偉大理想和信心。”(《吳承恩與〈西游記〉》,北京出版社1973年版)所謂“同時”云云,就是指《西游記》有兩個主題,與李說所見略同。但這里也有新的意見,在李先生那里,孫悟空先反抗統治階級,后征服自然,前后形象似乎斷為兩截;而王俊年先生則指出,孫悟空前后是一致的,因為“小說中的神魔本是一體,因此孫悟空的抗魔斗爭,可以說是大鬧天宮的繼續,不過一是直接反抗最高統治者,一是橫掃他們的爪牙,清除他們的統治基礎”。照這么說,去西天取經途中孫悟空的抗魔斗爭乃是在基層清理階級隊伍,繼續進行革命;可是這樣一來,西行途中的斗爭也就不再是什么征服自然、戰勝困難了——這同作者先前所總結的《西游記》主題又不免互相齟齬。
張、李、王都是水平很高的學者,但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要按主流意識形態來分析研究小說,特別是像《西游記》這樣的神魔小說,費了很大力氣,動足了或者說傷透了腦筋,而仍然難以自圓其說。追尋這一段學術史,不能不歸咎于當時那條“綱”。
二
一般來說一部成功的小說應當只有一個主題,而不會同時有兩個,或者其前后有絕大的轉化。事實上《西游記》以取經故事為主要內容,前七回介紹孫悟空參與取經事業的前史,乃是小說的序幕之一,第八回至第十三回交代唐僧取經的前史則是其序幕之二,先把這兩個主要人物準備好了,然后才可以上路,去戰勝那九九八十一難,取得真經,修成“正果”。
小說的主題其實很明顯,這就是正義和邪惡的斗爭。取經自然是“正”,破壞取經則是“邪”;這與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沒有什么關系——吳承恩大約不懂階級斗爭,更不懂什么是高層統治者的階級基礎,他只是根據民間傳說和先前業已存在之取經題材的小說、戲劇,進一步綜合加工,推陳出新,創作一套好玩的故事,講不管多么困難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
孫悟空的主要戰績是在取經過程中建立的;能走到西天取到真經,主要靠他的神通廣大、英勇善戰,豬八戒、沙僧兩位師弟也各有貢獻;單靠慈悲為懷一片好心的唐三藏自己,是行不了路取不到經的。
至于先前的大鬧天宮一事,不管研究者給予多高的政治評價,其實不過是孫猴子一時的鬧騰,作者吳承恩是不贊成的,斥稱之為“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亂大倫”(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并有詩云:
妖猴大膽反天宮,卻被如來伏手降……
若得英雄重展掙,他年奉佛上西方。
在吳承恩的心目中,孫悟空是一個犯有前科的英雄,盡管他自認為大鬧天宮乃是自己的光榮歷史,而作者認為這只是他早年的一段彎路;只有到他跟著唐僧去西天取經的時候才算走上正路,并得以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作者的思路一貫到底,前后并無變化。中國的傳統是英雄可以不問出身,也不計較歷史舊賬,只看當下的作為和業績。孫悟空是一位有個性有能力的大英雄,先前犯過錯誤,改了就好。
當然,作者在展開豐富的想象細細描寫虛幻世界的正邪之爭時,并沒有完全忘記現實生活,小說中多處涉及明代的時弊,主要采取隨手點染的方式,而且頗有點玩世不恭的意思,但并不影響作品的主線和主題——這就是魯迅總結過的“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中國小說史略·明之神魔小說(中)》),涉筆成趣,足以讓成人讀者發出會心的微笑。例如豬八戒是貪食的,吃相難看,第九十三回《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里沙僧勸他放斯文些,不要這樣滿盤通吃,“饅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八戒嚷道:“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沙僧笑道:“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里來,正替你我一般呢。”忽然為窮書生吐一口惡氣。穿插兩句,故事仍按原先的路徑繼續寫下去。后來魯迅本人寫《故事新編》諸作時,自稱有若干“油滑之處”(《故事新編·序言》),其取法的榜樣正是《西游記》。其中各篇除了《補天》之外,零星的穿插點染都不影響作品的主線和主題。
值得注意的是,孫悟空從“妖猴”進步到取經路上的英雄并且能堅持到底,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頭上有一道約束他的“箍”,什么時候他妖性復發了,唐僧就念起“緊箍咒”來,叫他痛不欲生,馬上變得老老實實,死心塌地地回到正軌上來。“緊箍咒”本名“定心真言”,意思是說,孫悟空本心是好的,在大鬧天宮的時候他迷失了本心,被壓在五行山下以后,本心失而復得,為了防止他本心得而再失,如來佛通過觀音菩薩交給唐僧一個“箍”,給套在孫悟空頭上;一旦孫悟空有什么越軌之處就念起這一套“定心真言”來,讓他復回正軌。正是這個戴著“箍”的孫悟空不斷建功立業,終于成了“正果”。
在作者的思路中,序幕階段的孫悟空處于某種異化狀態,后來才本性復歸,而能夠長期制約他的法寶就是“緊箍咒”。今天的讀者特別是小讀者也許不贊成這個“緊箍咒”,但我們在分析作品的時候卻不得不充分尊重這個東西,不得不按照吳承恩的思路去理解他筆下的主要人物孫悟空,理解作品的主題。
明朝人謝肇淛說:“《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豬為意之弛,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服,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五雜俎》卷十五)他到底是當時的高人,所以對吳承恩安排這緊箍一咒體會特深。魯迅相當贊賞謝氏的這一觀察,他在西安講《西游記》時有云:
《西游記》上所講的都是妖怪,我們看了,但覺好玩,所謂忘懷得失,獨存鑒賞了——這也是他的本領。至于說到這書的宗旨,則有人說是勸學;有人說是談禪;有人說是講道;議論很紛紛。但據我看,實不過出于作者之游戲……如果我們一定要問它的大旨,則我覺得明人謝肇淛所說的……這幾句話,已經很足以說盡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五講《明小說之兩大主潮》)
階級斗爭一說,魯迅未及看到,當亦可納入“議論很紛紛”之列。魯迅但覺此書好玩。
吳承恩當然是反對妖魔的,而又主張反妖魔的英雄自己也要有外力的約束。這樣的意思,在作者當時固然非有不可,而就在今天看去,也并不錯,還可以講出另外一番道理來。這就是因為世界上真有唐僧那種內在定力的人大約相當少,完全靠自覺而不講任何約束是行不通或不能持久的,大家頭上都得有一副“箍”——只是念“緊箍咒”的最好不僅僅是師父或其他什么具體的人,而應當是紀律、法律、道義和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