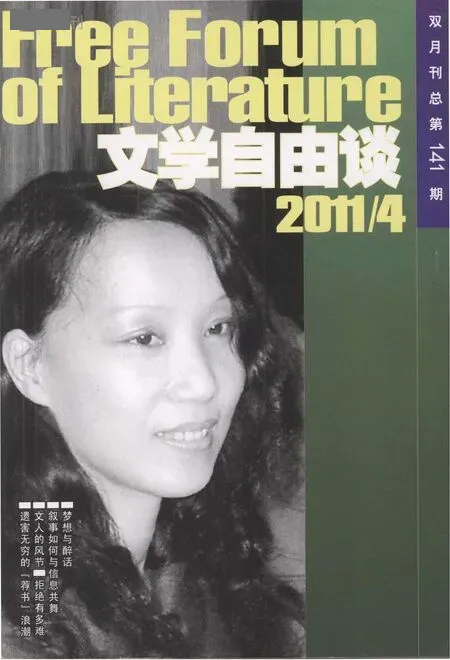吳景婭:正在接近時間深處的謎底
●文/黃桂元
《男根山》劍指人類蒼天,深陷歲月幽谷,里面的故事卻風生水起,云蒸霞蔚。任何自以為是的望“名”生義,都失之簡單和輕率,也都會破壞小說的質地和品位。君不見,有關兩性演繹的攻防劇情跌宕起伏,一路綿延,卻大多似曾相識,人們已漸漸感覺到了視覺疲勞,心理厭倦。一些女作家的欲望表演還不夠情色嗎?媒體炒作的推波助瀾還不夠添亂嗎?女性主義文學的嚴肅意義因此常常無辜地被稀釋、戲謔和褻瀆,這也給吳景婭的突破性寫作增添了被誤解的難度。若非她的堅忍、通透與篤定,《男根山》恐怕早已夭折。
我的印象中,重慶的吳景婭,堪稱一位實力派美文高手。記得當年,不經意間讀到了她的《鏡中》、《與誰共赴結局》以及《美人鋪天蓋地》等集子,那些才華橫溢的文字兼得北方之雄渾與南國之妖嬈,有如急管繁弦繽紛而至,對筆者寫作信心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她的昔日散文固然美輪美奐,卻多見青春期的夢影與落寞,而鮮有靈魂深處的掙扎與拷問。那時她的女性意識還處于被遮蔽狀態,“我們革命時,都沒拿自己當女人”。這話是《男根山》中大姑說的,尋常之中含著徹骨悲涼。在非常年代,性別的消失與異化都不稀奇。那一切畢竟漸行漸遠。女人回到滾滾塵世,經西蒙娜·德·波伏瓦提示,恍然發覺,主宰我們人類社會的皆為“男權中心”和“男性經驗”,而自己不過是“第二性別”,是“他者”,且無聲無息,逆來順受,昏暗中匍匐了遠遠不止千百年。
毫無疑問,這個事實意味著人類歷史的可恥倒退。據說遠古時期,人類非常渴望男女性別能夠真正不分彼此,融為一體,這樣的結果卻使得他們無法繼續生存,最終還是只能回歸各自的性別,扮演不同角色和諧共處。世界史大師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舊石器時代的兩性關系,遠比此后的任何時代都更加平等,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婦女卻逐漸淪為弱勢,依順男人而失去自我,仿佛天經地義,順理成章,從不曾聽到為女性不公處境提出抗議的聲音。人類女性史是一部苦難史,這也是女性主義文學必然存在的根本原因。
小說隨之敞開了一種憂患視野。時光斑斕,紅塵蒼茫,“男根山”長年矗立,是隱喻,還是寓言,那個巨大陰影,為什么與生于斯長于斯的女人命運糾纏不休?“男根山很像奕華一生都放不下的十字架,背來背去,不知何時是個頭。”45歲那年,女作家藍奕華突然把筆名改成了“男根”,她還嫌動靜不大,索性把戶口名也換成“男根”,以示斬草除根的決絕。名字不過是個符號,她未必天真到以為換個名字就可以脫胎換骨,不再隸屬于“第二性別”。波伏瓦說:“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動地變成女人。”早已被“變成女人”的奕華,雌激素正在不斷衰減,卻莫名其妙地與“男根”結緣,難道不是一種反諷?
還是在青翠欲滴的少女時期,奕華就被迫目睹了女人的種種噩運。在逐步“變成女人”的過程中,對奕華影響最大的是母親、大姑、卡卡姑娘、上官子青等長輩女人。要害的是,她們無一例外,讓奕華學會了仇恨男人。母親祖籍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漂亮,高傲,精明,卻被南亙山的小城日子磨損得日益脫形,扭曲。那個整天在寺廟面壁的大姑,以慘烈的身體記憶告誡還只有十七八歲的奕華,像是在完成對一個女人的救贖:“男人不是女人的親人、朋友、同類,男人禽獸不如。”歷盡滄桑的神秘老女人“卡卡姑娘”,更是把狠話說得字字見骨,老天爺造男根是用來與我們女人配對,讓我們生孩子、高興的,男人卻把它當成了鐵錘、箭、匕首、槍,專門迫害女人”。上官子青是奕華的碩士生導師,清高,脫俗,卻被感情與婚姻搞得身心俱疲,終于下了決心,離開痛哭流涕的亂情丈夫一走了之,給偷情成功的女弟子留下了老喬,一個雞肋般的男人,還有一生的負疚、糾結和虛茫。
“男根山”一如既往地冷漠著。它見證了奕華的變化,她的花季怎樣枯萎蕭條,她的夢想如何土崩瓦解。她內心的疼痛和掙扎與日俱增。寫作可以療傷,也在加劇她的痛感。奕華審視著身邊出沒的一個個男人,目光凄然而兇狠。那些男人已面目皆非,不過是她生命中的過客。早早去世的父親,記憶中陌生、自私而委瑣,從不曾給過她和母親實實在在的安全感。林肯是少女時遇到的愛神,他們一起尋找百年難遇的神奇素荷,普希金《歐根·奧涅金》是傳遞他們浪漫愛意的媒介,這對大家眼里的金童玉女,卻無緣終成眷屬,林肯只能是可望不可及、可遇不可求的鏡花水月,與她靈魂相伴,直至永遠。她怎能甘心?冥冥幻覺中,那一幕靈光乍現,“林肯變成了男根山那般巨碩的‘桅子’,強行進入了她的身體,她的私處被撕碎般的劇痛,血從那里流出,向床下流去,房子里全飄著她的血……”那段刻骨銘心的愛,只能是她一生的憑吊和遙祭。
失去了夢縈魂牽的如意郎君,奕華反而自由無羈了,像是隨時可以地把自己的身體交出去。與新男友林一白的短暫交往,使她成為一段同性戀的犧牲品,她跌入了一個尷尬的感情深谷,艱難爬出,眼前一片虛無。她已經有些滿不在乎了,“想象自己在耳邊插上了石竹花,向著性挑釁。但她的對手在哪里呢?”她茫然四顧,渴望讓自己風流一把。老喬是自己導師的丈夫,她和老喬的偷情,已分不清誰是獵手誰是獵物,慣性之下,她幾乎就是在自暴自棄,破罐破摔,順勢讓自己栽進了風雨飄搖的婚姻城堡,帶來的卻是綿綿無盡的失望。
什么樣的男人有助于世俗婚姻?解答這個問題,著名的“木桶理論”(木桶的容積不取決于最長板而是最短板)或許會有些參考價值。日常婚姻的諧調,更重要的應該是男人在柴米油鹽方面表現出的“短板”作用,而對于一些孤高、飽學的知識女人,男人更吸引她們的則是他們的“長板”(精神、氣質、見識、視野)。對于擁有“長板”的男人,吸引力也即殺傷力。吸引力、殺傷力與其欺騙性常常互為表里,相得益彰。根源可追溯到創世紀初的“原罪”,用該小說中的說法,“亞當在上帝面前沒說實話,男人由此變成了喜歡撒謊的人類”。應該說擁有超級“長板”的薩特一向拒絕撒謊,他從不諱言,在真正的愛人(波伏瓦)之外,“能同時體驗一下其他意外的風流韻事,那也是一件樂事”。早在青年時代,薩特就有驚人的野心,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思想和寫作為世間萬物謀篇布局,重新命名,蕓蕓眾生都在翹首他的撥云見日。功成名就后的薩特深得女人的崇拜與愛慕,他曾露骨地說過,“我寫作一向是為了勾引女人,包括寫劇本,也包括寫小說和哲學論著”。男人如此厚顏無恥,并不斷踐行,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波伏瓦的智慧在于審時度勢,從一開始她就懂得自己并不可能成為薩特的惟一,“兩個個體之間從來不存在和諧”(她的這句名言還被薩特寫進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正是波伏瓦的因勢利導,才使他們的愛情有驚無險,一生默契。
在兩性關系上,往往是女人的精神“清潔度”更高,對男人也更挑剔,而且不需要太多理由。比如馬狂,在奕華的眼里只能是一個戰友,無比信任卻又無法接納。馬狂看得很透,對奕華嫁給老喬這件事更是洞若觀火,認為沒有幾個女人真是因為愛男人身體而與他做愛的,女人更喜歡男人的大腦、口才、知識、權力和謊言,讓這些進入身體,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奕華被馬狂點中死穴”,也就承認了男人對女人不見得有什么具體的意義,心理需求往往大于生理用途。她甚至為自己選擇老喬找到了一個堂皇理由,孩子。當老喬指責女人往往都很物質,她們對愛的定位多源于生存的需求與質量,而不是本能的反應,并強調男人看重女人的身體年輕漂亮,其實是更脫俗,對女人的愛也更接近生命密碼的時候,奕華反唇相譏,女人看重男人的大腦、才華、名氣、內在的豐富性,恰恰說明女人比男人更進化,更文明!并詰問他,愛一張漂亮的臉蛋,比愛一個智慧的大腦或名氣高明到哪里去?雙方各執一端,以深刻的片面豐富了一個有趣悖論。
奕華當然清楚,慣于招蜂引蝶的老喬不會是任何女人的惟一,卻不愿丟掉幻想,只能是雪上加霜。奕華初次見到老喬,第一印象其實并不佳,“老喬只是上帝的半成品。……他的五官一如照片所表現的,稱得起英俊。也有寬闊的肩膀和胸膛。但,到了下半身,上帝就像不耐煩了,亂七八糟地拼湊,腿太短,大腿粗壯,小腿過于纖細,龐大的腦袋和上半身壓上去,讓細腳桿不勝承受。嘰嘰咔咔作響”。一年后,奕華對他的觀感更糟,“老喬已老態畢露,腮幫子與脖子上的肉,像被泥石流沖塌的房舍,稀里嘩啦往下掉,幾乎都讓人聽得到皮膚衰老的聲響”。老喬如此不堪,為什么還去偷情,她就那么在乎男人的“長板”?女人常常是個多重性的矛盾體,“善良與邪惡、純潔與兇險、天堂與地獄,皆為一念之間”。奕華雖明察秋毫,仍自食其果,最終悲哀地發現,“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展開愛的游戲。……接下來的性,如一截甘蔗,被榨去糖水后,只會剩下一堆渣”。被榨成渣的性,與人的生命需求實在是相距甚遠。性感是個奇妙的東西,并不專屬于男人或女人,它所透露出的生命力旺盛的性征感覺,是任何“長板”所無法一筆勾銷的。性感源于身體活力,自然而神秘,無論男人或女人,最作不得假的就是身體的感覺和反應。一個人的感官對異性身體是否接納或排斥,根本無法對自己說謊,此時的“力比多”指向往往比精神契合更為苛刻。這也意味著,愛情的游戲面對“力比多”便會原形畢露。無視此,就會受到老天的捉弄,這也是身體為人類文明堅守的最后一道底線。
奕華的自救行為開始于45歲那年。她把戶名改成了“男根”,是為表示“不甘平庸老去”,意識深處卻是對時間的恐懼。而時間其實是所有女人的天敵。孤傲、剛烈的茨維塔耶娃有一天站在鏡子前,驀然看到了自己的白發,頓時驚呆,許多幻想從此破滅。這位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女詩人”只活了49歲,卻分別與里爾克、帕斯捷爾納克、巴赫拉赫和羅澤維奇等杰出男性留下過浪漫的情感佳話,最終選擇自縊身亡,實質上選擇的是絕望,讓時間吞噬自己。波伏瓦也記錄過自己的內心驚悸:“當我看到衰老正一步步向我進攻,而我身體內部的一切都措手不及的時候,我被嚇壞了……”
美永遠是瞬間的。無論怎樣挽留,美的消失都難以逆轉,必然會被時間席卷而去,沒有任何回旋余地。時間就是大限,面對時間,人是渺小的,女人尤其嶙峋和脆弱,時間的虛無感如影隨形。這時候,有痛感的女作家最容易成為哲學家。女人抵御時間,又往往伴隨著清算男人。時間君臨萬物,這點很類似男權,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時間過分寵愛男人,使他們習慣于喜新厭舊,妄自尊大。時間改變了女人的年齡、容顏和軀體,也改變著男人打量女人的目光。女人是否被男人欣賞來自時間的裁決,而男人最欣賞女人的,往往不是她們成熟的境界而是年輕的軀體。在時間的溶劑中,水性揚花的常常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女人抵御時間,其實是在抵御人類的不公。不過,時間并非只能給女人帶來被動和無助,波伏瓦就是以非凡的智慧化解了時間之殤,與薩特從容攜手,一同經歷了所有的繁華與平淡。時間對于他們是平等的。自信的女人荷爾蒙長盛不衰,絕不會輕易就范于時間的迫害,就像杜拉斯,活到了82歲,一生都在愛著,寫著。也如伍爾芙留給伴侶倫納德的臨別之言:“記住時光,記住愛……”
“退守女人之軀”,一味清算時間和男人,未必是吳景婭的選擇。她的視野擁有自己的制高點。美學崇尚感性,倫理學拒絕多愁善感,她游刃其間,只想用寫作來證明自己真實地與這個世界遭遇過,就像伍爾芙說的,女人“必須生活過,愛過,詛咒過,掙扎過,享受過,痛苦過,而且要有巨人的胃口,吞食下生命的整體”。這一切過程,恰恰需要在異性那里得到證實。對于男人,吳景婭并沒有后現代弄潮兒們的解構沖動,小說只是一個載體,一個寓言,承載并隱喻了兩性存在的奧秘。埃萊娜·西克蘇認為:“人類的心臟是沒有性別的,男人胸膛中的心靈與女人胸膛中的心靈以同樣的方式感受世界。”兩性的存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命運殊途同歸,應如小說中妮兒河與男根山山水環繞那樣,達到彼此的“諒解”與默契。吳景婭拒絕給兩性辟疆劃界,而嘗試著相互理解的可能,消弭彼此間的積怨和成見。她對男人的種種鄙陋、偽善、自私深表失望,對女性自身的弱點也在反省。女性主義作家有個通病,她們常常不遺余力地捍衛群體、同仇敵愾,同時對同性又表現得尖酸刻薄,有失仁厚。吳景婭沒有這樣,她對筆下的女同胞皆抱以善意的同情和悲憫。
小說的休止符令人驚詫莫名,唏噓回味。興致勃勃的老喬被兩位年輕女子圍簇著,興沖沖爬上“巫山云雨”游泳池邊的小山堡,縱身往下一跳,轟鳴的深潭接納了他,然后是末日般的平靜。有了美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蓋茨比死在自家游泳池里那一幕的暗示,奕華倏忽跟進,令人揪心的是,她沒有升騰而在墜落。奕華跳入深水,是身不由己,還是主動選擇,已經不重要了,關鍵是“她不再恐懼,也不拒絕了——她已與水不分彼此”。生活真的不用再提供答案了,而必須采用非文學的方式,才能完成一種拯救嗎?
讀解《男根山》是挑戰,也是享受。寫作氣質一向感性的吳景婭,呈示了一種難得的理性思辨深度,并與豐沛的原創精神互為養殖,從而同攬鏡自戀的、苦大仇深的、刺耳尖叫的各類女人寫作保持了個性距離。比如,有關旗袍的描寫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旗袍不僅是女人外在衣飾,更被作者賦予了一種文化寓意。對于中國女人,旗袍擁有自己的語言和編碼,內存巨大,各式各樣的旗袍裹住了女人若隱若現的肢體,使之曲線起伏,儀態曼妙,動靜皆宜,風情萬種,更凝聚和吸納了男人的無窮遐想。然而,旗袍也在制約女人身心的自由。旗袍可以看做是男人投射到女人身上的另一種“男根”陰影。作者對旗袍的詮釋,意蘊深刻而另辟蹊徑,在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中似乎還不曾多見,堪稱神來之筆。
女人寫作有著得天獨厚的自身優勢,對此,就連以激進和尖銳著稱的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我夢想像個女人那樣寫作。”寫作的女人是怎樣一種狀態?伍爾芙的說法是,“女人應該有閑暇,有獨立的財產和屬于自己的房間”。若加上波伏瓦的一段話,才是更完整意義上的女人寫作詮釋:“我只是一位作家——一位女作家,而所謂女作家,她不是一位會寫作的家庭婦女,而是一個被寫作支配了整個生活的人。”同時擁有“閑暇,獨立的財產和屬于自己的房間”的吳景婭是一個耐冷受熱的孤獨矛盾體,無論是做女人的世俗享受,巔峰感覺,或深淵體驗,她都直接間接地擁有過。她由此跋涉在了不知終旅的女性主義文學之途。她正在接近時間深處的謎底。它們會水落石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