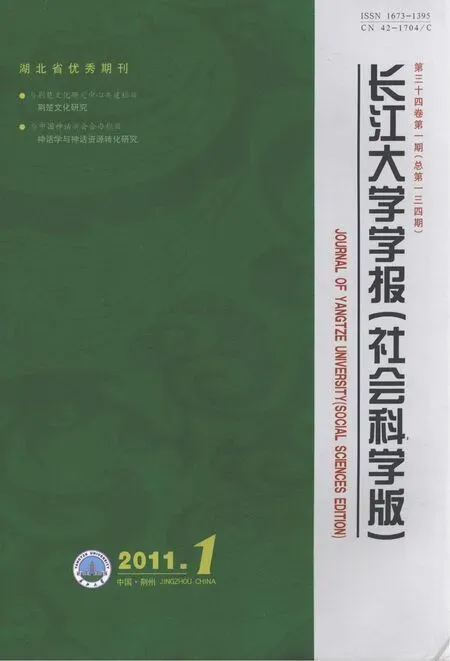論西曲歌的情愛表現特征
梁惠敏
(長江大學藝術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論西曲歌的情愛表現特征
梁惠敏
(長江大學藝術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西曲歌絕大多數為情歌,既寫商人與多情女的離別之情,也寫農村青年男女清新自然的愛情,既描繪節俗中男女一起歌舞的歡快之情,也直接描繪兩情相悅,男歡女愛之情。西曲歌寫情的手法多樣,內涵豐富,較之吳歌,有平民與貴族之間的審美差異。其原因在于當時南北文化的融合,使西曲歌中雜有中原曲調,又因荊、郢、樊、鄧遠離中央,與北方胡人邊境相接,人口雜居之地,人文環境受到北方文化的影響有關。但吳歌西曲尚情的總體風貌比較一致。
西曲歌;情愛;表現特征
文學作品的體裁總是決定著它應有的內涵,中國南朝西曲歌作為“曲”自然也規定了它應有的內涵。王昆吾先生曾將“謠”和“曲”做過區別說明:“一旦作為作品題目,‘謠’和‘曲’就有了兩重用法:一方面,代表歌謠和曲子;另一方面,代表歌的風格或歌曲的風格。……具體分析一下各種題作‘謠’或‘曲’的作品,便能發現以‘謠’為題者,往往文辭質俚、風格樸拙、格調古拗,題材富于批判精神;而以曲為題者,往往音節和諧振婉,情調纏綿,多寫男女相思及相悅,富南方歌辭風格。這就表明:命題之中,有文學的考慮,而不僅是音樂的考慮。”[1](P335)西曲歌是古代中國南方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以王昆吾先生之論,自然是音節和諧振婉,情調纏綿,多寫男女相思及相悅。《樂府詩集》收錄西曲歌34曲,絕大多數都是情歌,富有南方歌辭風格,這正體現出荊楚文學藝術“尚情”的審美特點。
一
荊楚民歌的尚情之風源遠流長,早在《詩》之《周南》、《召南》與《楚辭·九歌》之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作,就鮮明地呈現出江漢之間民歌手與文人們的尚情之風。西曲歌繼承了二南與《楚辭·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作關于寫男女情思的審美品格,將其抒寫得情味盎然,動人心緒。但由于前人慣以儒家禮樂教化觀評說這一類的作品,常常視其為“哀淫靡曼之辭”,如 《樂府詩集》卷六十一引《宋書·樂志》云:“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浸微,風化不競,去圣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于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其實,當我們對這些作品稍加品味,不難感受到那個時代商業社會、市井生活濃厚的生活氣息,同時也深刻地體味到下層人民鮮活的愛情生活,以及結合農村勞動、民風民俗特點來描寫愛情的開朗明快的筆調。
首先,西曲歌最善于寫男女離別之情:
《石城樂》:布帆百余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歡還?
《莫愁樂》: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這里描寫情人離別的場景,表達出一種依依惜別的深情,感人至深。
《那呵灘》兩首也是寫男女別離時的情歌,以對唱的形式出現,別有情味:
離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愿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女子以真摯的情思表達出真情的愿望;男子的對答,則又有一種身不由己的遺憾和悲哀。
再如《估客樂》寫商人經商外出,男女離別之情: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這位女子可謂一往情深,不僅十里相送,還把自己頭上的金釵用作男人經商之資,但是自古商人重利輕別離,女子心底自然不免充滿“一去無消息”的擔憂,將女性的心理活動真實地描繪出來,令人心緒感動。以至于唐代李白情不自禁仿西曲而作《江夏行》云:“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卻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李白在《估客樂》的基礎上擴大了篇幅,對男女情愛描寫得更加細膩,將商人婦的心理活動展示得更加真切。由于《估客樂》中的“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把男女分離時的情景寫得格外生動,給詩歌帶來了自然而別致的情味,從而在梁代就被詩人所化用。如陸罩的《閨怨》:“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余影,含意結愁眉。徒知令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向蘼蕪悲。”這里的“分釵”顯然是言離別之恨,緊承《估客樂》本意而來,意謂而今情郎一去不返,想必頭釵也為其提供了一定的資費,女子自然要對自己當初的“分釵”舉動感到悔恨。所以,此處“偏恨分釵時”化用“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詩意,將女主人公的情絲表達得曲折生動,別有韻味。
中國地域遼闊,離別之后,由于山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音信傳達甚為艱難,常常帶來男女的相思與愁苦,從而使這類作品以悲怨為主調。《楚辭·九歌·少司命》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江淹《別賦》亦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西曲歌中也有此類感動人心之作,如《壽陽樂》即是。《古今樂錄》說:“宋南平穆王(劉鑠)為豫州所作也。”《樂府》作古詞,謂其歌辭“蓋敘傷別望歸之思”:
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后莫相忘!
辭家遠行去。空為君,明知歲月駛。
籠窗取涼風,彈素琴。一嘆復一吟。
夜相思,望不來。人樂我獨悲!
丈夫辭家遠行,久而不歸,雖彈素琴以慰相思,但相思似揮之不去纏綿之繩,纏裹著獨處思婦之心,以至有“一嘆復一嘆”的哀嘆與“人樂我獨悲”的相思與悲傷。
梁武帝《襄陽蹋銅蹄》則與《壽陽樂》的寫法迥異,既寫了離別的愁苦,也寫相思的悲傷,更寫最終相聚的幻像,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喜劇故事: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第一首寫閨中少婦與情人的離別,第二首則寫她在春天里的相思,第三首又寫她與情人的相聚,由相別到相思、相聚,最后給人以喜劇故事的結局。雖然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失望的結局,但作者寧可相信從相別到相思,最終有相聚的想象,讓相思的女人陶醉于這種想象之中,也不讓相思的女人失望和悲傷。《三洲歌》更多一些想象的成份:
送歡板橋彎,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愿作比目魚,隨歡千里游。
湘東酃醁酒,廣州龍頭鐺。玉樽金鏤碗,與郎雙杯行。
《古今樂錄》云:“《三洲歌》者,商客數游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生意場上的商人總是“利”字在先,生活中的男歡女愛多是逢場作戲,并不十分在乎女人們的纏綿之情,但《三洲歌》中的這位多情女子送“歡”板橋彎,直到“三山隱行舟”,“歡”的船帆都看不見了,仍心有不甘,以想象化作比目魚而隨“歡”千里游,想象到湘東、廣州“玉樽金鏤碗,與郎雙杯行”的浪漫溫情,完全打破了鐘嶸《詩品·總論》所謂“離別托詩以怨”的抒情模式,離別反倒成為暢想未來恩愛甜美生活的契機。
其次,寫農村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清新自然而又含蓄蘊藉,雖然這類作品不多,但在西曲歌中卻十分顯眼,如《拔蒲》二首:
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與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荊楚之地于端午節為了驅邪避害,有掛菖蒲的習俗。這里寫一對正處在熱戀中的青年男女同去拔菖蒲,為了傾吐戀情,結果是“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清新含蓄,情趣盎然。與《詩經·周南·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的詩句相比較,雖然《卷耳》以思念征夫的婦女的口吻來寫,此處卻是一對青年男女陶醉在美好的愛情生活之中,但都是因情誤工,一個“不盈頃筐”,一個“竟日不成把”,隔代之詩,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唐代張祜仿《拔蒲》作《拔蒲歌》:“拔蒲來,領郎鏡湖邊。郎心在何處,莫趁新蓮去。拔得無心蒲,問郎看好無。”透過女子擔心男子另有新的吸引目標,要這位男子專一愛自己:“拔得無心蒲,問郎看好無。”確實另有一番情趣。
《采桑度》一曰《采桑》,描繪采桑女與情人一起采桑的情事,質樸自然,無復雕飾,也沒有《樂府詩集》中《陌上桑》與《秋胡行》曲折故事所表現的道德主題,卻鄉味濃郁。《唐書·樂志》曰:“《采桑》因三洲曲而生,……梁時作。”《古今樂錄》曰:“《采桑度》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即非梁時作矣。”無論是否為梁代之作,但它確是西曲歌中少有的幾首描繪農村男女之間自然之情的情歌:
冶游采桑女,盡有芳春色。姿容應春媚,粉黛不加飾。
春月采桑時,林下與歡俱。養蠶不滿百,那得羅繡襦。
采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
美麗的采桑女與心上人一起去采桑,粉黛不施,一如平常,“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也寫得極其自然。還有《作蠶絲》以農村常見的蠶絲說事:
蠶春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捐,纏綿自有時。
素絲非常質,屈折成綺羅。敢辭機杼勞,但恐花色多。
以蠶絲的纏綿、花色,妙合雙關,表達出一個女子憂心男子為眾多“花色”所誘惑,正合于民歌風味。《作蠶絲》與《采桑度》中的女主人公的表現,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保存了民歌本真的風味。不無遺憾的是,由于荊、襄、郢、鄧濃厚的城市商業生活,吸引了販運途中的商人、估客、游子,從而沖淡了農村田園生活色彩,以致于人們忽略了這類農村情歌的搜集,“所謂南朝民間樂府,稍具有鄉村意味者,惟上數曲而已”[2](P234)。
其三,通過描寫特別的節俗,表現女性歡快之情的,也別具風味。如《江陵樂》:
不復蹋踶人,踶地地欲穿。盆隘歡繩斷,蹋壞絳羅裙。
不復出場戲,踶場生青草。試作兩三回,踶場方就好。
陽春二三月,相將蹋百草。逢人駐足看,揚聲皆言好。
暫出后園看,見花多憶子。烏鳥雙雙飛,儂歡今何在。
詩中描繪出古代江陵的踏歌習俗,踏地為節,邊歌邊舞,是一種以自娛為主的群體舞蹈。《古今樂錄》曰:“《江陵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杜佑《通典》曰:“江陵,古荊州之域,春秋時楚之郢地,秦置南郡,晉為荊州,東晉、宋、齊以為重鎮。梁元帝都之有紀南城,楚渚宮在焉。”江陵自古有陽春二三月婦女群體出門踏青的習俗,這四首詩就是表現婦女們踏青時,邊歌邊舞的熱鬧場面與歡快心情的。婦女們放開腳步,盡情歡樂,以至于“踢壞絳羅裙”。歌舞的熱鬧場面也引起了“逢人駐足看,揚聲皆言好”的贊賞,但在詩的結尾處寫到這位女子在歌舞的熱鬧過后,自己還沒有如烏鳥那樣成雙成對,又不免留下一種失落之感,用筆真實生動。
江陵踏歌興起于漢代,發展于南朝,興盛于唐代,如劉禹錫《踏歌行四首》就對江陵的踏歌習俗有過生動的描繪。與《江陵樂 》相較,劉禹錫更注重描繪春江月出,大堤女郎連袂踏歌的場景與楚宮故地的地方特色,而沒有在意西曲《江陵樂》所重在“烏鳥雙雙飛,儂歡今何在”的言情色彩。
其四,最能反映西曲歌尚情特點的還是那些直接描繪兩情相悅,男歡女愛之情的作品。如《孟珠》,又名《丹陽孟珠歌》: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游冶郎,恨不早相識。
望歡四五年,實情將懊惱。原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
將歡期三更,合冥歡如何。走馬放蒼鷹,飛馳赴郎期。
這幾首民歌本是當時明白曉暢的民間歌曲,但由于時代的遙遠,有些詞句尚不易明白,于是蕭滌非先生有一個說明:“實情猶言委實,將歡,猶言與歡。合冥,猶言合昏,謂天已全黑。冥與暝通。按《讀曲》歌云‘合冥過藩來,向曉開門去’,則‘合冥’亦當時常言。”[2](P236)從《孟珠》中所引四首詩中我們不難感受到有情人表達情感的直白。第一首寫女子為俊男所吸引,從而證明了美貌、英俊是產生情愛的第一要素,正如后來韋莊《思帝鄉》所謂 “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終被無情棄,不能羞。”第二首表白得更大膽,將四五年積累的情思化作“原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的意念;第三首有了實現約會的最終結果,于是乘著傍晚而“走馬放蒼鷹,飛馳赴郎期”。從愛慕之情的產生,到想象親熱的表達,再到約會的最終實現,自然抒寫,水到渠成,作者向我們敘述的就是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
西曲歌的形式特點,是體制小巧,大多為五言四句,語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說“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清妙的民歌隨口唱來,不假雕飾,無需做作,便將內心深處細膩纏綿的情感真切地表現出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數抒情長詩《西洲曲》。這首民歌可能經過文人的加工潤色,內容是寫一個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間穿插著不同季節的景物變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動、服飾及儀容的點染描繪,一層深過一層地展示人物內心的情思,將那種無盡的相思表現得極為細膩纏綿而又委婉含蓄。全詩以“蓮”雙關“憐”,以“絲”雙關“思”之類的同音字,不僅使得語言更加活潑,而且在表情達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句式上四句一換韻,又運用了連珠格的修辭法,從而形成了回環婉轉的旋律。這種特殊的聲韻之美,形成似斷似續的審美效果,這同詩中續續相生的情景結合在一起,聲情搖曳,余味無窮。所以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說:“《西洲曲》搖曳輕,六朝樂府之最艷者。初唐劉希夷、張若虛七言古詩皆從此出,言情之絕唱也。”沈德潛《古詩源》卷十二說此詩:“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似絕句數首,攢簇而成,樂府中又生一體。初唐張若虛、劉希夷七言古發源于此”。這首詩是西曲歌中藝術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以至于對唐詩產生了深遠影響。
西曲歌寫情的手法多樣,內涵豐富,應特別稱道的是其中《莫愁樂》描繪了一位真實歷史人物——莫愁女。《唐書·樂志》云:“《莫愁樂》者,出于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由此可知《莫愁》從《石城樂》演變而來,可能產生于《石城樂》同時或稍后。《古今樂錄》亦云:“《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樂府解題》亦特別作了辨證:“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莫愁樂》兩首為: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據民間傳說,莫愁女姓盧,名莫愁,生活于楚襄王時代,善歌舞,先聞名于民間,后入楚王宮中,歷盡磨難,最終又回到了民間。莫愁女的許多傳說故事,也從西楚傳播到東吳。在鐘祥,則留下了莫愁村、莫愁湖、莫愁渡等名勝古跡。關于莫愁的動人故事流傳甚廣,皆為歷史人物莫愁女衍生而來。《莫愁樂》兩首自然質樸地描繪了一位民間多情女子的形象。作品并不著筆于細節刻畫,而是言莫愁女的生活之地,與人們近距離的親切感受,言莫愁女與情郎相別時的情態,她仿佛就在我們的眼前,如清水芙蓉,親切可人。由于莫愁女形象的深遠影響,以至于在郢中之地的民間有“家家迎莫愁,人人說莫愁,莫愁歌一字,恰恰印心頭”之說。后世關于莫愁女的詩詞歌賦眾多,民間傳說不斷,而西曲《莫愁樂》則是其中最為感人最具情味的作品。
西曲歌中,情思纏綿的主角總是女性,她們中間既有農婦、商人婦,也有官吏的妻妾,還有家妓、歌女、舞女,既有戀愛中的少女,也有失婚的女子,這些作品以反映她們的思想情感與生活遭際為主要內容,但總不出一個“情”字。
二
西曲與吳歌相比較,雖然同樣寫情,二者甚有差異。從身份上看,吳歌大都是上層社會的女子。如《子夜四時歌·春歌》中的兩首:“珠光照綠苑,丹華粲羅星。那能閨中繡,獨無懷春情。”“鮮云媚殊景,芳風散林花。佳人步春苑,繡帶飛紛葩。”《子夜歌》中的“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口珠發艷歌,玉指弄嬌弦”,住在豪華的園林香閨之中,或繡花,或散步,或彈琴,西曲中沒有這樣的描寫。西曲中的女子大多是平民。最典型的如《安東平》:
凄凄烈烈,北風為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
吳中細布,闊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余有三丈,為郎別厝。
制為輕巾,以奉故人,不持所好,與郎拭塵。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與郎相知,當解千齡。
這位勤儉持家的女子用吳中細布為郎作袴,剩下的三丈,打算為郎作條輕巾為郎拭塵。從“拙手所作”,可知女子親歷親為,這樣的女子在吳歌中是找不出的。吳曲中雖然也有如《讀曲歌》“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愿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之類的激烈之詞,但更多的是“綺帳待雙情”、“腹中陰憶汝”、“慎莫罷儂蓮”、“是儂淚成許”之類的吳儂軟語,更多的是嬌媚女人的萬種風情,如《子夜歌》:“宿昔不梳頭,絲發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氣清明月朗,夜與君共嬉。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諸如此類的大量描寫,表明情調上與西曲的差別所在。因此,從情調上看,吳歌中的女子纏綿多情,性格溫柔,風情萬種;西曲中的女子,勇敢果斷,性格堅強,自然質樸。
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問相隨否,不計道里長。(《襄陽樂》)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愿作比目魚,隨歡千里游。(《三洲歌》)
聞歡下揚州,相送京津灣;愿得篙槽折,交郎到頭還。(《那呵灘》)
望歡四五年,實情將懊惱;愿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孟珠》)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風慮。橫篙擲去槳,愿倒逐流去。(《楊叛兒》)
布帆百余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歡還。(《石城樂》)
這些歌詞直抒胸臆,爽快淋漓,不受禮法約束,情感表達自由而充分。這些話絕非千金小姐或貴族婦女之所言說,只有如普通下層婦女才能有如此干脆果決之詞。所以劉大杰先生指出:“吳歌艷麗而柔弱,西曲浪漫而熱烈,其內容雖同為男女戀愛的描寫,其作風卻有不同的情調。”[3](P32)
產生吳歌與西曲的差異性,原因有多種。
首先,與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關系甚大。永嘉之亂造成中原漢人的大量南遷,據《宋書》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州郡》記載:“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晉、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遣民南渡,并僑置牧司,非舊土地。”大規模的“遣民南渡”,形成荊、揚二州人口激增,《宋書·何尚之傳》所謂“荊、揚州,戶口半天下”,必然產生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西曲歌中雜有中原曲調,從而直接影響其審美情調也就成了很自然的現象。
其次,與當時南北對峙的政治形勢關系最為重要。建業乃南朝國都,帝王、貴族集中之地,而荊、郢、樊、鄧遠離中央,與北方民間在商貿方面的交流比較多,雖然梁元帝蕭繹曾建都江陵24年,但后被西魏與北齊夾攻,江陵滅亡,在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169年的時間之中,時間是比較短暫的。荊雍本是南朝漢人和北方胡人邊境相接人口雜居之地,人文環境自然受到北方文化的影響要多于建業,因此吳歌中的女子珠光寶氣,雍容華貴,柔媚者甚多,西曲歌中的女子勇敢果斷,性格堅強,自然質樸的一面接近北方民歌,與受其影響不無關系。
當然,從抒情的主要特點而論,吳歌與西曲互為影響,有著更多的共同點,同為水鄉澤國的自然環境,相同的語用詞匯及表達方式,有時使人難以區分。楚與吳的關系在歷史上總是“吳楚”聯稱,不僅地緣上“吳頭楚尾”相聯,甚至楚語和吳語都曾被看作同一種方言。陸法言《切韻》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陸德明《經典釋文》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淺,或滯于沉濁。”這里的“河北”指 “燕趙”,“江南”指“吳楚”,可見吳楚語言文化的同源性。正因為如此,二者經常混淆,如吳歌中的《黃竹子歌》:“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槳,得娘還故鄉。”本為《江陵女歌》:“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樂府詩集》注引唐代李康成的話說:“《黃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時吳歌也。”《樂府詩集》鮑照吳歌三首,描述的曹操的軍隊在夏口被孫劉聯軍打敗,“夏口”卻是西曲的地區。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五引西曲《雙行纏》,卷五、卷六引西曲《月節折楊柳歌》,卷十引西曲《江陵樂》,均把它們喚作吳歌。因此可見,吳歌西曲總體風貌比較一致,尤其是尚情的美學特點則是相同的。
[1]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6.
[2]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4]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責任編輯 韓璽吾 E-mail:shekeban@163.com
I207.2
A
1673-1395(2011)01-0001-05
2010 10 -20
梁惠敏(1958—),女,湖北荊州人,副教授,主要從事荊楚民歌與聲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