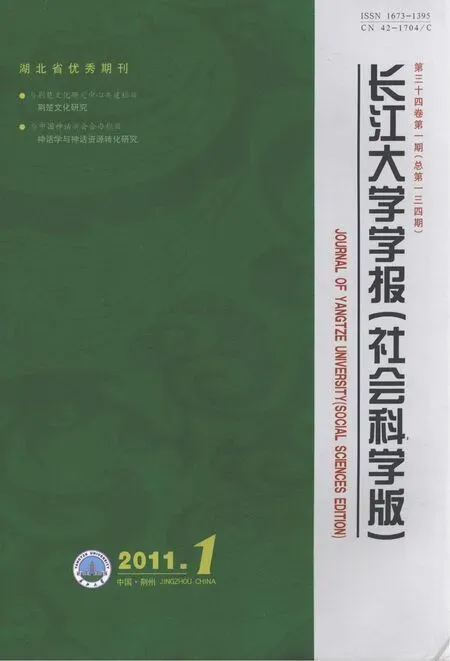古代小說和戲劇中的愛情與死亡之關系
李根亮
(長江大學文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古代小說和戲劇中的愛情與死亡之關系
李根亮
(長江大學文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古代小說和戲劇中描寫的愛情經常與死亡發生聯系。愛情因死亡越發顯得凄美和沉重,死亡也成為衡量愛情堅貞與否的標志。
古代小說;古代戲劇;愛情;死亡
愛情是美麗的,但在強大的外力面前,有時卻表現得非常脆弱,以至于不得不以無奈的死亡來與其對抗。如在中國古代的小說與戲劇中,既有喜劇的大團圓愛情故事,也有以死亡為結局的愛情悲劇。而文學家將死亡與愛情聯系在一起,恐怕不僅僅是出于純粹的敘事技巧上的原因,也許更多的是為了將生活中的真相揭示出來。愛情因與死亡聯系在一起,越發顯得凄美和沉重,同時,死亡也成為衡量愛情堅貞與否的標志。在人們內心深處,超越死亡的愛情,越發顯出其光輝。
一、超越死亡的愛情
人類將愛情與死亡聯系在一起,并非樂見青年男女為愛情而主動死亡,只是渴望一種不因死亡而恐懼,不因死亡而猶豫,不因死亡而背叛的真誠且忠貞不渝的愛情。這種超越死亡的愛情在現實生活中太難得了,因而不斷被文學家所關注,甚至于被夸張描述。在中國古代小說與戲劇里,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其中的主人公為愛而死,又為愛而活;或者人鬼相戀相結合,直至死而復生。這是一種超越生死界限的愛情,既現實又浪漫。
干寶《搜神記》“紫玉”篇敘述了吳王夫差小女紫玉與韓重生死不渝的愛情故事。吳王夫差小女紫玉與韓重相愛,并私下“許為之妻”。韓重外出之前請其父母向吳王夫差求婚,然而“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韓重外出三年后歸來,聽說紫玉已死,就到其墳墓前祭奠紫玉,并與其同到墓中,“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在這篇故事里,作者的原意其實是在表達一種鬼魂實有的觀念,但客觀上卻稱贊了一種超越死亡的愛情。我們從中既看到了中古時代冷酷的現實,也隱約體會到當時社會人們內心世界的某種精神渴望。
這種超越死亡的愛情,不但發生在未婚男女之間,也出現在已婚夫妻之間。漢代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所寫焦仲卿與劉蘭芝夫妻之間的愛情即如此。焦母棒打鴛鴦,將劉蘭芝趕出焦家后,夫妻二人先后自殺。他們自殺的原因,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僅僅是因為道德上的緣故,若沒有忠貞不渝的愛情,他們要走向死亡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所以,當他們死后,作者幻想讓他們重新結合。
明代戲劇《牡丹亭》寫了一個貴族少女杜麗娘因夢而亡,然后死而復生的愛情故事。杜麗娘長期深居閨閣之中,接受著嚴格的封建倫理道德規范的教育,但仍免不了思春之情,夢中與書生柳夢梅幽會,隨后因情而死,死后之魂再與柳夢梅結合,并最終還魂復生,與柳在人間結成夫婦。湯顯祖寫這部戲的用意在其“作者題詞”里說得很明白:“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顯然,作者表彰了一種“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超越死亡的情感。當然,在湯顯祖的觀念里,這種情感的內涵比較復雜,不過主要還是以男女相知相悅之愛情為核心。
古代文學描寫的這種超越死亡的愛情,其實質乃是最人性化的情愫,因而不斷地感動著后代的讀者,但同時在哀傷之余,又給人以幻想的滿足。
二、杜十娘之死與青樓女子的愛情
超越死亡的愛情畢竟是一種浪漫的幻想,而現實中的愛情有時就往往不那么浪漫。愛情一旦真的與死亡聯系在一起,恐怕就是一場撕心裂肺的凄慘悲劇。如古代文學經常描寫的青樓女子與士人的愛情故事,因為她們低賤的身份,她們的愛情往往遭到致命的打擊,等待她們的要么是不幸被拋棄,要么是死亡的命運。對于她們而言,真誠的愛情也許是一件奢侈品。
唐人傳奇《霍小玉傳》描寫了妓女霍小玉與士子李益的愛情悲劇。霍小玉對李益的才華傾慕已久,通過鮑十一娘的介紹得以與其相識相戀。不過,霍小玉對于自己的愛情能否持久下去,始終充滿憂慮,于是向李益祈求八年的歡愛:“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壯士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愿畢此期。然后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為晚。妾便舍棄人事,剪發披緇,夙昔之愿,于此足矣。”可是這種執著、乞求得來的愛情,很快被冷酷的現實擊得粉碎。李益得官后,聘表妹盧氏,與霍小玉斷絕了來往。霍小玉思念成疾,在豪士黃衫客的幫助下,見到了李益,誓言死后必為厲鬼報復,隨后“長慟號哭數聲而絕”。
像這種“癡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是古代社會常見的現象,況且女主角又是妓女的身份,因而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可是,作家何以一定要將女主人公寫“死”呢?第一,這樣描寫突出了女主人公的癡情和純潔。盡管妓女的身份讓人有一種“不潔”的感覺,但妓女的愛情也是人的愛情,甚至比世人的情感更純潔和忠貞不渝。第二,它強調了現實生活的冷酷,揭示了生活的真相,那些像霍小玉一樣身份的女子,要想獲得純真的愛情,并非易事,因為從人之常情來看,有身份、有地位的士人與妓女結合,畢竟是不體面的,若非當事人真誠相愛,且有沖破世俗習慣勢力的勇氣和毅力,其結局最終難免成為悲劇。
明代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也是類似的愛情悲劇。北京名妓杜十娘久有從良之志,后遇到李甲,“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十娘尋機離開妓院,完成了從良心愿。在與李甲一起回江南的路上,偶遇富商孫富。李甲擔心十娘不為嚴父所容,加上孫富的誘惑,李甲便以千金之資把杜十娘出賣。杜十娘得知后,萬念俱灰,隨抱百寶箱投江而死。
從小說的描寫中發現,杜十娘投江而死的原因,與孫富和李甲兩人的個人品質有莫大的關系。我們既看到金錢對純潔人性的腐蝕,也看到了社會習慣勢力和禮教觀念對人們行為方式的左右。這也是小說的重要思想價值所在。但若全面分析的話,造成杜十娘悲劇的直接原因,與杜十娘自身的性格、愛情道路上的選擇失誤,也有關聯。作為一個青樓出身的女子,杜十娘渴望有尊嚴的生活,而且渴望像普通女性那樣得到真誠的愛情,而不是用金錢換來愛情,這并沒有錯誤,只是她忘記了一個冷酷的現實,那就是她的風塵經歷和卑下的身份,這不是可以憑借個人的愛情力量能扭轉的。面臨著情人的最后背叛,依照杜十娘的性格發展邏輯,她只有選擇死亡,因為她已無路可走。她既不愿意再回去過那種與男人打情罵俏的無愛生活,也不愿意隨便找個男人結婚過庸庸碌碌的生活,卻又無法像才子佳人那樣陶醉于風花雪月的浪漫生活,所以她只有死亡。
從霍小玉到杜十娘,她們的愛情之所以失敗,與她們的風塵經歷有必然聯系。她們面臨的不僅僅是封建禮教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文化習慣勢力,如果她們無法調節自身的精神需求,如果她們沒有足夠的運氣遇上一個好男人,也許只有她們的死,才會讓她們所愛的人為其愧疚流淚。
三、楊貴妃之死與帝王的愛情
對于歷史上帝王的愛情,人們始終抱有一種矛盾的心理,既羨慕其艷福不淺,又嘲笑其荒淫無恥。然而,拋開政治不談,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皇帝畢竟也是人,他們也有正常的情感需求,只是他們的情感,與現代人所說的愛情還有相當的距離,與其說是愛情,還不如說是好色風流。例如,皇帝與他們欣賞的女子,并不是處于平等的地位,因此他們之間的愛情常常不是以相知相悅為前提。皇帝是愛情的施舍者,女方更可能是被動的接收者,況且,多情的帝王還面臨著大量的外部環境壓力,甚至各種考驗和誘惑,由于這些多情的帝王們不會到只愛美人不要江山的地步,所以最后的結局,往往是他們喜歡的女子,遭遇到了比皇帝本人更大的不幸。
隋文帝楊堅與文獻獨狐皇后最初結合時,“誓無異生之子”(《隋書·列傳第一》),他們的婚姻是有感情基礎的,而獨狐皇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隋書》說獨狐皇后“性尤妒忌”,是在楊堅成了皇帝之后。《隋書·列傳第一》記載:
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于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余里。高颎、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
隋文帝感嘆自己“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是可笑的,因為他在感情上首先背叛了獨狐皇后,卻不反思自己的錯誤,反而以為他的風流好色是對的。盡管獨狐皇后隨意殺人的行徑令人可怕,但隋文帝無法保護好自己喜歡的女人,也是不可原諒的。由此可見,對于帝王的所謂愛情,實在有必要保持足夠的冷靜,尤其是對那些深陷其中的女人而言,但后代的文人墨客,對于帝王的風流韻事,卻不愿如此冷靜地描述。他們更喜歡夸大其辭,以理想化的眼光看待帝王的愛情,其中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最為文人津津樂道。
在歷史上,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情感糾葛始于翁媳亂倫。楊貴妃受寵后,其家族勢力開始強盛起來,尤其是其兄弟楊國忠把持朝政,使朝野均對他們充滿了怨恨。后來安祿山謀反,就“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楊貴妃最終成了唐朝政治的犧牲品。以今人的視野來看,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不能說完全是逢場作戲,只是這場愛情發生在了帝王身上,加上安史之亂的發生,人們有理由懷疑李楊之情究竟是愛情還是荒唐。而楊貴妃成為政治的替罪羊,既有道德文化傳統上的原因,也與楊家的飛揚跋扈有一定關聯,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楊貴妃之死又確實值得同情。
白居易的敘事詩《長恨歌》,就是從人性的角度來審視楊貴妃之死和李楊之間的愛情。詩人謳歌的重點是李楊之間的纏綿悱惻的愛情,以及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對楊貴妃的綿綿思念之情。最后,詩人將李楊的愛情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顯然,白居易美化了李楊之間的情感。
清代洪昇的《長生殿》一劇,將李楊的愛情放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上進行了描述,并賦予其新的內涵,從而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楊貴妃之死的無奈及其悲劇意義。作為文學家的洪昇和歷史家是不同的,他寫楊貴妃之死之所以更讓人同情,是因為他所描述的帝王的愛情更接近普通人的情感,而且在生死關頭,楊貴妃以國家利益為重,主動請死,這更贏得人們的尊重,所以,《長生殿》里的楊貴妃之死,有雙重意義:一為愛情,二為國家。
四、林黛玉之死與才子佳人的愛情
所謂才子,在古代文學作品里大多是指有才華的士子;佳人往往是指青樓女子以外的,一般貴族或士人家庭出身的,德色雙馨的女子。大部分古代文學作品寫到才子與佳人的愛情時,往往賦予其皆大歡喜的結局。這樣處理未必完全是錯誤的,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有相似的情形,但一味地寫成大團圓的結局,而且公式化,就難免使人感到單調且不完全符合實際;況且在古代社會,男女的交往并不頻繁,才子與佳人之間發生愛情并能順利地結合在一起,恐怕也不容易。既然才子與佳人的交往及戀愛如此困難,再加上外部環境的阻撓,悲劇就難免發生,男女主人公殉情而亡的可能性就大為增加。拋開文學家的幻想成分,像前文提到的《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之死,在真正的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復活的。死亡就是死亡,沒什么浪漫可言。人們渴望超越死亡的愛情,畢竟是一種奢望。
宋代以后出現的文言小說《嬌紅記》,以及明人孟稱舜據此撰寫的《嬌紅記》傳奇,就敘述了一場這樣的愛情悲劇。其中的男女主人公申純與王嬌娘雙雙死亡,為才子佳人的愛情譜寫了一曲挽歌。雖然《嬌紅記》最后也寫了申純與王嬌娘死后化為鴛鴦的情節,但從整體上看,其描述的重點仍著眼于現實的殘酷。
孟稱舜《嬌紅記》的目的是要寫一段“生死情長”、“情同鐵石”的愛情,而其死亡的結局使這段愛情顯得特別沉重。申純與王嬌娘的死亡,使我們看到了封建禮教強大的力量,尤其是嬌娘父親的固執簡直莫名其妙。這是現代人所無法想象的。即使你的愛情多么熱烈,即使你申純已經進士及第了,也有人們所難以預料的情景出現。你可以死亡,但你改變不了現狀。
與《嬌紅記》類似,《紅樓夢》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在題材上也屬于一種才子佳人式的愛情,但他們的愛情,卻以賈寶玉出家、林黛玉死亡為結局,其悲劇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林黛玉之死,留給人很深的印象。加上《紅樓夢》是長篇小說,作家也充分地對林黛玉的死亡心態、死亡歷程、死亡結局進行了細致描述。
林黛玉死前就經常想到死亡。如小說第27回,因與賈寶玉發生誤會,黛玉遂創作了《葬花吟》。該詩的主旋律其實就是死亡。林黛玉由花及人,感嘆春殘花落,實乃感嘆紅顏薄命、花落人亡。所謂花魂、鳥魂、香丘、艷骨、凈土之語,無不使我們聯想到死亡。林黛玉對于落花和死亡的詠唱引起了賈寶玉的共鳴與悲傷,從而激發了后者對人生的幻滅感。另外在小說第76回,黛玉與史湘云聯詩時所詠“冷月葬花魂”一句,更是悲涼頹喪。
在曹雪芹原來的構思里,林黛玉最后是以死亡為結局的。從小說開始提到的“還淚說”中看出,林黛玉是淚盡而亡,但如何死去,曹雪芹沒有說明。根據高鶚的續書,林黛玉是因為聽到賈寶玉與薛寶釵的婚事后,氣急而亡。那么在筆者看來,至少有兩方面的因素直接刺激了林黛玉并促使她主動放棄生命:一是她感到了寶玉對愛情的背叛(這其實冤枉了賈寶玉),她失去了人生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二是她失去了對外祖母賈母的信任,賈母也在關鍵時刻拋棄了自己的親外孫(盡管這樣寫明顯不符合曹雪芹的構思)。由于愛情和親情都無法得到滿足,林黛玉這樣一個自尊心很強的貴族少女,在絕望之余,就很容易走極端。至于林黛玉的健康問題,并非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從藝術效果上講,高鶚所寫的林黛玉之死,仍然是成功的。首先,它使我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封建禮教對自主愛情的漠視和不以為然。在小說第97回,林黛玉死前看到賈母時說:“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雖然難受,但卻說了一番令現代人可能要寒心的話:“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別的想頭,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所謂“做女孩兒的本分”,就是要守婦道,不能有“心病”,如果與男子有私情,則是大逆不道之事。親生的外祖母都如此對待自己的外孫女,又何況他人呢?家長對于子女的愛情既不理解,也不寬容,更談不上妥協了。其次,它清醒地讓人們看到才子與佳人們在追求自主愛情婚姻時的軟弱和無奈。林黛玉渴望愛情,但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賈寶玉身上,以及家長們的理解和施舍上,一旦失敗,唯求速死和自殘。而賈寶玉在得知真相后從不考慮挽救的方法,也不采取任何行動,只是無奈地接受現實。所以說,林黛玉之死,像申純和王嬌娘之死一樣,不過又是一曲才子佳人的愛情挽歌罷了。然而,從這首挽歌里,我們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愛情受到褻瀆而產生的悲劇和一往情深的心靈的痛楚”[1](P390)。
林黛玉近于自殘式的死亡,與女主人公“質本潔來還潔去”的人生價值觀念也有關系。當林黛玉發現自己信任的賈寶玉竟然也背叛了她的愛情時,她已經很難相信這個現實還有什么干凈純潔的土壤了,而且更不會去接觸別的什么“臭男人”。因為她不會像薛寶釵那樣隨波逐流,又不會像惜春那樣從宗教世界里尋求解脫,所以她只有像屈原那樣選擇死亡。從這個意義上說,林黛玉之死不僅僅是一個失戀女子的死亡,它甚至集中凸現了古代文人身上那種屈原式的文化人格精神。
以上關于古代小說與戲劇中死亡和愛情關系問題的分析思考,并非說明死亡與愛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只是在強調:古代社會文化環境對于自由愛情的成長,有明顯的阻礙作用。人類對愛情的追求,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經常遭遇失敗甚至死亡的結局,而死亡在無意中,也成為衡量人們對待愛情忠貞與否的標志,甚至表現出某種文化意義。
[1](保加利亞)基·瓦西列夫.情愛論[M].趙永穆,范國恩,陳行慧,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
責任編輯 韓璽吾 E-mail:shekeban@163.com
I206.2
A
1673-1395(2011)01-0026-04
2010 10 -12
李根亮(1964—),男,河南新密人,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