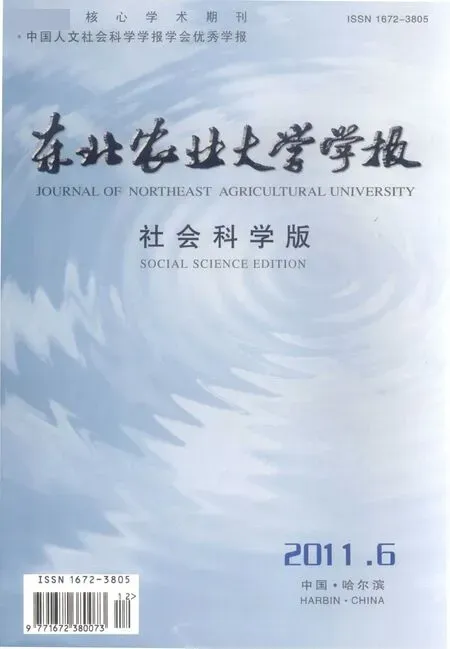影響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因素與策略構建
吳 玲 曹海英
(1.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哈爾濱150030;2.哈爾濱金融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30)
影響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因素與策略構建
吳 玲1曹海英2
(1.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哈爾濱150030;2.哈爾濱金融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30)
在城鄉統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探究農民工城市社會的適應性,分析了制度因素、社會因素及個人因素對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影響與障礙,提出了重塑社會價值理念、推動制度創新、變革城市社會組織機制、重構個體網絡支持系統等推動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策略,保障社會變遷中的社會整合和秩序,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有效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戰略。
農民工;城市適應;影響因素;策略
一、問題的提出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里指出:“20世紀50年代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入口處,這就是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這一預言目前已經成為中國面臨的現實,在具有中國特色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驅動下,2億多中國農民工正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遙望著工業文明象征的城市。
農民工現象出現的中國意蘊。農民工作為當今中國最具特色的一個社會群體,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中的發展和進步。在中國現有的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下,農民城市遷移具有特殊的路徑,歷經了農民成為農民工、農民工成為市民的兩個發展階段。農民工成為市民化的一種過渡形態,在城市的新環境下繼續社會化,實現了職業的非農轉變、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社會關系的重構、現代社會意識和心理的調試,這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社會結構變遷的不徹底性、艱難性。從農村到城市,在地理空間意義上或許僅有一步之遙,而從農民到市民,在社會空間意義上卻有相當長的路途要走,需要全社會從思想觀念到行為方式、從心理意愿到制度變遷的全方位轉型。現實表明,農民工群體徘徊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法適應與融入城市社會,因此,有效鞏固和擴大這一現有成果,推動農民工從過渡形態向終極形態演進至關重要。
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事關我國城市化、現代化的實施。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工的城市化。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目前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49.68%。中國在21世紀要實現社會大發展,農村人口必須大幅度向城市遷移,但能否被城市社會所接納,或同化、融合,或并存,或嵌入,或邊緣化,始終存在一種空間的秩序和運作邏輯,存在著定居城市抑或回流農村的雙向選擇。如何保障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關系到城市化、現代化的有效實施。
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2009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農民工作為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是我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第一功臣(龍永圖,2008)。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2%;在加工制造業從業人員中占68%,在建筑業從業人員中占80%。如果社會長期讓一個如此龐大的人群邊緣化,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難以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久之勢將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研究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引導和推動農民工適應城市社會,將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二、影響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基本因素分析
1.制度因素
老一代農民工是城市的“過客”。以戶籍制度為標志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是農民城市適應的最大成本和障礙。由于戶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制度、醫療制度、子女教育、社會福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生存和發展的成本提高,融入城市社會的難度加大。農民工大多從事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給城市居民帶來方便,促進了城市經濟發展,但他們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權益受損,子女在城市難以入學。在此制度背景下,相當一部分具有“自知之明”的老一代農民工認為,城市只是謀生的地點和場所,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隨著年齡增大,他們選擇回流農村,中斷城市化。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城鄉“邊緣人”的可能。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相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態度與老一代農民工迥然不同。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對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有著更強的憧憬和向往,渴求改變農民身份;基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傾向于長期居住城市,對城市的認同超越農村;打工的目的不僅是基于生存需要,而且更多關注未來發展的契機;關注自身價值實現,渴望被他人尊重和社會認可。但在城鄉二元分割制度沒有被徹底打破之前,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有著類似的社會境遇,甚至面臨更為迫切的城市適應與市民化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與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約,在城市中難以獲取穩定的、高收入的工作,位于城市社會的底層;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消解著他們對農村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也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在農村社會又處于邊緣位置。在現階段的制度安排下,他們向往城市,卻不被接納;根在農村,卻日益疏遠。倘若一旦在城市無法實現立足,他們也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務農,比起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會變成既融不進城,也回不了鄉的“邊緣人”。新生代農民工必須市民化,這事關城鄉社會的穩定、和諧與可持續發展,而這需要破解制度困局。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2.社會因素
社會歧視。戶籍性質不同所帶來的不平等意識是城里人對農民工歧視的主要原因。日常生活中城里人對農民工的歧視行為主要有:語言輕蔑,有意回避,職業排斥(包括就業崗位方面的歧視、勞動報酬和社會福利、生活待遇上的歧視)、人格侮辱、執法歧視等。農民工對歧視非常敏感,并把部分城里人的歧視行為泛化成所有城里人一致的態度,從而泛化了對城里人的敵視、冷漠,對城市疏遠,無形中化解了自身參與城市社會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阻礙了對城市生活的適應和融入。
社會沖突。農民工對城市不滿情緒的積聚,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化為激烈的社會沖突。近年來,農民工與廠方之間的勞動爭議呈上升趨勢,上訪、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農民工與城里人的沖突也時有發生,如買賣中的糾紛、公共場合的爭吵和打斗等。城市下崗人員與農民工競崗而導致的利益沖突也時有出現,這些雖然是小摩擦,但造成的影響常常泛化為群體敵視。由于農民工的弱勢地位,沖突最終的受害者總是農民工,從而造成農民工不是個人城市化的短暫中斷,就是對城市不信任感的加深,或兩者兼有。
社會交往的局限性。與城里人交往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的主要途徑。城里人并不熱衷與農民工的互動,這使得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具有同質性、表層性、工具性、不對稱性、被動性等特點。農民工與城里人交往更多的只是業緣、地緣關系,較少情感上的溝通與交流,更多的是與同鄉、親屬、朋友以及與自己身份近似的農民工交往,社會交往具有明顯的封閉性,缺乏城市特質。由于農民工文化適應力弱,加上城市的排斥,農民工本身也產生排斥和抗拒心理,回避與城里人交往,固守在狹隘的初級交往圈和同質性網絡,客觀上形成了社會隔離狀況,出現了“城市中的村民”。而“村民”心態使農民工對城市無法產生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只有自卑的“陌生人”感覺,如果得不到適當的處理,會妨礙農民工在城市的正常生存和發展。
3.個人因素
人力資本因素。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因素對于城市適應有著重要影響。人力資本中首推受教育程度。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與鄉村的聯系就越弱,留城傾向就越強,并給農民工接受新事務的速度、人際交往、心理調適等適應城市生活方面帶來很多直接、有益的影響。
經濟因素。經濟狀況是農民工考慮是否居留城市的關鍵因素。火車票、汽車票價格的提高,使他們盡量減少往返于城市與鄉村的次數;一定時期的失業常把理性的他們推回農村;收入偏低、工作不穩定使他們對城市文化娛樂活動持不參與態度;擁有較多經濟資本,在城市的活動空間就大,發展機會就多,從而能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
心理因素。老一代農民工出生并生活在農村,有著較濃的鄉土意識;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并在城市長大,但身份是農民。他們在城市謀生,受到都市文明與外來文化的沖擊,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明顯兼有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性、不平衡性。老一代農民工戀土和離土的矛盾情結:一方面懷念故土,不愿背井離鄉;另一方面,城鄉差距激發他們離土進城,但在城市扎根的意識不強。新生代農民工自信和自卑的矛盾心理:城市生活的豐富與高品質,使農民工找到了自信,不愿意回到農村;城里人的歧視使得農民工充滿憤怒與自卑,又使他們難以適應城市生活,徘徊在農村和城市之間。
家庭因素。農民工如果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轉移,原有土地將喪失,轉移成本增加。為了降低轉移成本,保留原有土地和農業收入,大多數轉移以勞動者個人或夫妻為主,老年人和兒童居于原地,從而導致轉移的脆弱性和不徹底性,影響個人的城市化進程。雖然近年來農民工家庭化流動的趨勢增強,但是受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影響,很多農民工家庭無法承受子女在城里接受教育的昂貴費用,被迫把子女放在農村家里撫養和接受教育。父母與子女相分離使得部分農民工經常往返城鄉之間,影響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適應。
三、推動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策略
保障農民工城市適應是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系統工程,主要包括重塑社會價值理念、推動制度創新、變革城市社會組織機制、重構個體網絡支持系統,這四個子系統之間相互支撐,共同構成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社會支持結構,加速其融入城市社會的進程。
1.重塑社會價值理念
政府主導的公正。政府執政理念必須體現對社會公正的維護。農民工作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者,政府必須給予公正對待,為農民工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和生活環境,并引導和控制不利于農民工獲得公正待遇的社會環境因素。農民工是一個弱勢群體,政府執政理念必須體現對社會公正的維護,以保障農民工基本國民待遇為中心,任何一項制度和政策的設計都不能以損害農民工利益為代價。
媒體報道的客觀。媒體要大力宣傳國家對農民工實施的各項制度與政策,使其知曉并學會利用政策維護自身權益。媒體應倡導全社會關注農民工的社會氛圍,讓農民工的真實生活和心理寫照呈現在公眾面前,改變城里人對農民工的歧視與偏見。媒體發揮自身應有的監督權,對危害農民工權益的現象進行曝光和批判,體現自身的社會責任。
社會公眾的支持。農民工要融入城市社會,最終要獲得城里人的理解和認同。城里人應該以平和的心態看待農民工,克服自身的優越感,充分認識農民工對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農民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城里人需要對其關心和幫助。農民工也應充分培養自信和自尊,強化權利保護意識。
2.推動制度體系創新
改革戶籍制度。這一目的是要變“城鄉分治”“城鄉兩制”的戶籍制度為城鄉統一、一視同仁的人口管理制度。通過改革戶籍制度,給予農民工向城里人轉變的一種準入機制,使其合法獲得市民身份,享受國民待遇。可采用國際上通用的按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徹底取消現行戶口所具有的身份、待遇和登記差別的特殊功能,使戶口不再成為一種制度性身份。
變革勞動就業制度。這一目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制度環境,給予農民工平等競爭權,在市場經濟原則下自由流動、自主擇業,享有合法權益,逐步形成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政府要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秩序,強制性要求用工單位和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并履行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健全農民工就業權益保護制度,切實保障農民工在勞動就業中的基本權益。
創新教育制度。其目的是為農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機會。流入地政府要放開城市公辦學校的就學門檻,讓農民工子女就近入學,取消針對農民工子女的不合理收費;鼓勵和支持民辦學校及民工子弟學校發展,通過財政投入、師資投入等方式幫助學校規范化辦學。流出地政府要重視農民工留守子女受的教育問題,通過建立寄宿制學校使其在教育、生活、安全等方面得到保障。
健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使農民工在遭遇失業、工傷、醫療、養老等問題時能夠得到保障。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應該享有與城市工人一樣的社會保障待遇,保險基金應由企業、個人共同交納,國家給予政策性扶持。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建構,既要考慮到與當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又要考慮到農民工流動性強、工作不穩定等特點,使這一制度能夠滿足農民工進入制度方便、退出制度自由、城鄉銜接容易的要求,打造全國聯網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網絡化管理平臺。
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其目的是要實現農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農民工獲得個人經濟補償,解除了后顧之憂,安心在城市打工與創業,同時土地配置效率提高,促進了規模化經營,實現了個人與社會雙贏。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一要明晰農村土地產權,保障農民工土地承包關系長期化,擁有土地相關權益;二要建立土地使用權市場交易制度,為流轉土地提供規范的交易平臺。
3.變革城市社會組織機制
公正的工作單位。工作單位要切實保障農民工權益,做到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同工同權,使農民工享有與城里人一樣的權益。工作單位應把農民工深層次地納入業緣關系網絡中,通過開展有意義的文化娛樂活動,創造農民工與本單位城市職工交往交流的機會,營造公平、信任、友愛的企業文化氛圍。
維權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與工作單位之間存在著一種依存關系,往往將農民工排除在工會組織之外。因此,一要將農民工納入工作單位內的工會組織,因為農民工是產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二要組建農民工工會,這是針對工會組織的一種補充和嘗試,由農民工自己擔任工會各領導職務,不依附于任何單位。
和諧的社區組織。農民工在城市是以特定的社區為基本生活空間,社區組織應該將他們納入社會管理和社區服務,培養其社區歸屬感。一是要把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子女教育、勞動就業、婦幼保健、衛生防疫、法律服務和社會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各有關部門和社區管理責任范圍,并將相應的管理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二是提供必要的生產、生活幫助,積極組織農民工參與社區文化娛樂活動,促進與城市社會的融合。
發展的自治組織。自治組織是指農民工組建自我管理的社會組織形式。目前的自治組織主要包括農民工協會、農民工同鄉會、農民工行業協會、農民工興趣協會等。但是這些自治組織沒有固定的場所、穩定的經費和專職人員,在開展活動、維護農民工權益時力不從心。國家應該在政策上對農民工創建自治組織提供扶持,適當降低創建條件;所在單位要支持農民工創建自治組織,在資金、場地上予以幫助,并引導自治組織向良性方面發展。
利他的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NGO)是一種獨立于國家、政府力量之外的非營利性群體組織,包括慈善組織、志愿者組織、社會團體及“草根組織”等,在農民工培訓、權利維護、權益意識增強等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應該鼓勵和支持為弱勢群體代言的非政府組織,它不僅維護農民工等社會群體權益,同時也倡導社會公平與正義,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4.重構個體網絡支持系統
鞏固同質性網絡。農民工進城一般是依靠強關系來提供信息和幫助,在遇到問題和困難時,他們也傾向向這些人尋求支持和幫助。因此,以血緣、地緣關系為主的同質性關系網絡對于農民工在城市中更好地工作、生活給予了極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并能起到其他機構和團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進一步鞏固己有的血緣、地緣關系十分必要。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城市社區都要為此提供必要的幫助,架設交流平臺。如可以為外地同鄉農民工舉辦某些形式的聯誼會、聯歡會等,創造農民工之間相互交往、溝通的平臺。
拓展異質性網絡。農民工與城里人缺乏交往,既不利于農民工深度融入城市社會,也不利于城市社會的和諧。因此,有必要拓展農民工的交往空間,擴大農民工社會網絡的規模,增強網絡異質性,不斷培養農民工的城市文明素質,使其做一個合格的新市民。當然,加強農民工與市民的交往,改善雙方之間的關系,并非易事,除了需要雙方的努力外,政府、工作單位和社區應該發揮應有的作用,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活動,讓農民工對城市社會、工作單位及社區等產生歸屬感,讓他們感覺到是真正地“生活”在城市中,而不僅僅是在城市中“打工賺錢”及“養家糊口”。
[1]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
[2]龍永圖.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第一功臣[EB/OL].http://news.66wz.com/system/2008/12/15/101018014.shtml.2008 -12 -15.
[3]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N].工人日報,2010-6-21.
[4]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R].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25~27.
The Factors and Tactics Affecting a Peasant Laborer Adapting to the City
Wu Ling1,Cao Haiying2
(1.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2.Harbin University of Finance,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adaptability of peasant laborers into the city;analyzes the effect and obstacle of system factors,soci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o make peasant laborers adapting to the city;proposes the concept of reshaping social values,driving the connovation of system,reforming the system of municipal community,rebuilding individual network supporting system to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adaptability of peasant laborers into the city,guarantee social integrity and order of social reform,push forward the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nd accomplish the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easant laborer,adapt to the city,factors,tactics
G912.3
A
1672-3805(2011)06-0055-05
2011-06-26
東北農業大學科學研究基金“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實證分析與政策選擇”(編號:20061122)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研究”(編號:20060390778)的階段性成果
吳玲(1970-),女,黑龍江綏芬河人,東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