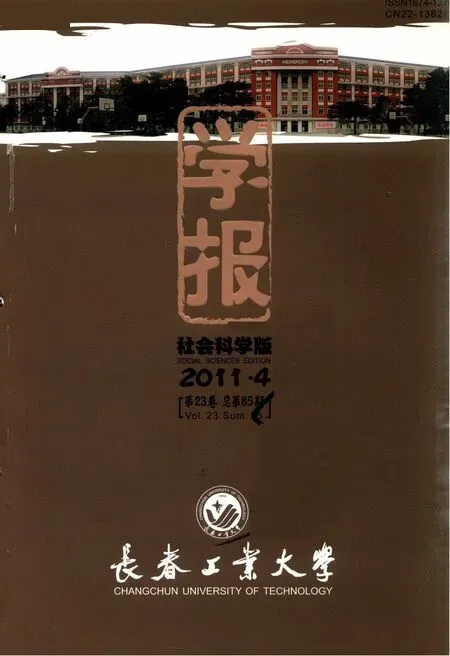網絡流行詞語衍生的制約因素探究
靳開宇
(綏化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黑龍江 綏化152061)
網絡流行詞語衍生的制約因素探究
靳開宇
(綏化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黑龍江 綏化152061)
以網絡流行詞語“很X很XX”和“被XX”為例,分析詞語結構特點,說明網絡流行詞語模式產生的三個主要制約因素:首先,交際者情感與審美功能的需要與實現;其次,不同于傳統的口語語體和書面語體的特點,網絡語體在傳播信息時具有的特殊性;最后,社會文化因素的推動作用。
流行詞;語體;情感功能;藝術功能
當前網絡流行詞語產生的速度和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本文僅以“很X很XX”和“被XX”模式為例,對網絡流行詞語衍生的深層制約因素進行分析闡釋。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柏森認為語言與其他現象的不同恰恰在于語言無法脫離開它的使用者而存在,他認為“人們被群體的語言習慣帶著跑,隨波逐流,而同時又可能不知不覺提供全新的東西,對此別人會采用并加以發展”。[1](P20)本文通過對流行詞語模式形式與功能特點的分析,從考察語言交際者和交際環境角度揭示了網絡流行詞語產生的主要制約因素。
一、新興網絡流行詞語的結構特點
黃伯榮、廖序東在《現代漢語》中把現代漢語詞匯系統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基本詞匯具有穩固性、能產性和全民常用性,是詞匯系統中最主要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一般詞匯,它的最大特點是具有靈活性,即動態性。“社會的急劇發展,在語言中首先反映在一般詞匯上。新詞總是先進入一般詞匯,然后有一部分可能進入基本詞匯。一般詞匯數量多,不一定為全民族的成員所普遍掌握。哪些人掌握哪些一般詞,情況不一樣”。[2](P260)我們將漢語流行語劃歸到一般詞匯中,正是基于流行語具有動態靈活性。當代漢語新詞語由于經由網絡媒介快速傳播的渠道從而具有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如果這類詞語在一定時間里被廣泛復制使用,那么這類詞語便具有了流行語的身份、資格。
隨著電子媒介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廣泛使用,當代漢語新詞語的產生路徑經由網絡傳播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得到大量復制。本文作者曾經選取了“很X很XX”和“被+XX”兩類網絡流行語進行詳細分析,可以看到雖然最初產生來源不同的流行語但是最終都通過網絡交流得到快速傳播,從而具備流行語在短時間內使用頻度高的主要特點。
例如“很X很XX”這一流行語模式最初來自于電視新聞采訪,其中的“很黃很暴力”這一語言形式最初就是從采訪中的現實口語交際中來,最后經過網絡視頻的廣泛傳播,以此類推出現了一系列象“很傻很天真”、“很好很強大”、“很丑很封建”、“很酷很瀟灑”等相同模式的流行語。這類流行語形式上是一個多音節結構,由同一程度副詞“很”重復使用構成兩個偏正結構,前后兩個偏正結構連用,音節形式上由雙音節過渡到三音節,詞語整體形式雖長,但是節奏停頓靈活,富于變化。
不同于“很X很XX”類流行語最初由口語交際中產生,由“被”字組成的一系列“被+XX”式網絡流行語,例如,被就業、被自殺、被自愿、被小康等詞語模式最初就是在網絡中使用然后被廣大網友關注和傳播的,廣泛使用后又從網絡交際中進入我們日常語言生活。日常交際中人們普遍更為熟悉使用的是“被字句”中“被”作為被動句式的標記功能,現今由“被”字組成的網絡流行語卻是以新的構詞方式出現,與以往“被告”、“被迫”、“被害人”等“被+XX”構詞方式不同,它具有兩個主要特點:(1)詞語的組合成分之間關系松散,結合不緊密,“被”與另一構詞成分可分可合;(2)與“被”組合的詞語成分中及物動詞比較少,但是構成成分可選擇的范圍更大,名詞、形容詞和不及物動詞都可以進入該模式中。
二、流行詞語模式產生的制約因素
(一)交際者語言功能的實現
詞語的價值在于它負載了意義,因而借助語言符號可以幫助人類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和情感需求,這就是語言形式完成的功能,從而達到為交際者服務的目的。
我們更熟悉的是語言幫助我們完成傳遞信息的功能,除此而外,語言還可以實現情感功能。語言的情感功能指的是人類利用語言間接實現了情緒情感的抒發。考察“被+XX”類流行語模式,我們發現“在這一成分組合結構模式中‘被’的高頻使用是整個結構強勢賦義的先導,使能夠進入這一結構的詞語都普遍具有了該結構凸顯的被動義”。[4](P50)能夠進入這一格式的詞語例如“寂寞、朋友、結婚、就業”等在詞義上具有[+主觀性、+自愿性]的語義特征,而組合后的詞語語義特征卻是[-非自主,-不可控],這就造成了詞語自身語義與結構整體上的不相容,需要使用者重新調整原有的社會認知心理模式,使詞語符合結構整體表義的需要,這些具備主觀自愿性的語義成分由于“被”的語義制約產生了新的語義即原本該是自主的行為現在是非自主的,而這些行為明明只能是本體自主發出的,無法被動發出。這樣看似矛盾的組合正是通過組合上的超常搭配凸顯了語義上的被迫性,從而完成語義上的重新整合,因此這類網絡流行語一經產生就由于強烈的情緒表達被網友廣泛復制使用。
另一方面,人類創造語言符號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活動,當我們的注意力是符號本身而不是符號傳遞的信息,也就是我們像欣賞時裝表演、欣賞文學作品一樣看待符號形式本身具有的特點時,我們其實是在欣賞符號自身的結構,例如平仄搭配、押韻、語言結構上的對稱等語言的形式特點。通過這一方式滿足人類審美心理的需要,這就是語言實現的藝術功能。作者認為“很X很XX”這類網絡流行語“表面上是對現代漢語雙音節詞匯形式的叛離,實際上體現的正是人類保守與創新內在動力的不斷抗爭,保守的力量在維持著語言約定俗成的效率,而創新的本性又驅動人類不斷豐富和尋找更有生命力的語言表達形式,所以新形式的出現是語言發展的必然”。[4](P94)
(二)網絡語體的特殊性
語言是為人服務的,所以語言功能實現實質上是人的自身需要的實現,在現實的交際中就是交際者自身的需要和交際目的實現的需要。網絡流行詞語產生除與此有關之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到詞語產生的語言環境——是在網絡交際的過程中產生的。網絡作為一種特殊的電子媒介,不同于我們傳統的的語言具有與我們口語和書面語不同的語言風格特色,呂明臣等學者把這種在網絡語言使用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語體稱為“網絡語體”,[5](P32)這種語體的主要特征就是交際時具有視覺性、即時性和非面對面性,因此帶來了這種語體風格特點是自由、輕松和娛樂性。
因為網絡語言交際時尤其偏重視覺性(可觀賞性),所以它很多時候可看性很強,這不同于現實的口語交際,它偏重了書面語的特點,但又不同于書面語的莊重、凝練與典雅的語言特點,它以情感宣泄與娛樂效果的實現為主要目的,所以像“被+XX”、“很X很XX”等字數很多的詞語結構都可以在網絡中使用,“詞”與“語”的界限使用起來并不分明,在網絡交際中口語和書面語的特點會雜糅出現,比如:神馬都是浮云、有木有、傷不起、我唱的不是歌是寂寞、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等等網絡流行詞語的使用,再加上各種可視的圖像符號綜合形成了不同于傳統語體的網絡語體風格。
(三)社會文化因素的推動作用
我們知道,影響一個時代語言時尚的根本動因在于從本質上說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滿足社會需要的產物。所以語言的發展變化是各種不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語言與文化發展因素的關系尤其密切。孫維張認為,“語言中的許多發展變化的現象是由社會教育、宗教、文化交流等因素造成的”。[6](P64)
通過考察“很X很XX”和“被XX”兩種網絡流行語模式快速傳播的原因也讓我們更深刻認識到這一現狀:不管我們是否出于自愿,社會科技的發展進步,已經使我們進入到電子交際的時代,多媒體的發展正在改變著我們過去單一傳播途徑——日常言語交際方式。“很X很XX”這一流行語模式就是先由現實交際然后進入到網絡交流中而成為流行語的;“被XX”模式是首先在網絡交際中出現隨后又進入到人們現實口語交際中而被廣泛傳播起來的,這說明網絡交流與日常言語交流這兩個傳播信息的途徑已經密切相關,互相影響。
當今我們所處的網絡語言交際環境已經使我們進入到電子交流社會,這一媒介下的言語交際特點也在深刻影響著我們進而形成新的交流習慣、交流方式和文化特征,這可以稱為一種新型的“網絡交際文化”,正是這一社會文化因素的強力推動作用使網絡流行語得以快速傳播,如上所述,它的特殊語體風格不同于我們傳統的主流文化,在網絡虛擬的世界里,更強調快捷、真實、新奇、娛樂與情感宣泄作為其文化的核心內涵,滿足上述目標的詞語可以更快速地憑借網絡這一交流平臺進行同時異地的傳播從而達到衍生繁殖的目的。
三、結語
電子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使用,也使當代漢語新詞語產生的途徑更為多樣化。 我們僅以“被+XX”和“很X很XX”這類網絡流行詞語構成模式為例,分析了網絡流行詞語衍生的主要制約因素:首先是交際者語言功能實現的需要,流行語模式打破了我們傳統的構詞習慣,這種不合常規的組合使其在完成表述功能的同時凸顯了獨特的表情功能和美學功能;其次是網絡語體的特殊性——自由、輕松和娛樂性;最后是社會文化因素的推動作用,網絡世界的虛擬性帶來了突出快捷、真實、新奇、娛樂與情感宣泄為目的網絡交際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為滿足上述文化內涵的流行語憑借網絡媒介達到同時異地的傳播衍生。
[1]〔丹麥〕奧托·葉斯柏森.葉斯柏森語言學選集[M].任紹曾,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2]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靳開宇.“很×很××”流行語模式的語言動因分析[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4).
[4]靳開宇.“被+XX”式詞語結構模式分析[J].長春大學學報,2010,(7).
[5]呂明臣,等.網絡語言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
[6]孫維張.漢語社會語言學[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靳開宇(1972-),女,文學碩士,綏化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語言理論和語言應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