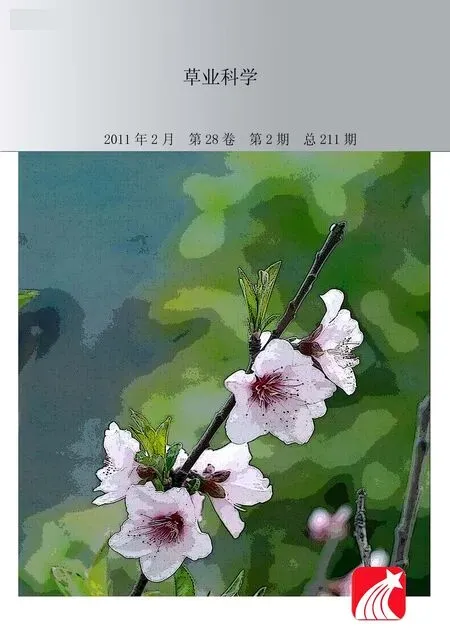草地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與生態(tài)閾值研究進展
劉 艷,張澤華,王廣軍
(1.沈陽農(nóng)業(yè)大學園藝學院,遼寧 沈陽 110866; 2.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北京 100081)
我國擁有近4億hm2草地,占國土面積的41.7%,是我國陸地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主體。近年來,由于全球氣候變化及超載過牧等原因造成了沙化、退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失去平衡,導致蝗蟲等生物災害的不斷發(fā)生。1999年以來我國北方草原連年發(fā)生大面積蝗災等生物災害,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步入草場退化-害蟲猖獗-草場進一步退化的惡性循環(huán)[1]。以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為例,1999-2006年,該區(qū)連續(xù)暴發(fā)蝗災,累積草原蝗蟲發(fā)生危害面積達0.622億hm2,蟲口密度均在50頭/m2以上,最高可達650頭/m2[2]。蝗災不但給畜牧業(yè)造成巨大的經(jīng)濟損失,而且嚴重威脅著我國北方草原生態(tài)安全。因此,開展草地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economic threshold)與生態(tài)閾值(ecological threshold)研究,對于有效指導蝗蟲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1 害蟲防治經(jīng)濟閾值的研究進展
害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問題是現(xiàn)代害蟲管理系統(tǒng)中進行優(yōu)化決策的基本依據(jù),也是使害蟲治理的經(jīng)濟效益和生態(tài)效益與生產(chǎn)措施相聯(lián)系的唯一紐帶。1959年Stern等[3]最早提出了經(jīng)濟閾值一詞,并將其定義為“害蟲的某一密度,在此密度時應采取控制措施,以防種群達到經(jīng)濟危害水平”。此后,經(jīng)濟閾值的概念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與深入探討。Edwards[4]將經(jīng)濟閾值定義為“可以引起與控制措施等價的損失的害蟲種群大小”。Headley[5]提出的定義是“使產(chǎn)品價值增量等于控制代價增量的種群密度”。Norgaard[6]提出損害閾值(damage threshold),定義為“引起經(jīng)濟損失的最低種群密度”。在我國,盛承發(fā)先生[7-8]曾在該領(lǐng)域進行過全面的綜述與討論,他給經(jīng)濟閾值的定義表達為“害蟲的某一密度,達此密度時應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否則,害蟲將引起等于這一措施期望代價的期望損失”。繆勇和許維謹[9]在對經(jīng)濟閾值定義的討論中,認為經(jīng)濟閾值應是“針對某一密度(含預測)的害蟲種群,邊際成本函數(shù)等于邊際產(chǎn)值函數(shù)時的種群密度。超過此密度時,應適時采取控制措施,將種群密度壓制至該密度水平,可以獲得最大凈收益”。實際上,經(jīng)濟閾值不同于產(chǎn)量損失閾值和經(jīng)濟損害水平,因為經(jīng)濟閾值作為害蟲防治的決策依據(jù),要綜合考慮到防治成本、產(chǎn)品價格、生態(tài)效益、環(huán)境保護等諸多問題,是一個經(jīng)濟生態(tài)學參數(shù),是進行防治決策的依據(jù),是生產(chǎn)者關(guān)注的焦點[10]。
國內(nèi)外在農(nóng)業(yè)害蟲防治經(jīng)濟閾值領(lǐng)域的研究較為廣泛。Naranjo等[11]對棉花上煙粉虱[Bemisiatabaci(Gennadius)]的防治經(jīng)濟閾值開展了研究;Szatmari[12]研究了鱗翅目昆蟲對樹莓(Rubusidaeus)損害的經(jīng)濟閾值;Singh[13]對印度西部一種有斑點的螟蛉(Eariasspp.)的經(jīng)濟閾值進行了研究;Diaz[14]研究了煙草(Nicotianatabacum)上蚜蟲(Myzuspersicae)的經(jīng)濟閾值;Bharpoda[15]在印度研究了棉鈴蟲(Helicoverpaarnigera)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Ukey等[16]對辣椒(Capsicumfrutescens)螨類的經(jīng)濟閾值進行了研究;Afzal等[17]對大米蛀蟲(Scirpophagaspp.)的經(jīng)濟閾值進行了研究。國內(nèi)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關(guān)于經(jīng)濟閾值研究的報道也較多。盛承發(fā)[18-19]、高宗仁等[20]對棉鈴蟲的經(jīng)濟閾值均進行了探討;曹瑩等[21]對危害水稻(Oryzasativa)的中華稻蝗(Oxyachinensis)、稻螟蛉(Narangaaenescens)和粘蟲(Mythimnaseparata)的經(jīng)濟閾值進行研究,并提出水稻孕穗期是進行化學防治的最佳時期;趙利敏和張海蓮[22]報道了灰翅麥莖蜂(Cephusfumipennis)的經(jīng)濟危害水平和經(jīng)濟閾值,為麥田生產(chǎn)提供了防治的參考依據(jù);此外,牟少敏等[23]對蘋果黃蚜(Aphiscitricala),蔣杰賢等[24]對菜青蟲(Pierisrapae),姜鼎煌等[25]對苦瓜(Momordicacharantia)地的瓜實蠅(Bactroceracucurbitae),盧巧英等[26]對韭菜遲眼蕈蚊(Bradysiaodoriphage)等害蟲的經(jīng)濟閾值進行了研究探討。這些研究基于挽回損失等于防治成本的原則,為害蟲適時防治提供了科學的參考指標,為農(nóng)業(yè)管理者進行害蟲有效控制提供了決策依據(jù)。
2 害蟲防治生態(tài)閾值的研究進展
相對于經(jīng)濟閾值,生態(tài)閾值的定義和研究是近些年才受到重視的。1977年May[27]最早提出了生態(tài)閾值的概念,指出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特性、功能等具有多個穩(wěn)定態(tài),穩(wěn)定態(tài)之間存在的閾值和斷點(thresholds and breakpoints)就是生態(tài)閾值。此后,生態(tài)閾值的概念受到生態(tài)學和經(jīng)濟學界的普遍關(guān)注,并展開了學術(shù)探討。Friedel[28]認為生態(tài)閾值是生態(tài)系統(tǒng)兩種不同的狀態(tài)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界限(boundaries);Muradian[29]定義生態(tài)閾值為獨立生態(tài)變量的關(guān)鍵值,在此關(guān)鍵值前后生態(tài)系統(tǒng)發(fā)生一種狀態(tài)向另一種狀態(tài)的轉(zhuǎn)變。Wiens等[30]認為生態(tài)閾值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轉(zhuǎn)變帶(region or zone),而非一系列的離散點。Bennett和Radford[31]等提出生態(tài)閾值是生態(tài)系統(tǒng)從一種狀態(tài)快速轉(zhuǎn)變?yōu)榱硪环N狀態(tài)的某個點或一段區(qū)間,推動這種轉(zhuǎn)變的動力來自某個或多個關(guān)鍵生態(tài)因子微弱的附加改變,如從破碎程度很高的景觀中消除一小塊殘留的原生植被,將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急劇下降。總的來說,相關(guān)研究普遍認為生態(tài)閾值有兩種類型,即生態(tài)閾值點(ecological threshold point)和生態(tài)閾值帶(ecological threshold zone),在生態(tài)閾值點前后,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特性、功能或過程發(fā)生迅速的改變,生態(tài)閾值帶暗含了生態(tài)系統(tǒng)從一種穩(wěn)定狀態(tài)到另一穩(wěn)定狀態(tài)逐漸轉(zhuǎn)換的過程,而不像生態(tài)閾值點那樣發(fā)生突然的轉(zhuǎn)變,生態(tài)閾值帶在自然界中可能更為普遍[32]。
目前,基于生態(tài)閾值理論的相關(guān)研究較少。Noy-Meir[33]研究指出,在放牧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家畜利用面積的5%是其供應牲畜取食的閾值,這為人類活動干預下草原退化與恢復演替的研究,特別為確定天然草原放牧強度的生態(tài)閾值提供了依據(jù)[34]。韓崇選等[35]以人工林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嚙齒動物群落和主要造林樹種為研究對象,提出了人工林群落生態(tài)閾值概念,并指出林區(qū)嚙齒動物管理中的群落生態(tài)閾值是單個林木過渡到森林群落的預測指標,考慮的是嚙齒動物群落與林木的相互影響,其目的是保證成林。駱有慶等[36]研究表明,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楊樹天牛(Anoplophoraglabripennis)的防治生態(tài)閾值為4.8個羽化孔,并指出對于以生態(tài)防護效益為主的防護林來說經(jīng)濟閾值具有局限性,而應以生態(tài)閾值作為害蟲防治的參考依據(jù)。可見,生態(tài)閾值在有害生物防治中不同于經(jīng)濟閾值,這一指標是以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和資源可持續(xù)利用為出發(fā)點,對于在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探討害蟲的防治閾值具有廣闊的研究與應用前景。
3 我國草地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與生態(tài)閾值研究動態(tài)
前已述及,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是畜牧業(yè)發(fā)展的基礎(chǔ),同時在我國也發(fā)揮著重要的生態(tài)作用。蝗蟲作為一種危害性較大的食草害蟲,自古至今對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的危害屢有記載。據(jù)統(tǒng)計從公元前707年至1907年間我國共發(fā)生蝗災739次,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地方志均有蝗災的詳細記載[37]。21世紀以來,我國西部主要草原區(qū)蝗災時有發(fā)生,2004年內(nèi)蒙古草原蝗蟲發(fā)生面積達529萬hm2,2006年新疆草原蝗蟲危害面積為203萬hm2,甘肅省草原蝗蟲高峰期危害面積達197萬hm2[38-40]。草地蝗蟲防治也因此成為草地植保領(lǐng)域的研究熱點問題之一。開展蝗蟲防治閾值(包括經(jīng)濟閾值和生態(tài)閾值)的研究與制定,對于控制蝗蟲暴發(fā),減少經(jīng)濟損失和維持生態(tài)平衡具有重要的意義。
3.1草地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nèi)少數(shù)學者開始從事草地蝗蟲防治經(jīng)濟閾值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結(jié)合某一草原類型區(qū)的優(yōu)勢蝗種開展區(qū)域性研究,為所研究地區(qū)的蝗蟲控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防治閾值。1998年,李新華等[41]選擇新疆天山北坡蒿子(Artemisiaspp.)+苔草(Carexliparocarpos)+羊茅(Festucavalesiaca)草地植被類型,探討了意大利蝗(Calliptamusitalicus)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得出采用馬拉硫磷和敵敵畏控制該區(qū)意大利蝗,3齡前的最低防治密度為69頭/m2。同樣是意大利蝗,張泉等[42]在新疆瑪納斯縣南山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區(qū)研究后,得到3齡前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為8頭/m2。同一蝗種在兩個不同試驗區(qū)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相差高達8.6倍,這主要是由于草地群落植被組成、初級生產(chǎn)力等具有較大的差異造成的。因此,不同地區(qū)蝗蟲種類和草地類型不同,需要根據(jù)不同地域的蝗蟲危害和防治措施,制定不同的防治經(jīng)濟閾值[43]。西伯利亞蝗(Gomphocerussibiricus)是新疆山地草原的主要危害種,喬璋等[44]采用田間罩籠試驗首先計算了蟲口密度與牧草損失量的關(guān)系式,然后通過測算確定3齡前化學防治西伯利亞蝗的經(jīng)濟閾值為26.8頭/m2。烏麻爾別克等[45]采用相同研究方法,對新疆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區(qū)主要危害種紅脛戟紋蝗(Dociostauruskraussi)的防治經(jīng)濟閾值進行了研究,提出化學防治的最低經(jīng)濟閾值為8頭/m2。邱星輝等[43]測定了內(nèi)蒙古典型草原5種優(yōu)勢蝗蟲的防治經(jīng)濟閾值,亞洲小車蝗(Oedaleusasiaticu)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最小,為16.9頭/m2,小蛛蝗(Aeropedellusvariegatesminut)最大,為37.4頭/m2,分析指出經(jīng)濟閾值與蝗蟲的個體大小呈負相關(guān),即個體大者因造成的牧草損失大,其經(jīng)濟閾值小。以上研究主要是結(jié)合特定區(qū)域的優(yōu)勢蝗種,對單一種群的防治閾值進行探討,但是草地蝗蟲的發(fā)生往往比較復雜,常常是多個種群的混合暴發(fā)。廉振民和蘇曉紅[46]對甘肅省祁連山東段草地蝗蟲復合防治指標(經(jīng)濟閾值)進行了研究,指出牧草的損失量取決于受損害量,而蝗蟲只是起執(zhí)行損害過程的作用,因此無論幾種蝗蟲為害,只在牧草的受損量達到28頭/m2時才進行防治,這是關(guān)于混合種群蝗蟲防治經(jīng)濟閾值的一個新觀點。總的來說,我國在草地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領(lǐng)域已經(jīng)開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但是與農(nóng)業(yè)害蟲的研究相比仍十分薄弱,且研究缺乏系統(tǒng)性和持續(xù)性,難以有效指導草地上復雜的蝗蟲災變形勢,因此蝗蟲經(jīng)濟閾值研究仍將是今后的重點研究課題。
3.2草地蝗蟲防治的生態(tài)閾值研究 目前,關(guān)于草地蝗蟲防治生態(tài)閾值方面的研究少見報道,本領(lǐng)域尚處于研究的起步階段。草地蝗蟲暴發(fā)的直接后果是造成草地初級生產(chǎn)力和次級生產(chǎn)力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從生態(tài)層面上引起的草地退化,在蝗蟲防治時單純考慮經(jīng)濟閾值,不制定以生態(tài)效益為主導的生態(tài)閾值顯然是不利于草地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周壽榮[47]結(jié)合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提出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在不斷降低和破壞其自動調(diào)節(jié)能力的前提下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的外界壓力(臨界值),稱為生態(tài)閾值。當蝗蟲的為害超過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耐受范圍時,就有可能引起草地退化的發(fā)生和加劇,因此,草地蝗蟲防治生態(tài)閾值的探討具有重要的生態(tài)意義。盧輝[48]根據(jù)經(jīng)濟閾值的基本概念,挽回損失=防治成本的原則,將補償作用和蓋度的指數(shù)引入模型,初步建立了亞洲小車蝗為害草地的生態(tài)閾值模型,這個模型把草地植被蓋度作為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變化的參數(shù),提出隨著蓋度增加,也是草地類型從荒漠草原-半荒漠草原-典型草原的過渡,亞洲小車蝗防治生態(tài)閾值也在增加,例如,蓋度值為0.2時,防治指標為3.4頭/m2; 0.4時,防治指標為6.0頭/m2;0.7時,防治指標為15.3頭/m2。 余鳴[49]在研究蝗蟲防治生態(tài)閾值時,將干旱因子引入了模型中,理論上提高了經(jīng)濟閾值的可用性,但是在他的閾值模型中對于蝗蟲與草地平衡之間的關(guān)系尚不明確,衡量指標模糊,需要進一步的田間試驗研究驗證。這兩篇關(guān)于草地蝗蟲防治生態(tài)閾值的學術(shù)論文,為本領(lǐng)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觀點與方向。筆者在文獻查閱時未找到更多關(guān)于蝗蟲防治生態(tài)閾值的資料,因此在草地植保領(lǐng)域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新課題。
3.3經(jīng)濟閾值與生態(tài)閾值在蝗蟲防治應用中的思考 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與生態(tài)閾值之間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二者作為蝗蟲防治決策的參考依據(jù)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在蝗蟲危害達到經(jīng)濟閾值指示的防治指標時,并未危及草地生態(tài)平衡,即生態(tài)系統(tǒng)尚有一定的耐受能力,這時經(jīng)濟閾值小于生態(tài)閾值,在防治時則應以最大限度的挽回經(jīng)濟損失為目的,以經(jīng)濟閾值作為防治指標;另外一種情況是,蝗蟲的種群暴發(fā)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尚在可承受范圍之內(nèi),但草地物種多樣性等生態(tài)指標遭到破壞,致使草地生態(tài)失衡,在這種情況下當以生態(tài)閾值作為防治的指標。
4 蝗蟲防治閾值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4.1存在的問題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草地蝗蟲發(fā)生數(shù)量急劇上升,蝗蟲災害頻繁暴發(fā),嚴重影響了天然草地植被的正常生長發(fā)育,削弱了草地生態(tài)功能作用的發(fā)揮,加劇了牧區(qū)人民經(jīng)濟負擔,威脅到草地畜牧業(yè)和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50]。但是,由于我國草原面積大,草地蝗蟲種類多,在蝗蟲防治閾值的研究方面存在較多問題:1)參考防治指標陳舊,存在“一刀切”的問題,難以適應當前日趨復雜化的草原保護形勢;2)不同草原區(qū)優(yōu)勢蝗種的生態(tài)學研究匱乏,限制了經(jīng)濟閾值與生態(tài)閾值的研究;3)偏重于經(jīng)濟損失方面的經(jīng)濟閾值研究,對反映生態(tài)平衡的生態(tài)閾值缺乏深入研究與探討;4)國家對草地蝗蟲防治及科研工作的重視程度與投入經(jīng)費不足,限制了本領(lǐng)域的發(fā)展。
4.2建議 當前,我國草原退化形勢仍十分嚴峻,造成了草原退化-蝗蟲發(fā)生-草原進一步退化的惡性循環(huán)。因此,開展蝗蟲防治閾值方面的研究顯得十分迫切與重要。今后,在本領(lǐng)域應組建包括昆蟲學、生態(tài)學、經(jīng)濟學等方面的跨學科團隊,對我國草地蝗蟲防治的經(jīng)濟閾值與生態(tài)閾值進行全面、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加大對草地蝗蟲生態(tài)閾值的研究,為實現(xiàn)經(jīng)濟效益與生態(tài)效益的雙贏提供有力指導。對不同草地類型區(qū)和各區(qū)優(yōu)勢蝗種開展有重點的研究與探討,為各區(qū)的蝗蟲防治提出科學的防治閾值。此外,應進一步爭取國家對蝗蟲防治研究的投入,以保障取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1] 潘建梅.內(nèi)蒙古草原蝗蟲發(fā)生原因及防治對策[J].中國草地,2002,24(6):66-69.
[2] 哈斯巴特爾,高娃,斯琴,等.內(nèi)蒙古草原蝗蟲成災原因與防治對策[J].內(nèi)蒙古草業(yè),2007,19(4):52-55.
[3] Stern V M,Smith R F,van den Bosch R.The integ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ontrol of the spotted alfalfa aphid[J].Hilgardia,1959,29(2):81-101.
[4] Edwards C A.The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entomology[M].London:Chapman and Hall,1964.
[5] Headley J C.Defining the Econontic the Threshold[A].In:Metcalf R.Pest Control Strategy for the Future[C].Washington D 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972:100-108.
[6] Norgaard R B.The economics of improving pesticide use[J].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1976,21:45-60.
[7] 盛承發(fā).經(jīng)濟閾值定義的商榷[J].生態(tài)學雜志,1984(3):52-54.
[8] 盛承發(fā).防治棉鈴蟲的新策略[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
[9] 繆勇,許維謹.經(jīng)濟閾值定義等的討論[J].安徽農(nóng)學院學報,1990(2):137-142.
[10] 郝樹廣,張孝羲.對害蟲經(jīng)濟閾值理論的再思考[J].生態(tài)學雜志,1998,17(2):71-77.
[11] Naranjo S E,Chu C C,Henneberry T J.Economic injury levels forBemisiatabaci(Homoptera:Aleyrodidae)in cotton impact of crop price,control costs,and efficacy of control[J].Crop Protection,1996,15(8):779-788.
[12] Szatmari S.Lepidoptera living on raspberry in North Hungary,Integrated plant protection in orchards,soft fruits[J].Bulletin OILB-SROP,1998,21(10):35-38.
[13] Singh J.Economic threshold for spotted bollworms,Eariasspp.in cotton,GossypiumarboreumL[J].Journal of Insect Science,1998,11(1):66-68.
[14] Diaz F P.Economic threshold of Heliothis virescens in three tobacco varieties from Cuba[J].Revista Colombiana de Entomologia,1999,25:1-2,33-36.
[15] Bharpoda T M.Evaluation of economic threshold levels forHelicoverpaarmigeraon ‘H 6’ cotton (Gossypiumhirsutum) in central Gujarat region[J].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69(4):304-305.
[16] Ukey S P,Naitam N,Patil M J.Determination of economic threshold level of mites on chilli crop[J].Journal of Soils and Crops,1999,9(2):268-270.
[17] Afzal M,Yasin M,Sherawat S M.Evalu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economic threshold level (ETL) for chemical control of rice stem borers,ScirpophagaincertulusWlk.andS.innotataWl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y,2002,4(3):323-325.
[18] 盛承發(fā).華北棉區(qū)第二代棉鈴蟲的經(jīng)濟閾值[J].昆蟲學報,1985,28(4):382-389.
[19] 盛承發(fā),楊輔安.棉鈴蟲經(jīng)濟閾值研究中的幾個問題[J].生態(tài)學報,1999,19(9):720-723.
[20] 高宗仁,趙洪義,秦田豐.河南棉鈴蟲再猖獗的生態(tài)學特點及經(jīng)濟閾值研究[J].棉花學報,1994,6(1):57-60.
[21] 曹瑩,曹志強,肖紅.3種水稻食葉性害蟲對遼粳454為害經(jīng)濟閾值研究[J].沈陽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2002,33(1):35-39.
[22] 趙利敏,張海蓮.灰翅麥莖蜂(Cephusfumipennis)的經(jīng)濟危害水平和經(jīng)濟閾值(膜翅目:莖蜂科)[J].西北農(nóng)業(yè)學報,2008,17(1):65-69.
[23] 牟少敏,劉忠德,孔繁華,等.蘋果黃蚜危害蘋果經(jīng)濟損失和經(jīng)濟閾值的研究[J].山東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2002,33(1):87-88.
[24] 蔣杰賢,王奎武,陳永年.菜青蟲為害春甘藍不同生育期對產(chǎn)量的影響及經(jīng)濟閾值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2,20(4):312-316.
[25] 姜鼎煌,艾洪木,趙士熙,等.瓜實蠅經(jīng)濟閾值的研究[J].福建農(nóng)業(yè)學報,2006,21(3):207-210.
[26] 盧巧英,張文學,郭威龍,等.韭菜遲眼蕈蚊防治閾值研究[J].西北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2008,17(2):279-284.
[27] May R M.Thresholds and breakpoints in ecosystems with a multiplicity of stable states[J].Nature,1977,269:471-477.
[28] Friedel M H.Range condition assessment and the concept of thresholds a view point[J].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1991,44:422-426.
[29] Muradian R.Ecological thresholds a survey[J].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8:7-24.
[30] Wiens J A,VanHorne B,Noon B R.Integrating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scale in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A].In: Liu J,Taylor W W.Integrating Landscape Ecology in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3-67.
[31] Bennett A F,Radford J Q.Know your ecological thresholds[J].Thinking Bush,2003(2):1-3.
[32] 趙慧霞,吳紹洪,姜魯光.生態(tài)閾值研究進展[J].生態(tài)學報,2007,27(1):338-345.
[33] Noy-Meir I.Stability of grazing systems:an application of predator-prey graphs[J].Journal of Ecology,1975,63(2):459-481.
[34] Lv D R,Chen Z Z.Climate-ecology interaction in Inner Mongolia semi-arid grassland[J].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02,9(2):307-320.
[35] 韓崇選,楊學軍,王明春.林區(qū)嚙齒動物群落管理中的生態(tài)閾值研究[J].西北林學院學報,2005,20(1):156-161.
[36] 駱有慶,宋廣巍,劉榮光.楊樹天牛生態(tài)閾值的初步研究[J].北京林業(yè)大學學報,1999,21(6):45-51.
[37] 游修齡.中國蝗災歷史和治蝗觀[J].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2):94-100.
[38] 陳素華,烏蘭巴特爾,曹艷芳.氣候變化對內(nèi)蒙古草原蝗蟲消長的影響[J].草業(yè)科學,2006,23(8):78-82.
[39] 傅瑋東,姚艷麗,李新建,等.新疆草原蝗蟲發(fā)生面積與大氣環(huán)流特征量指數(shù)模型的研究[J].草業(yè)科學,2009,26(12):124-130.
[40] 方毅才.甘肅草原蝗蟲現(xiàn)狀與防治對策[J].草業(yè)科學,2009,26(11):157-160.
[41] 李新華,趙智剛,牛永綺.草場蝗蟲的種群密度與受害程度及經(jīng)濟閾值的探討[J].干旱環(huán)境監(jiān)測,1998,12(3):158-160.
[42] 張泉,烏麻爾別克,喬璋,等.意大利蝗造成牧草損失研究及防治指標的評定[J].新疆農(nóng)業(yè)科學,2001,38(6):328-331.
[43] 邱星輝,康樂,李鴻昌.內(nèi)蒙古草原主要蝗蟲的防治經(jīng)濟閾值[J].昆蟲學報,2004,47(5):595-598.
[44] 喬璋,烏麻爾別克,熊玲,等.西伯利亞蝗對草原的危害及其防治指標的研究[J].草地學報,1996,4(1):39-48.
[45] 烏麻爾別克,張泉,喬璋,等.紅脛戟紋蝗損害牧草及其防治指標的評定[J].草地學報,2000,2(8):120-125.
[46] 廉振民,蘇曉紅.牧場蝗蟲復合防治指標的研究[J].植物保護學報,1995,22(2):171-175.
[47] 周壽榮.草地生態(tài)學[M].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96:39-40,187-188.
[48] 盧輝.內(nèi)蒙古典型草原亞洲小車蝗防治經(jīng)濟閾值和生態(tài)閾值研究[D].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2005.
[49] 余鳴.蝗蟲生態(tài)閾值研究[D].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2006:328-331.
[50] 孫濤,趙景學.草地蝗蟲發(fā)生原因及可持續(xù)管理對策[J].草業(yè)學報,2010,3(19):2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