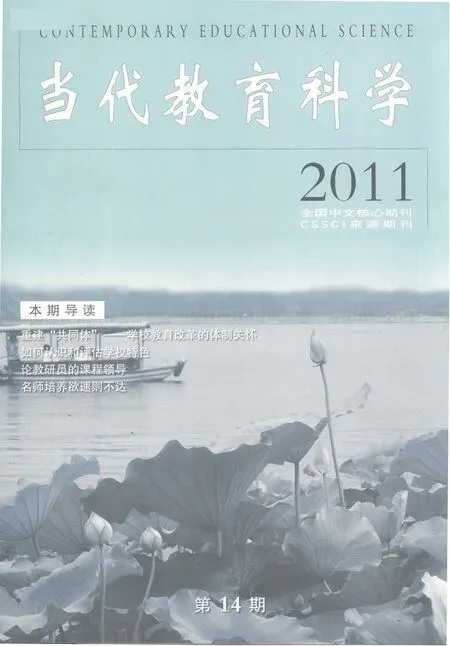校園安全事故問責制的思考
● 馬寧奇
校園安全事故問責制的思考
● 馬寧奇
校園安全工作成為學校管理的首要任務,國家也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規范校園安全管理,但是在校園安全事故責任承擔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問題,特別是事故處理中的責任追究制度還不完善。雖然《義務教育法》對教育問責制度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實施中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一、校園安全責任承擔上存在的問題
(一)校園安全責任承擔主體不明確
沒有明確法律責任主體的法律是一部可操作性不強的法律。在《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中,對校園安全責任承擔主體還不夠明晰。其中,第八章專門規定了獎勵與責任的制度,第61條規定:“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設、交通、文化、衛生、工商、質檢、新聞出版等部門,不依法履行學校安全監督與管理職責的,由上級部門給予批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上級部門和所在單位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者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規定學校不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職責,對重大安全隱患未及時采取措施的,有關部門應當責令其限期改正等等。《辦法》中囊括了所有校園安全的責任承擔主體,但是沒能根據校園安全的類別對責任主體具體化、明確化,這容易導致校園安全事故發生后各部門相互推卸責任的現象,在安全事故中找不出真正的責任人,無法問責。
(二)校園安全事故的歸責原則不明晰
歸責原則的不明晰直接導致責任主體不明確。依據我國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學校在學生傷害事故中應當承擔過錯責任,即有過錯擔責任,無過錯無責任;同時也有過錯推定責任原則,法律法規之間不統一。在 《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采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對于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在學校受到傷害的采用的是過錯推定責任原則,這就造成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如果依據的法律不同審理結果就不同,責任的承擔也不同。
(三)校園安全事故的責任追究不徹底
按照我國有關法律的規定,對學生傷害事故負有責任的當事人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但是,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往往只追究直接當事人的責任,而忽略了與直接當事人相關的責任人的追究。責任追究往往不徹底,在校園安全事故的許多案例中,如教師體罰了學生就把該教師免職,學校倒塌事故就把校長撤職了等等,而沒有追究校舍是誰建造的、是誰提供的、學校是誰舉辦的這些真正的原因,只是在表面上做到了對事故責任人的追究,不能真正追究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及其造成傷害的真正責任人。
二、校園安全事故處理中實行問責制的必要性
問責制通常是指政府及其公務員應承擔他們行為的法律義務的機制。問責性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及其官員因為違法或失職而受到懲罰,承擔民事或刑事法律義務。二是政府及其官員要就其工作的績效與結果承擔責任。我國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提出了問責制,第9條第2款是關于引咎辭職制度的規定:引咎辭職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這次法律修訂,是我國立法中第一次將“引咎辭職”寫入法律規定,體現了國家保障和推進義務教育的態度和決心。本款規定的引咎辭職主體為“負有領導責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之所以規定為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主要是因為實施義務教育是政府的職責,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教育行政部門具體負責義務教育實施工作。[1]這是整個教育立法中最大的亮點。
(一)只有確立了校園安全事故的問責制才能真正落實校園安全責任的主體
責任的追究其實質就是追究事故責任主體的責任。在國外對校園安全的問責方面,普遍重視學校的舉辦者、管理者、教師和其他職員,對于學校的安全和學生權利的保障,負有重要的責任。如英國在對付肇事者方面特別強調學校與警察的合作,但是作為一個原則,其主要的責任還是在于學校而不是警察。因此,只有明確校園安全事故的問責的制度、歸責的原則,才能準確的定位責任主體。也只有落實責任主體,才能把校園安全工作落到實處。
(二)校園安全事故問責制是歸責原則得以正確執行的保障
問責制的核心就是責任主體在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違法行使職權時,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責任,管理范圍內誰負責,誰的責任追究誰。特別是在學校安全管理中,《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規定:“學校負有對學生進行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職責,這涉及到學校對學生是否有監護責任上存在疑問,所以在校園安全事故的處理中更難以進行明確的歸責。如果能夠把責任清晰化,并明確規定各主體的權利、義務、違反義務應承擔什么后果等等,并事先建立切實可行的預案機制,就能保障歸責原則的執行了。
(三)校園安全事故問責制是校園安全應急預案執行的保障基礎
隨著國內校園安全事故的頻頻發生,教育行政部門、學校都加大了校園安全預案工作的執行力度,建立了校園安全應急預警機制,設置了應急預案工作小組及其負責人,但是對未履行義務的主體應承擔的責任、怎樣追究責任很少規定,這就導致校園安全應急預案機制形同虛設,在真正發生校園安全事故時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要使校園安全應急預案機制增加其執行力度,就要切實制定好校園安全事故問責機制。
三、完善校園安全事故問責制的對策
(一)厘清校園安全事故問責的主體
校園安全是指在學校職責范圍內,不發生學生和教職工傷害和財產損失的事故。校園是一個濃縮的小社會,校園安全也不僅包括校內也包括校外,校園安全的責任不僅僅限于學校、教師和學生,教育行政部門以及其他職能部門、社會各團體等也擔負著責任,凡屬于與學校產生法律關系的單位和個人都可能是責任主體。所以,在制定問責制時,不能只考慮追究學校和教師的責任,要根據不同的校園安全事故類型,明確地規定可能涉及到的不同責任主體的責任,一旦發生安全事故,才能有的放矢,準確迅速地根據其責任的大小追究其相應的責任,保護師生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二)明確校園安全問責的范圍
只有明確問責的范圍才能落實責任主體的責任進而維護責任主體的權利,不然就會導致“談問責色變”,不利于保護校園的安全。校園安全包括學校飲食衛生安全、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活動安全、消防安全、教學設施設備安全、網絡安全、自然災害、校園暴力與校園周邊安全等等。這些安全事故涉及到學校的舉辦者、管理者、相關職能部門,只有明確問責的范圍才能真正保護學生的利益不受損害,在眾多的安全管理工作中難免存在一些安全隱患和突發的安全事故,所以必須采取過錯責任原則,而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以及過錯推定責任原則僅在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才適用于學生傷害事故。學校如果存在過錯,在校園傷害事故發生后,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的精細劃分就可以使被問責者得以有的放矢地履行他的份內責任。
(三)校園安全事故問責的實施方式多元化
在校園安全應急預案中體現問責制。問責制其實不在于追究責任,而是要警示責任主體如有過失是會受懲戒的,是要求他們在平時認真而充分地履行職責。沒有懲戒的問責制是難以執行的,無論是引咎辭職還是責令辭職,無論是賠償損失還是降職降薪,只有問責的方式合適,才能達到懲戒的目的,才能促使責任者認真地履行其職責。
校園安全事故問責的主體不僅包括直接責任人,還應追究與校園安全事故有關的主體的責任。眾多案件判決表明,大多數都是對學校的直接負責人員進行了行政處分,并給予一定的經濟賠償,并沒有根據事故的實際情況,追究其背后的真正責任者。如某小學廁所倒塌砸傷學生案。根據《學校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學校應當依法承擔責任,但這是一個籠統的責任主體,必須要將其細化,落實到每個個體的責任人,即負責學校安全工作的教師或工作人員為第一責任人,其領導部門——該校的校長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學校的上級主管部門——當地的教育行政部門也有連帶的責任,而最大的責任者是學校的舉辦者。
第三,校園安全的問責并不應僅僅是至上而下的責任追究,還應包括至下而上的問責,以及監督和反饋責任的承擔情況。問責蘊涵著責任理念,實施問責制,必然要求政府樹立向公眾負責的行政理念。[2]在校園安全事故發生時,應該結合學校的主體,如學生、教師、學校工作人員等其他非當事人,接受他們的問責,接受他們對責任承擔情況的監督與反饋,這樣會對事故的處理更明晰,更有利于提高問責的效率和準確率。
[1]石連海.中小學校安全管理模式及其啟示——以贛州市學校安全臺帳管理為例[J].當代教育科學,2009,(24):50-52.
[2]李樹峰,校長問責制的定義探析[J].教育科學,2006,(06):50-54.
馬寧奇/河南省城建學院
(責任編輯:陳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