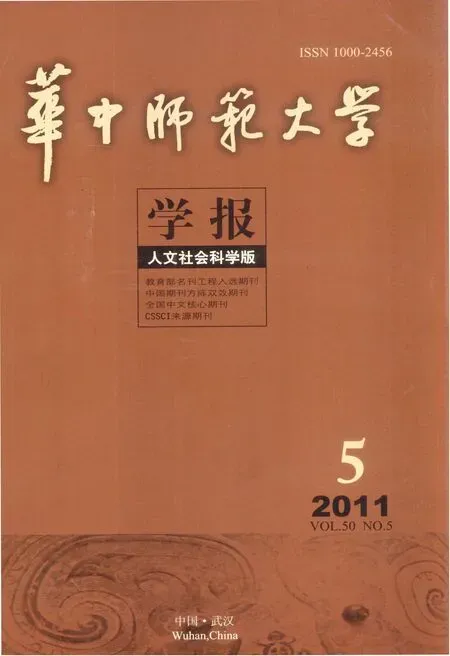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本體觀念的確立
胡星亮
(南京大學(xué)中國新文學(xué)研究中心,江蘇南京210093)
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本體觀念的確立
胡星亮
(南京大學(xué)中國新文學(xué)研究中心,江蘇南京210093)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電影的成熟期。中國電影家對于電影本體的認識此時也走向深化。其突出標志是電影界普遍的“電影意識”的確立,“以電影的表現(xiàn)方法來發(fā)揮電影藝術(shù)的特性”。它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追求鏡頭、畫面的視覺化創(chuàng)造,注重蒙太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功能,強調(diào)導(dǎo)演是電影創(chuàng)造的中心。中國電影家對于電影藝術(shù)特性的把握在漸趨深入。
電影意識;視覺化;蒙太奇;導(dǎo)演中心
中國電影發(fā)展到1930年代,首先在題材和主題方面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電影家將攝影機對準社會人生,其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強烈的時代感和現(xiàn)實感。然而,如同歷史上新興階級文學(xué)藝術(shù)崛起時其思想內(nèi)涵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往往難以平衡,1930年代初的中國左翼電影也存在類似情形,“在技巧上,在描寫上,的確還沒有得著優(yōu)良的運用。這是說把握了主題,還沒有很技術(shù)的處理題材”①。這里所謂“還沒有很技術(shù)的處理題材”有兩層意思:一是作為一般文藝創(chuàng)作而論,其思想內(nèi)涵的藝術(shù)表達還不夠深入;二是從電影作為獨立的藝術(shù)來說,其審美表現(xiàn)的“電影性”還不夠充分。電影界對此進行了認真檢討。尤其是后者,直接關(guān)涉到中國電影藝術(shù)的發(fā)展和成熟,更是引起電影家的思考和探索。它促使中國電影人對于電影藝術(shù)和電影本體有了新的認識,并由此帶來普遍的“電影意識”的覺醒。
關(guān)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家對于電影本體的認識,長期以來,學(xué)術(shù)界覺得它較之早期“影戲是由扮演的戲劇而攝成的影片”的看法有進步,但強調(diào)其“影戲”傳統(tǒng)還是根深蒂固。認為它“對電影根本性質(zhì)的看法,仍然是從戲劇、文學(xué)這樣一種直觀整體的角度去把握”,認為它是“以對敘事內(nèi)容的戲劇性要求為核心,以敘事蒙太奇為主要特征的理論體系”②。而實際上,這一時期中國電影本體觀念的發(fā)展要深刻、豐富得多。
一
對于中國電影來說,“很技術(shù)的處理題材”的關(guān)鍵,就是如何處理“影戲”傳統(tǒng)的電影與戲劇的關(guān)系問題。總體而言,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家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除鄭正秋等少數(shù)老電影家外,早期占據(jù)主流的“影戲是由扮演的戲劇而攝成的影片”的觀念,已被逐漸揚棄。1920年代后期出現(xiàn)兩種見解:一是認為“電影劇是電影術(shù)與戲劇的結(jié)合”,注重劇情編撰、演員演戲、也注重繪畫、攝影、光影等藝術(shù)表現(xiàn);二是認為“影劇是一種獨立的藝術(shù)”,把視覺影像和光影結(jié)合的創(chuàng)造力看作是電影審美特性。這兩種認識成為此期主導(dǎo)性的電影觀念并有新的探索和發(fā)展。
認為“電影劇是電影術(shù)與戲劇的結(jié)合”的觀念,在這一時期可以蔡楚生為代表。蔡楚生受到鄭正秋的影響頗深,他非常注意中國觀眾“對于欣賞戲劇的能耐性——或是貪性”,因而強調(diào)電影創(chuàng)作“勢必先投其所好地將每一個制作的材料,盡可能地增加得豐富些”,并且“必須在描寫手法上加強每一件事態(tài)的刺激成分”③。其影片成功當然有畫面構(gòu)圖優(yōu)美、鏡頭轉(zhuǎn)換自如等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他是憑借戲劇的經(jīng)驗和藝術(shù),以家庭倫理、悲歡離合、善惡因果、豐富曲折,有頭有尾、平鋪直敘,曉暢明快、通俗易懂等,而贏得普通觀眾的廣泛贊譽。桑弧、黃佐臨、金山等電影家在這方面也有相似的審美傾向。
然而更多的電影家看到電影與戲劇的不同,并努力探求屬于電影自身的藝術(shù)特性。比較早地在實踐和理論中體現(xiàn)出如此探索的是費穆。費穆1933年攝制的處女作《城市之夜》,就以嶄新的電影意識引起影壇的關(guān)注和討論。夏衍、鄭伯奇、柯靈等敏銳地發(fā)現(xiàn),盡管該片在思想內(nèi)涵上還不十分健全,但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方面,它突破當時“許多電影藝術(shù)家還過分重視甚至迷信戲劇”的傳統(tǒng)觀念,“全部電影中,沒有波瀾重疊的曲折,沒有拍案驚奇的布局;在銀幕上,我們只看見一些人生的片斷用對比的方法很有力地表現(xiàn)出來。其中,人和人的糾葛也沒有戲劇式的夸張。”他們由此對電影與戲劇的關(guān)系進行了深入探討:
電影雖然和戲劇是最接近的親屬,但是,電影有它的藝術(shù)上的特質(zhì),決不是戲劇的改裝,也不是戲劇的延長……誠然,在電影的遺產(chǎn)中,戲劇的成分曾占過重要的地位,可是,現(xiàn)在電影已經(jīng)達到獨立成年的時期,它應(yīng)該盡力發(fā)展自己的特長,不必再為戲劇的隸屬。同時電影藝術(shù)家也應(yīng)該抓住電影藝術(shù)的特質(zhì),使它盡量作正當?shù)陌l(fā)展。④
費穆也認為:“戲劇既可從文學(xué)部門中分化出來,由附庸而蔚為大國;那么電影藝術(shù)也應(yīng)該早些離開戲劇的形式,而自成一家數(shù)。”并且明確提出他是在探索一種“新的電影的觀念”⑤。
“電影化”問題因而受到中國電影界的普遍重視。顯而易見,從中國電影轉(zhuǎn)型期對于思想意識的充分強調(diào),到此時同時強調(diào)“電影藝術(shù)的特質(zhì)”,乃至強調(diào)“電影(就)是電影”,認為“一個電影片即使有了非常豐富非常尖銳的內(nèi)容,而如果不能以電影的表現(xiàn)方法來發(fā)揮電影藝術(shù)的特性,那么無論如何,這總是一種根本的失敗”⑥,中國電影家對于電影的認識漸趨完整、深刻。
那么“電影藝術(shù)的特質(zhì)”主要是什么呢?人們閱讀文學(xué)作品可以自由想象、自造幻境,而觀看電影,卻是要取決于、受限于影片所給定的視覺形象。故從電影攝制必須通過攝影機去觀察和攝取的獨特性出發(fā),電影家認為“電影藝術(shù)的特質(zhì)”首先是要注重現(xiàn)實描寫的鏡頭、畫面的視覺化創(chuàng)造。它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用洪深的話來說,一是“事實是否視覺化”,二是“鏡頭運用是否恰到好處”。前者如洪深所說:“電影本是給人看的,故事的敘述,應(yīng)當就是許多幅連綴著的好看的圖畫。一個事情的意義,一個人的心事情緒,都得用那醒目有趣的行動,很明顯地表達出來,無須乎再有言語的解釋”,所以電影“敘述事實,應(yīng)當從畫面和動作上著想!”后者,著重是指電影敘述事實的畫面和動作,其“‘鏡頭’是否柔和美麗,‘角度’是否新奇不俗”,以及由于攝影機位置的變換而產(chǎn)生的遠景鏡頭、中景鏡頭、近景鏡頭、特寫鏡頭、移鏡頭、跟鏡頭、推拉鏡頭等的運用是否巧妙別致⑦。
不同于早期中國電影著重靠劇情的波瀾跌宕、悲歡離合去感染觀眾,電影家經(jīng)過實踐探索,終于感悟到電影藝術(shù)的特質(zhì)主要不是“戲”(劇情),而在于其鏡頭、畫面的視覺形象性。明白這一點,人們對電影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就有了新的認識。夏衍說:
電影藝術(shù)的基礎(chǔ)既然是視覺的形象的言語,那么電影藝術(shù)家當然的該用繪畫的表象的方法,來表現(xiàn)和傳達一切的感情和思想。⑧
夏衍在這里抓住“視覺的形象的言語”和“繪畫的表象的方法”,確實是敏銳而深刻的。這種觀念在相當程度上將中國電影從戲劇的包圍中解放出來,改變以前攝影機按照劇情發(fā)展順序去講述故事的觀念,而強調(diào)電影是通過眼睛來觸動感情的畫面的藝術(shù),強調(diào)電影必須以形象直接訴諸于觀眾的視覺,注重運用鏡頭、畫面去敘述情節(jié)和刻畫形象,注重鏡頭、畫面的敘事性和表現(xiàn)力。進一步,洪深還提出電影編劇其“材料是否適合于電影化的問題”⑨,要求電影編劇必須懂得電影的特性,努力找尋和運用鮮明生動的視覺形象來表現(xiàn)影片內(nèi)涵。
中國電影家已經(jīng)認識到,讓鏡頭和畫面說話,將豐富的思想蘊涵于視覺形象之中,以繪畫的表象的方法去表情達意,是電影藝術(shù)區(qū)別于戲劇和其他文學(xué)藝術(shù)的最基本的特征。這種觀念的進步,對中國電影藝術(shù)的發(fā)展影響深刻。
二
比之早期主要從戲劇角度去理解電影,認為“影戲是由扮演的戲劇而攝成的影片”,這一時期中國電影家注重鏡頭、畫面的視覺化創(chuàng)造,則是從機械性、攝影性去理解電影的。此即孫瑜所言:“電影的藝術(shù)是以攝影的技巧為出發(fā)點的。電影藝術(shù)獨特的表現(xiàn)方法,也必須經(jīng)過了攝影機然后才能夠成立。換一句話說,電影雖然綜合了已經(jīng)成立的文學(xué)、戲劇、詩歌、音樂、舞蹈、繪畫、建筑等藝術(shù)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軀殼,但是它的生命的基礎(chǔ)是建筑在攝影的技巧上的。運用攝影機來表現(xiàn)這一種新的藝術(shù),才能夠誕生電影獨特的軀骨和生命。”⑩從電影與戲劇兩種相似藝術(shù)形式的類比,進而努力探尋電影描寫現(xiàn)實的獨特語匯和手段,這是中國電影家經(jīng)過長期實踐而對電影審美特性的新認識。
當然,創(chuàng)作實踐要比理論探索復(fù)雜得多。多用鏡頭、畫面素樸地紀錄現(xiàn)實的《春蠶》等作品不甚賣座,和注重劇情感染的《姊妹花》、《一江春水向東流》廣受歡迎,又提醒人們電影創(chuàng)造既要注重“攝影的技巧”,又要注重“影片本身的劇力”?,尤其是面對“太習(xí)慣于傳奇”?的中國觀眾。所以中國沒有出現(xiàn)過歐洲“純粹電影”、“絕對電影”之類的觀念和創(chuàng)作?。既注重“攝影的技巧”,又注重“影片本身的劇力”,上述此期兩種主導(dǎo)性電影觀念——一種認為“電影劇是電影術(shù)與戲劇的結(jié)合”,一種認為“影劇是一種獨立的藝術(shù)”——也正是在這里部分重合。嚴格地說,它們更多是或注重視覺形象性或注重劇情感染力,各有偏重。
這就是說,無論是偏重“攝影的技巧”,還是偏重“影片本身的劇力”,此期電影家都強調(diào)劇情內(nèi)容必須通過鏡頭和畫面表現(xiàn)出來。不同于早期“影戲是由扮演的戲劇而攝成的影片”,其劇情敘事更多是戲劇式場面的連接;此期電影注重鏡頭、畫面的視覺形象性創(chuàng)造。但它又如何敘事而能使眾多鏡頭、畫面成為一部完整的藝術(shù)作品呢?是蘇聯(lián)蒙太奇理論的譯介使中國電影家知曉了其中的奧秘。劉吶鷗在這方面的論述具有代表性。他認為攝影機所拍攝的鏡頭、畫面,“能夠把普通我們的視覺所覺察不到的狀態(tài)和過程表示出來”,因此它不但能解說腳本,而且能創(chuàng)造它“自己的形式”;然而,“這開麥拉的特質(zhì)如果不與奇跡的‘織接’(Montage)合作,是不會有它的創(chuàng)造的生命的。”正是Montage把攝影機所拍攝的眾多鏡頭、畫面,組織成為“那銀幕上的動作底連續(xù)的映像”,所以劉吶鷗說,“影戲?qū)嶋H上是用Montage構(gòu)圖而組成的”。?
中國電影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主要是從敘事蒙太奇和表現(xiàn)蒙太奇兩個方面去理解蒙太奇的。關(guān)于前者,就像洪深所闡述的:
事實既然視覺化了;每個鏡頭,本身也是恰當而美麗了;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怎樣能將畫面連綴起來,使得觀眾覺到整部影片是流利的悅目的,有抑揚頓挫有旋律有焦點是引人入勝的,是雄辯的有力的,是可以逼得觀眾不能不同情于劇旨的。?
這種將不同鏡頭、畫面連接起來去講述一個連續(xù)的、完整的故事,便是美國電影家格里菲斯開創(chuàng)的敘事蒙太奇?zhèn)鹘y(tǒng)。洪深在這篇文章中還談到,這種蒙太奇的剪接要善于變化、調(diào)和、相襯,以增加影片敘事的藝術(shù)感染力。這其中盡管也涉及到一些鏡頭、畫面連接的意義生成等蒙太奇思維和創(chuàng)造問題,可是更多的,它所處理的是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上相連貫的事件,影像剪接注重流利悅目、抑揚頓挫、引人入勝等鏡頭畫面連續(xù)完整地講述故事的功能。
表現(xiàn)蒙太奇更多注重意義內(nèi)涵在“影片生成上”的功能。劉吶鷗曾以詩人的詩語、文章的文體作類比,稱之為“導(dǎo)演者‘畫面的’的言語”:
詩人在做詩的時候不是躊躇地思想著挑選著用字,經(jīng)過幾番雕琢之后才決定他所欲用的詩語嗎?導(dǎo)演者亦須用同樣的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在開始開麥拉之前幾番思維,選擇他所欲用的畫面。這“畫面的”工作才是實在的Montage,所以Montage可以說是作品上的現(xiàn)實的創(chuàng)造主,導(dǎo)演得用Montage由在不同的瞬間里,在種種的地方攝來的景況而構(gòu)成并“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與現(xiàn)實的時間和空間毫沒關(guān)系的影戲時間和空間,即“被攝了的現(xiàn)實”……?
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電影攝制要注重蒙太奇思維。特別是導(dǎo)演,在影片攝制之前和攝制過程中,要像詩人寫詩推敲詩語一樣,去思考和選擇他用以表現(xiàn)影片現(xiàn)實內(nèi)涵的鏡頭和畫面。二是電影審美要注重蒙太奇創(chuàng)造。單個的鏡頭畫面和多個畫面組成的鏡頭段落就像是字和句,其本身再美都不能稱為真正的藝術(shù)。只有當它們與蒙太奇結(jié)合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電影時間和空間,這些本來互不關(guān)聯(lián)的若干現(xiàn)實片斷,才呈現(xiàn)出一種構(gòu)成新的意義且富有表現(xiàn)力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所以劉吶鷗接著上述引文說,蒙太奇“能夠使物變換其本質(zhì)的內(nèi)容,確保其新的價值,給影片以從前所沒有的意義。”就像作家運用文法組合字句而完成一部獨特的創(chuàng)作。
大體而言,上述敘事蒙太奇更多接近美國電影家所稱分鏡頭構(gòu)成本的康替尼迭(Continuity意為“連續(xù)”),表現(xiàn)蒙太奇更多接近蘇聯(lián)電影家所稱分鏡頭構(gòu)成本的蒙太奇(Montage意為“構(gòu)成”)。二者都有鏡頭、畫面的剪接功能,其不同是:“Montage是從畫面間的編接著手,組織一部電影全部的構(gòu)成;而Continuity是從全部的構(gòu)成的概念著眼,去整理、安插各個畫面。前者是運用編接去創(chuàng)造影像(Visual image),后者是通過影像去構(gòu)成編接。前者用畫面間的對位法的(跳躍的)運動把個別的影像統(tǒng)一起來,后者根據(jù)影像的連貫性的運動把畫面的斷片組織起來。換言之,前者是畫面間的編接支配畫面內(nèi)的構(gòu)成,后者是畫面內(nèi)的構(gòu)成支配畫面間的組織。”?雖然在中國它們都稱為蒙太奇,但電影家對其不同的藝術(shù)功能和審美特性有比較準確的把握。陳鯉庭1941年出版專著《電影軌范》,對蒙太奇和康替尼迭有更為深入細致的闡述。
盡管因為中國觀眾“太習(xí)慣于傳奇”,也因為當時中國電影家大都是戲劇出身,故中國電影較多注重敘事蒙太奇而較少探索表現(xiàn)蒙太奇,但無論如何,中國電影人對于電影的認識在深入,蒙太奇已經(jīng)成為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理論和批評的重要內(nèi)容?。它使中國電影家認識到,電影敘事與其說接近戲劇,倒不如說它與小說有更多相似。比如二者在時間上的高度自由性和空間上的高度靈活性。時間在小說中是極其自由的。而以蒙太奇手法組接鏡頭、轉(zhuǎn)換場景,電影也就能突破早期“影戲”以場面為單位組接劇情的局限,能“像小說一樣的驅(qū)使那回想的方法來進行時間的轉(zhuǎn)換”。尤其是當時類似“意識流”的電影“新敘述法”介紹進來,“亙古以來被認為無可更改的那種以時間為函數(shù)而發(fā)展故事的敘述法”被突破,鏡頭畫面“可以依著觀眾理解和情緒的起伏”來展開情節(jié),就使電影獲得更大的表現(xiàn)自由。同樣地,電影在空間表現(xiàn)上的高度靈活性,也使電影家認識到它不像戲劇受制于舞臺空間,“它的那種可驚的速度,可以在幾秒鐘里面,表示出在無數(shù)不同的場面之發(fā)生乃至進展的不同的事件”,其“連續(xù)的空間”的使用,表明“電影藝術(shù)在本質(zhì)上已經(jīng)克服了空間的限制”?。1940年代后期,法國電影家巴贊在總結(jié)歐洲電影實踐的基礎(chǔ)上指出:“電影在美學(xué)上是與小說相近的”,“電影的發(fā)展途徑在于不斷開掘它的小說潛在性”?,也是看到電影如同小說打破敘事的時空順序,能豐富人物性格塑造和心理刻畫,增強電影反映生活的內(nèi)涵量和表現(xiàn)力。
總之,結(jié)合創(chuàng)作實踐的理論探討使中國電影家認識到,電影是敘事藝術(shù),是以蒙太奇手法建構(gòu)新的電影時間和空間的獨特的敘事藝術(shù)。這種觀念的建立,極大地改變了早期中國電影或是平鋪直敘地圖解文學(xué)作品,或是戲劇式地在銀幕上搬演故事的幼稚情形,促進中國電影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迅速走向成熟。
三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家“電影意識”的覺醒,還體現(xiàn)在對于“導(dǎo)演是電影創(chuàng)造中心”觀念的強調(diào)。中國電影在1930年代初“仍是以明星為中心,幾乎是非明星不足以號召”,電影家指出,“若想有好的影片在中國出現(xiàn),必定要等著導(dǎo)演為中心的時候。”?
對于“導(dǎo)演中心”的強調(diào)主要是出于兩方面緣由:一是電影作為綜合藝術(shù),導(dǎo)演的工作性質(zhì)決定了他必然處在編劇、演員、攝影、裝置、化妝、燈光、洗印、剪接等影片攝制的中心位置。此即費穆所言:“導(dǎo)演應(yīng)該擔(dān)負整部影片的一切責(zé)任,因為演員和技術(shù)人員們都在供我的嘗試,所以責(zé)任更大”?。二是從電影審美創(chuàng)造來說,它更多取決于導(dǎo)演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功力。因為“導(dǎo)演是各種力量和各種要素的統(tǒng)治者。在他的監(jiān)督指導(dǎo)之下,各個的力量和要素才能夠密切地、有機地、節(jié)奏地組合起來而成了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所以孫瑜說,“導(dǎo)演是一個影片的靈魂,是電影工作中唯一的組織中樞。”?
強調(diào)“導(dǎo)演中心”,強調(diào)導(dǎo)演是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中樞”和“靈魂”,因而是符合電影創(chuàng)作規(guī)律和生產(chǎn)規(guī)律的。此前中國電影攝制盡管也注意到導(dǎo)演的作用,但是,它很少重視導(dǎo)演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只是簡單地“搬演劇本”或一味地“強調(diào)意識”。卜萬蒼曾結(jié)合自己的導(dǎo)演實踐總結(jié)其中的經(jīng)驗教訓(xùn)。他指出,1920年代拍攝影片,“只是一拿到劇本,并不加以選擇地導(dǎo)演起來,只要所導(dǎo)演的同劇本相同,或者甚至于差不多就行了。”1930年代初因為時代浪潮沖擊,電影導(dǎo)演看到“一張優(yōu)良的電影應(yīng)該是要明確地把握住正確的中心意識”的重要性,但又出現(xiàn)一味地“強調(diào)意識”而“疏忽了技巧”的嚴重偏頗。后來是在實踐中得到教訓(xùn),人們認識到電影攝制“光是技巧而沒有正確的主題固然不成其為藝術(shù),但表現(xiàn)方法的拙劣顯然也是藝術(shù)的死敵”,認識到導(dǎo)演在電影創(chuàng)造中其“技巧(形式)和意識(內(nèi)容)是分不開的”?,才對導(dǎo)演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因此電影導(dǎo)演既要注重現(xiàn)實內(nèi)涵,也要注重形式表現(xiàn)和影像創(chuàng)造。費穆當時批評部分左翼電影“內(nèi)容超過了形式”、“沒有適當?shù)男问奖憩F(xiàn)內(nèi)容”,強調(diào)“有了新的內(nèi)容一定要有新的形式”?,主要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言的。所以,他強調(diào)電影導(dǎo)演不能拘泥于“影戲”傳統(tǒng)和一般的電影套路,而要努力發(fā)掘電影表現(xiàn)社會人生的新的形式和手法。即便是在1936年的“國防電影”熱潮中,他仍然強調(diào)電影創(chuàng)造不能公式化、概念化。
那么“導(dǎo)演中心”的理想狀態(tài)是什么呢?費穆提出了“作者電影”的概念。他說:
在理論上講,一個導(dǎo)演即是一部影片的作者。最好是從內(nèi)容到形式由一人完成,思想和手法兩相統(tǒng)一。這是理想的制作。?
費穆1948年在這段話中所說的“作者電影”,雖然與1957年法國電影家巴贊所提倡的導(dǎo)演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要將他個人的鮮明印記持續(xù)地貫穿到其系列作品之中的“作者電影”概念有所不同,但它確實觸及到電影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費穆在這里強調(diào)的是,電影創(chuàng)作如要表達導(dǎo)演對于時代、現(xiàn)實和人的深刻體驗與獨到發(fā)現(xiàn),導(dǎo)演就要有賦予表現(xiàn)對象以激情和生命力的能力,就要有為表現(xiàn)思想情感而熟練駕馭電影技術(shù)的能力。
當然費穆說的是“理想的制作”,電影界的現(xiàn)實情形卻不盡如人意。最突出的,就是費穆在文章《國產(chǎn)片的出路問題》中所指出的,“一個好的導(dǎo)演不一定便是好的編劇”。這個問題在早期中國電影發(fā)展中極其尖銳,到三四十年代仍然十分嚴重。在還沒有條件形成“作者電影”的情況下,電影攝制強調(diào)“導(dǎo)演中心”,必須首先重視電影劇本的創(chuàng)作。而恰恰是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長期以來不被重視而成為中國電影發(fā)展中最明顯、最突出的軟肋。不僅僅是費穆說的“一個好的導(dǎo)演不一定便是好的編劇”的問題,更尖銳的是,制片人不重視編劇,導(dǎo)演不尊重編劇,因此少有劇作家從事電影編劇而出現(xiàn)影壇“劇本荒”。從1932年夏衍、鄭伯奇呼吁“一個劇的成敗,大部分系于劇本。劇本實在是電影的基石”,到1944年桑弧強調(diào)“在整個電影的制作上,劇本的優(yōu)劣仍是判斷那部作品的成敗的最直接的因素”,到1948年費穆感嘆“行萬里者始于足下。想來想去還是先搞劇本”?,等等,都是強調(diào)文學(xué)劇本在電影創(chuàng)造中的重要性。
而在注重文學(xué)劇本的前提下,以“導(dǎo)演中心”的電影創(chuàng)造其審美追求是什么呢?電影家多有探討,具有理論深度的是沈浮的“開麥拉是一支筆”的觀念。沈浮說:
我現(xiàn)在看“開麥拉”已不把它單純的看做“開麥拉”,我是把它看做是一支筆,用它寫曲,用它畫像,用它深掘人類復(fù)雜矛盾的心理。?沈浮的這段話,使人們想起同樣是在1948年,法國電影家阿斯特呂克說“攝影機是自來水筆”,它“能讓藝術(shù)家用來像今天的論文和小說那樣精確無誤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哪怕多么抽象)和愿望”?的著名論述。相比較而言,中國電影家闡釋得更為具體。沈浮把攝影機看作是“筆”,這是一支作家的筆(“用它深掘人類復(fù)雜矛盾的心理”),也是畫家的筆(“用它畫像”)和音樂家的筆(“用它寫曲”)。這段話所涉及的,是有關(guān)人物刻畫的深刻性、影像敘事的繪畫性、鏡頭及場面組接的音樂性等導(dǎo)演創(chuàng)造的重要課題。
早期中國電影大都從故事出發(fā),過分注重劇情。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電影家已經(jīng)認識到情節(jié)是人物性格的發(fā)展史,認識到人是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從而認識到人物刻畫對于電影導(dǎo)演創(chuàng)造的重要性:“從人物性格上來發(fā)展故事是最科學(xué)不過的”,并且“透過人物,還可以寫出這人物所生活的世界、國家和他的社會”。而要做到這一點,沈浮接著指出,最重要的是導(dǎo)演的攝影機鏡頭與片中人物不能“貌合神離”,甚或是“人物是人物,鏡頭是鏡頭”的“各自孤立”,而必須“鏡頭跟著人物走,跟著人物的情緒走;一切以人物為中心,力求做到人物與鏡頭水乳交融,生命抱合。”?
把攝影機看作是畫家的筆而“用它畫像”,沈浮認為,就是要求導(dǎo)演要充分發(fā)揮電影作為視覺藝術(shù),其鏡頭、畫面等影像敘事的繪畫表現(xiàn)力。不僅如此,電影家進一步指出,攝影機的繪畫表現(xiàn)力既要能使電影敘事視覺化,又要能“創(chuàng)造劇中的空氣”即氛圍營造,而“使觀眾與劇中人的環(huán)境同化”。費穆把這看作是電影導(dǎo)演的“法則”之一,并探討了如何創(chuàng)造的幾個要點:一是運用“攝影機本身的性能”,它指“攝影的角度既可以依劇的情調(diào)而變更,感光的強弱,更可以依劇的情緒而變幻”;二是注重“由于攝影的目的物本身而獲得”的效果,如外景拍攝“效果是要由角度、時間、陽光而取決”,內(nèi)景拍攝其“線條的組織與光線的配合”;三是采取“旁敲側(cè)擊的方式”,即“利用周遭的事物,以襯托其主題。”?
鏡頭及場面組接的音樂性,在中國電影實踐中越來越引起導(dǎo)演的重視。少年時期吹奏過軍樂的沈浮對此有更多探索。沈浮強調(diào)導(dǎo)演處理要注重情節(jié)進展、性格刻畫和影像呈現(xiàn)、氛圍營造,但“最主要的還須要把這一切納入一個音樂性中”。他說:“一部戲能把握住它的音樂性,那就節(jié)奏明顯,自成旋律,而觀眾的情緒也就會自自然然地沉入于你的旋律之中,使他們對于一切事物形象易于感受,而內(nèi)心共鳴。”?如此,電影導(dǎo)演就要從影片風(fēng)格出發(fā),對鏡頭及場面的何者應(yīng)長何者應(yīng)短、何者應(yīng)多何者應(yīng)少、何者應(yīng)遠何者應(yīng)近、何者應(yīng)快何者應(yīng)慢,要有準確的把握和組接——“讓每個鏡頭也就像(音樂中的)每個音跳動起來”?,從而使影像內(nèi)容能夠協(xié)調(diào)地、富有節(jié)奏地表現(xiàn)出來。
追求鏡頭、畫面的視覺化創(chuàng)造,注重蒙太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功能,和強調(diào)導(dǎo)演是電影創(chuàng)造的中心,這三者是相互聯(lián)系而又逐層遞進的。如果把鏡頭畫面比作字和詞,把蒙太奇比作組合字詞成句、成文的銀幕文法和攝影修辭,那么,導(dǎo)演中心則是指向影像敘事的目的——運用電影的形式和手法更好地表現(xiàn)電影家對于時代、現(xiàn)實和人的深刻體驗與獨到認識。比之早期占據(jù)主體的“影戲是由扮演的戲劇而攝成的影片”的觀念,不難看出,中國電影家對于電影藝術(shù)特性的把握在漸趨深入。
電影觀念的深化促進電影實踐的成熟。三四十年代出現(xiàn)的《神女》、《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等影片,成為20世紀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第一座高峰。
注釋
①凌鶴:《評〈鐵板紅淚錄〉》,《晨報》,1933年11月13日。
②參見陳犀禾《中國電影美學(xué)的再認識》(《當代電影》1986年第1期)、鐘大豐《“影戲”理論歷史溯源》(《當代電影》1986年第3期)。這兩篇文章在學(xué)界廣有影響,當下仍是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③蔡楚生:《會客室中》,《電影·戲劇》月刊1936年第1卷第2、3期。
④黃子布(夏衍)、席耐芳(鄭伯奇)、柯靈、蘇鳳:《〈城市之夜〉評》,《晨報》,1933年3月9日。
⑤費穆:《〈香雪海〉中的一個小問題——“倒敘法”與“懸想”作用》,《影迷周報》第1卷第5期,1934年10月。
⑥唐納:《〈烈焰〉》(1934),見《三十年代中國電影評論文選》,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第461頁。
⑦洪深:《編劇二十八問》(1934),見《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第 158頁、第159-160頁。
⑧蔡叔聲(夏衍):《一個電影學(xué)徒的手記》,《晨報》,1933年6月20日。
⑨洪深:《序》,見《電影導(dǎo)演論電影腳本論》,北京:晨報出版社,1933年,第1頁。
⑩??孫瑜:《電影導(dǎo)演論》,見《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第174頁,第174頁 ,第 176 頁 。
?張愛玲:《〈太太萬歲〉題記》,上海《大公報》,1947年12月3日。
?劉吶鷗的《影片藝術(shù)論》(《電影周報》第3期,1932年7月)、徐公美的《電影藝術(shù)論》(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等論著,都對1920年代出現(xiàn)在法國、德國的“純粹電影”、“絕對電影”進行了批評。此類電影驅(qū)逐一切文學(xué)的、戲劇的情節(jié)和形象要素,而強調(diào)視覺的、音樂的要素以追求影片的純粹性、絕對性。
??劉吶鷗:《影片藝術(shù)論》,《電影周報》第3期,1932年7月。“開麥拉”為英文camera(攝影機)的音譯。Montage通譯蒙太奇。
?洪深:《編劇二十八問》(1934),見《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第160頁。
?鄭君里:《再論演技》,《聯(lián)華畫報》1935年第5卷第9期至第6卷第5期。
?如夏衍等評論費穆《城市之夜》:“很大膽讓一些人生片斷盡量在銀幕上發(fā)展”,其“手法是非常明確而素樸”,又能“異常成功”而有“特別的力量”,主要“因為 Montage很好”。(黃子布(夏衍)、席耐芳(鄭伯奇)、柯靈、蘇鳳:《〈城市之夜〉評》,1933年 3月 9日《晨報》。)《姊妹花》則“完全是憑著他戲劇的經(jīng)驗而獲得情感上的成功”顯出鄭正秋的優(yōu)勢,而影片讓人感到戲劇化而少電影味,也主要在于“作者沒有很好的使用蒙太奇”。(亞夫:《〈姊妹花〉》,1934年2月24日《晨報》。)
?沈?qū)?夏衍):《〈權(quán)勢與榮譽〉的敘述法及其他》,《晨報》,1934年1月21日。
?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崔君衍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第323頁、第324頁。
?參見沙基:《中國電影藝人訪問記》(1933),見《中國無聲電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第1241頁。
?費穆:《導(dǎo)演的嘗試》,上海《大公報》,1933年2月22日。
?卜萬蒼:《我導(dǎo)演電影的經(jīng)驗》,《電影周刊》第37期,1939年5月。
?平如:《費穆》,《聯(lián)華畫報》第3卷第11期,1934年3月。
?費穆:《國產(chǎn)片的出路問題》,上海《大公報》,1948年2月15日。
?分別見席耐芳(鄭伯奇)、黃子布(夏衍)《〈火山情血〉》(1932年9月16日《晨報》);桑弧《作為導(dǎo)演和劇作者的話(之一)》(《新影壇》第3卷第2期,1944年9月);費穆《國產(chǎn)片的出路問題》(1948年2月15日上海《大公報》)等文。
????沈浮:《“開麥拉是一支筆”》,《影劇叢刊》第2輯,1948年11月。
?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一種新先鋒派的誕生——攝影機是自來水筆》,見馬賽爾·馬爾丹:《電影語言》,何振淦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年,第215頁。
?費穆:《略談“空氣”》,《時代電影》1934年11月號。
2011-06-15
南京大學(xué)“985”三期重大項目“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研究”(NJU985JD04)
責(zé)任編輯 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