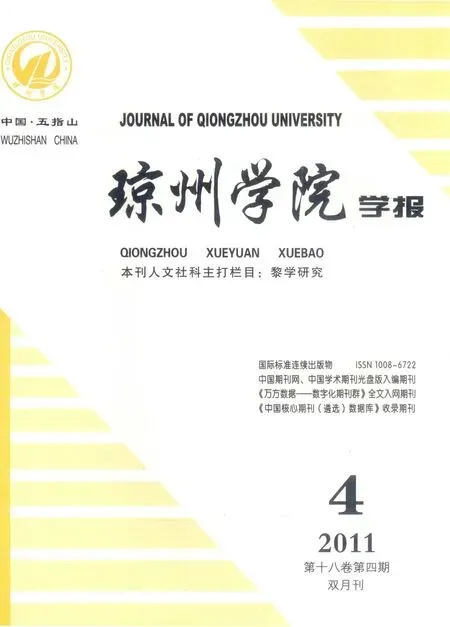黎族族源、族稱及族際關系
陳立浩 高澤強(黎族)
(瓊州學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海南 三亞 572022)
海南黎族歷史悠久,在距今3000年前其先民就在這里披荊斬刺,建立家園,成為最早開發海南島的居民。
一、族源
民族的源流、民族的稱呼都與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它既可反映一個民族的歷史進程,又可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變遷。所以,族源族稱自然成為一定歷史階段的歷史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史學界十分關注黎族的族源問題。不少專家學者根據文獻記載、考古文物并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從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等層面對黎族的族源進行了探索,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黎族系古代百越的一支——駱越的后裔。對此,在文獻記載、考古文物,以及黎族在對百越文化的傳承過程中均可得到證實。
(一)文獻記載與考古文物的印證。古時駱越分布的地域寬廣,相當于今廣西大部、廣東西南部、越南北部及海南島等地。西漢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王相呂嘉反,漢武帝派兵征討,后在嶺南設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珠崖、儋耳兩郡均在海南島上。《漢書》卷六十四下《賈捐之傳》也明確指出駱越是海南島上的土著居民。《資治通鑒》卷二十八《漢紀》胡三省注曰:“余謂今安南之地,古之駱越也。珠崖,蓋亦駱越地”。可見海南島自古就是屬于越地的一部分,而海南島上的居民黎族先民也即“駱越之民”。
文獻記載是考察黎族族源的一個方面,而考古的發掘又為人們探究黎族族源提供了寶貴的文物實證。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海南島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先后在海南島各地都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發掘出黎族先民使用過的各種器物,這些器物表明了海南島原始文化與兩廣大陸的原始文化相似,具有嶺南百越文化特征。
1954年,中南民族學院與廣東省各級有關部門組織隊伍在海南島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先后收集到87件石器,其中有肩石器51件、闊刃石斧21件,另有粗制石斧、石鏟、石錛、石錘、石鑿、石鋤、穿孔石紡輪等。1957年,廣東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與中山大學歷史系合作,赴海南進行文物普查,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遺址共135處。這些文化遺址多坐落于河流兩旁的山崗或臺地上,一部分在沿海港灣的沙丘上,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其中石器498件,有斧、錛、鑿、鏟、矛、犁、戈、管、餅、耳墜、網墜、碗、紡輪、敲砸器、環、珠及各種陶器。
在石器方面,主要有斧、錛、鑿、鋤、鏟等,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錛比較普遍,大型石鏟較多。這種大石鏟(身高20厘米以上)多發現于雷州半島、西江兩岸、廣西南部以及海南島等地,這正是古駱越人及其先民活動的區域。雙肩石器是海南島石器工具中一種較有特色的器物,數量大,分布廣,形式多。這種雙肩石器主要分布在我國的兩廣地區。廣西東興臨海河口、南寧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流域扶綏、邕寧、橫縣等14處貝丘遺址都發現了與海南島型相似的石器工具、網墜等。
在海南島出土的夾砂粗陶、泥質細陶和印紋硬陶3種陶系中,有新石器時代的飾繩紋、各種刻畫紋和籃紋的夾圓底釜、夾砂罐等;也有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晚的素面、夾砂陶器,口沿外翻成圓條或半圓條狀的盆缽類,有些陶器腹部飾鼻、耳等各式耳板;另有周秦時期的云雷紋陶器等。粵中地區常見的夔紋硬陶在這里比較少見。海南島出土的這些陶器既有自己鮮明的地方特點,又與兩廣大陸有極大的關聯。其文化性質與我國兩廣沿海地區出土的器物同屬一個文化類型,特別是與廣西欽州地區、廣東湛江地區(包括雷州半島)發現的原始文化遺存極為相似。
(二)百越文化的傳承。百越是古代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通稱。據專家學者研究,百越民族的稻作、紡織、儋耳、文身、銅鼓銅鑼和干欄建筑等物質文化都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特征。百越文化在黎族地區的遺存和傳播,在建國前就大量存在于黎族社會中。下面幾種百越文化在黎族地區的傳承,從多方面印證了黎族與百越族的歷史淵源關系。
稻作文化。1973年發現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表明當時河姆渡地區居民已經從事以栽培水稻為主體的農業生產,并開始飼養豬、狗等家畜。河姆渡文化是南島語族和百越民族的源頭,黎族是百越民族的后代,其先民進入海南島自然也將稻作文化帶了進來。而海南島是我國野生稻分布的地區之一,這里有豐富的稻種和優越的自然條件,黎族先民在海南島傳承稻作文化,大興稻耕農業,成為我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稻作民族之一。
紡織文化。百越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頗具特色的紡織文化。在遙遠的古代,黎族先民就已興起了樹皮布文化。據古文獻記載“……號曰生黎,巢居洞深,績木皮為衣,以木棉為毯。”①《太平寰宇記》卷169《瓊州》條.這里的“績木皮為衣”指的便是樹皮布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黎族地區又有吉貝文化的興起。“吉貝”是黎語的漢字記音,“吉”為黎語前綴音,“貝”是黎語的“棉花”之意。古代文獻有寫成“織貝”,應是指“織棉花”的之意。在我國,除黎族外,百越后裔的壯族、傣族等亦稱棉花為“貝”。現今黎族仍稱棉花為“貝”、“古貝”、“吉貝”等。春秋時期《尚書·禹貢》載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這里的“結貝”指的便是黎族先民的紡織。黎族先民所從事的紡織生產活動傳承了百越文化,體現了與百越族深遠的歷史淵源關系。
儋耳文化。據古文獻記載,“儋耳”本指古部族名,一在北荒,一在海南島。因這些古代部族皆“鎪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故興起儋耳習俗。范曄的《后漢書·哀牢傳》中有載,古代的云南地區有部分哀牢夷“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在同書的《南蠻傳》中對古代海南島的部族也有類似的記載:“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直至20世紀50年代,有一些地方的黎族婦女還常常佩戴大耳環,以致把耳朵拉長,下垂到肩上,這應該是歷史上“儋耳”習俗的遺存。
文身文化。文身是一種膚體裝飾的習俗,有些民族的文身與宗教有關,有些民族以此來表示成年,有些民族以此作為氏族、部落的標志等等。在世界范圍內,文身習俗廣泛流行于東南亞、東北亞、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等。在我國,文身的記載最早見于《山海經》、《莊子》等古籍。從文獻資料看,我國古代的“東夷”和“百越”兩大系統的民族都有文身習俗。20世紀50年代前,海南島的黎族婦女大都流行文身,這反映了黎族與百越民族的歷史文化淵源關系的。
銅鼓銅鑼文化。銅鼓主要分布在我國的華南和西南地區。西漢時期,馬援在南征百越“于交趾得駱越銅鼓”②王俞春.海南島移民史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8月.。考古資料表明,在嶺南古代百越民族聚居的地區均有銅鼓出現。雖然歷史文獻對海南黎族使用銅鼓沒有任何記載,但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海南島發現不少銅鼓,專家們認為這有可能是由進入海南島的所謂“駱越之人”帶進來的。黎族在節慶或祭祀之時常使用鑼鼓,其銅鼓銅鑼文化與百越民族一脈相承。
干欄建筑文化。“干欄”是一種用竹、木支撐使房屋離開地面成為上下兩層的高腳屋,樓上住人,樓下圈畜。這種建筑在古代廣泛分布于我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干欄”在有些古籍中也有稱作“高欄”、“閣欄”、“葛欄”、“麻欄”等。據考古發掘,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浙江余姚河姆渡、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都有樁上建筑遺跡發現,也就是“干欄”式建筑型。在文獻記載方面,先秦著作就已對“干欄”式建筑有所反映,“上古之世,……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巢氏”。③韓非子·五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今白沙黎族自治縣和五指山市一帶依然能見到典型的干欄式居屋,“黎,海南四郡島上蠻也。……屋宇以竹為柵,下以畜牧,人處其上”。④[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下).指的便是這種居屋,也就是現今海南人所稱的“船形屋”。隨著社會的發展,“船形屋”后來慢慢演變出另一種形式,即從高腳、低腳“船形屋”發展到居地式的“船形屋”。但是不論如何演變,黎族的“船形屋”是屬于古代遺留下來的“干欄”式建筑的一種派生類型。
二、族稱
黎族的族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黎族自己的稱呼以及內部之間的互稱,即自稱;另一種是其他民族對黎族的稱呼,即他稱。
(一)自稱。黎族有自己本民族語稱呼的族稱。歷史上,黎族對民族概念的認識非常有限,認為世界只有黎族和非黎族兩種,因此在與黎族以外其他民族交往時都一律自稱為“賽[ai5]3”,“賽”(也有寫作“篩”)含有“主人、本族人、自己人”的意思;而把其他的民族一律稱為“美[moi55]”或“邁[mai55],“美”即是“客人、外人、外族”之意。隨著黎族接觸的外族人多了,故往往在“美”(邁)稱的后面貫上特指的對象之名來分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人,如“美海南”(海南漢族)、“美北京”(北京漢族)、“美苗”(苗族)、“美外國”(外國人)等。
“哈[ha11]”習慣寫作“侾[ha11]”,古書上又有寫為“霞、遐、夏”,自稱為“賽[ai5]3”,因居住在黎族聚居區的外圍地區,在和其他方言的黎族交往時常稱自己為“哈”,故而得名。“哈”內部還分許多小支,小支中也有自己的自稱,主要有“博”(哈應)、“羅活”、“抱顯”、“抱懷”、“止強”、“止貢”、“抱由”、“抱曼”等,這些稱呼大部分為古代的峒名。
“杞 [gei11]”原作“岐”,自稱為“賽 [ai5]3”,但在和“臺”(加茂方言)黎族交往時又稱自己為“杞[gei11]”,故而得名。
“臺 [thai11]”自稱為“賽 [ai5]3”,在20世紀50年代黎語調查時才發現該方言,因專家首先調查的地方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的加茂鎮,故被稱為“加茂[kh?55vou53]黎”,在大部分的出版物上也多稱為“賽黎”,年輕人則已變讀為“臺[thai11]”,故得名。
“美孚 [mo:i53fau53]”自稱為“賽 [ai5]3”,但又被“哈”稱為“美孚”,他們也接受了“美孚”這一稱呼,故而得名。
盡管黎族內部有不少的自稱和互稱,并形成了五大方言,但在和外族交往時都一致稱為“賽[ai5]3”,這表明了黎族內部的一致性和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黎族“賽”的這個自稱源遠流長,“賽”的稱呼在后來的黎語中出現了不少的變讀,如“dai53”、“thai11”、“tsai53”、“?ai53”等。“賽”和“泰”、“傣”、“徠”等音比較接近,透過這些稱呼也許對探討壯侗語族遠古自稱有一定的幫助。
(二)他稱。海南有4個世居民族,除黎族外還有漢族、苗族、回族3個民族。這3個民族都自己的民族語言,他們透過自己的語言來稱呼黎族,這3個民族都有不同的稱呼。
漢族對黎族的稱呼主要為“黎”、“黎人”、“黎族”等。漢族與黎族的接觸,最早要追溯到西漢在海南島設置珠崖、儋耳兩郡時期,當時的漢文文獻中已能具體地將島上的先住民稱為“駱越之人”,這大概是漢族人對黎族的最早稱呼,當然這個稱呼包括了當時廣東、廣西以及越南北部的古代民族。東漢時,“駱越”稱為“里”、“蠻”取代,如“建武十二年(前36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①后漢書·南蠻列傳(卷86).。這里的“里”仍是泛指華南一帶的少數民族,其中包括生活在海南島的黎族先民。三國時“里”字轉化為“俚”,“廣東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②[吳]萬震.南州異物志.。到隋唐時,漢文史籍中又出現“俚僚”、“夷僚”并稱,同樣泛指我國南方少數民族。到唐后期,“黎”作為黎族的族稱第一次出現于史籍上,“儋、振夷黎,海畔采(貝)以為貨”③[唐]劉恂.嶺表錄異.。宋代后,各類漢文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如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在卷169《嶺南道十三》中敘述了儋州、瓊州的“生黎”風俗,私人著作中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蠻》篇辟有“黎”專目,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志》以及蘇軾父子謫居海南時的詩文等均以“黎”字專指黎族,于是“黎”稱一直沿用至今,成為漢族對黎族的專有稱呼。
在海南島的漢族,除了操本民族各種方言土語外,還有以操少數民族語為主的漢族,如臨高人和哥隆人(村人),他們對黎族也有自己的稱呼。臨高人把黎族稱為“勒林[lak55lim53]”,(意為“外族人”、“非自己人”),而把操海南話的漢族人稱為“勒科[lak55khak55]”(意即“客”)或“港科 [ko:?55khak55]”(意即“講客”)。這種把黎族視為外族,而把操海南話的漢人稱為“客”,反映了臨高人對島上3個人類群體的認識。哥隆人(村人)自稱為“謨[mo?44]”,也稱“奧帆 [?au53fa?53]”。“謨”是村人的真正自稱,而“奧帆”是“村人”之意,黎族則稱為“帝傣[di55tai51]”(“帝”為“孩子”之意,“傣”為“黎”之意)。臨高人對黎族的稱呼暫難于考證,但哥隆人(村人)對黎族的“傣[di55tai51]”稱明顯是黎族自稱“賽[ai5]3”的變讀。
海南苗族大約在明代中葉進入海南島,這才有機會和黎族接觸。海南苗族自稱為“金弟門[kam55ti51mu:n21]”,把其他民族一律稱為“嘟[tao11]”。為了區別漢族和黎族,漢族被稱為“嘟且[tao11thse11]”,而黎族則稱為“嘟唉[tao11?gai11]”。“唉 [?gai11]”稱有可能是從黎族杞方言的自稱“[gei11]”中借用過來。
海南回族對黎族的稱呼與漢族、苗族不同,他們自稱為“阿咋[a44tha21]”,把漢族稱為“阿魯[a44lu11]”,而黎族則稱為“阿徠[a44lai21]”。“徠[lai21]”稱與黎族自稱“賽[ai5]3”近似,也應是黎族自稱的變讀。
由上可見,黎族的他稱應該有5個:“黎族”、“黎人”(漢族稱法),“勒林”(臨高人稱法),“帝傣”(哥隆人稱法),“嘟唉”(苗族稱法),“阿徠”(回族稱法)。
三、族際關系
海南島是一個僅有3400多平方公里的島嶼,遠離祖國大陸。由于地理位置、交通不便等諸多條件的限制,被歷代封建王朝視為“荒蠻”之地,成為朝廷流放貶官謫臣的地方。然而海南島畢竟處于華南至東南亞這一廣闊地域的中心,這就注定了海南島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廣闊地域的遠古文化傳播和交匯之地①高澤強:《傳統服飾中的文化視野——試說黎族服飾文化蘊含及其社會傳承》,《全球化下的文化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年9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辦。。海南黎族,從其歷史文化淵源上看,她與祖國南方眾多民族和境外南島地域相關民族皆有親密的族際關系。
(一)與中國南方百越后裔諸民族的族際關系。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百,百越雜處,各有種姓。”這是指自今浙江溫州至越南北部整個東南沿海地區為百越所居之地。此外,還包括今山東南部、江蘇、上海、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的一部分以及海南等省市。百越支系眾多,諸如大越、東甌、于越、閩越、揚越、南越、西甌、駱越、滇越、山越等。本章在前文論述黎族族源時,曾指出“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黎族系古代百越的一支——駱越的后裔”。百越是古代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通稱,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指的對象及所包含的范圍都所不同。在四五千年前,百越包括了今南島語族的先民,而在兩三千年前,則僅指今壯侗語族的先民。當今學術界的百越民族概念,多指壯侗語族的先民。
壯侗語族是我國語言學界的學術名詞,國外一般稱為“侗臺語族”或“臺語族”,專指分布于我國廣東、廣西、云南、貴州、海南等地的壯、侗、布依、傣、黎、水等民族,跟分布于東南亞地區的泰國、老撾主體民族及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度等國的一些少數民族。
黎語屬于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中的黎語支,與同一語族的壯語、侗語、布依語、傣語、水語以及海南島上的臨高話、哥隆話有較為密切的親屬關系。每個民族的語言都反映每個民族的文化特征,特別是那些表現文化底層的詞匯,更能反映出各民族語言之間的歷史文化淵源關系。黎語中的“水田”、“稻草”、“木杵”、“糖”、“簸箕”、“棉花”、“甘薯”、“竽頭”、“小米”、“豬”、“狗”等基本詞匯與壯、布依、傣、侗等語同源。黎語中的“那”、“什(音達)”是“田”之意,“南”是“水”之意,在我國的廣東、廣西、云南等省區,境外的泰國、老撾、緬甸和越南北部,都有冠以“那”、“南”等字音的地名,文化內涵相一致。這反映了上述的廣大地區,遠古時代一直活躍著與黎族淵源相同或相近的人類共同體,這便是壯侗語族②高澤強:《黎族古籍及其價值》,載于《拂拭歷史塵埃》,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原載于《民族古籍》,1999年第4期。。黎族就是壯侗語族語在海南島經過千百年的歷史發展演變,融合了先期在海南島聚居生活的其他人類共同體(南島語先民)而最后形成的。
(二)與祖國寶島臺灣原住民族的族際關系。臺灣的原住民族據最新統計共有12個,在國內通稱為高山族。海南黎族與臺灣高山族有著久遠而親密的族際關系。德國人類學家史圖博曾有這樣的講述:“我在旅行海南島之前。曾經跑遍了臺灣,對于兩個島的土著居民在許多方面的相似,曾為此而感到驚奇,特別是黎族的一支與臺灣南部的一個民族之間,有著明顯的一致,尤其在衣服方面,看來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更進一步在肉體的特征方面,也有一致的地方。可以假定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③史圖博:《海南島民族志》。在我們看來,這不是假定,而是事實。它具體表現以下幾方面:
其一,從語言上看,高山族所講的語言為南島語族,也就是馬來波利尼西來語系。這種語系分布于現今北起我國臺灣、南至西太平洋三大群島、東起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等這廣闊的區域中,操這種語言的民族群體都具有民族語言親緣關系及文化內涵相似的關系。
1980年出版的《漢藏語系語言學論文選譯》集中,有位美國學者認為,黎語在“形態學和音韻學上的特點,與其說接近于印尼語,不如說接近臺語,而加岱語(包括黎語)的詞匯成分既有印尼語明顯的印痕,也有同樣深厚的臺語的印痕。簡單地說,數詞和零散的名詞,代名詞以及形容詞表明與印尼語近似,而許多其余成分則表明與臺語近似……臺語和加岱語,印尼語有一種真正發生學的聯系,而不是和漢語、藏緬語有這種聯系,不過在漢語影響下有了很大的變化罷了”④本尼迪克特:《臺語、加岱語和印度尼西亞語——東南亞的一個新的聯盟》,《漢藏語系語言學論文選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室、中國民族語言學術討論會秘書處合編。。“很可能黎語保留了某些印尼文化特征而這些特征早已為中國大陸漢化了的加岱部族所拋棄。很明顯,臺—加岱—印尼共同的人種圖象已被破壞而無從修整”⑤本尼迪克特:《臺語、加岱語和印度尼西亞語——東南亞的一個新的聯盟》,《漢藏語系語言學論文選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室、中國民族語言學術討論會秘書處合編。。這是相關學者第一次將黎語與南島語聯系起來的觀點。
到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國際學術交流頻繁,我國專家學者對壯侗語族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有學者認為“在語言學上,不少學者對南方壯侗語族的許多人群做了深入的語言調查,并與今南島語族語言進行比較,發現黎族、水族、侗族、壯族等民族的方言和口語與今高山族、菲律賓土著、馬來語等南島語言在基本詞匯上有很大的共性。同樣的現象存在于南方漢語方言中,閩、粵漢語方言和客家方言的語言調查表明,南方漢語方言的構詞和語音與中國臺灣阿美族、排灣族等高山族分支語言有很大的共性”⑥吳春明:《“南島語族”起源與華南民族考古》,《東南考古研究》第三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有的學者明確指出:黎語乃至整個壯侗語族早期可能使用原始馬來語,后來由于長時間地、大面積地受到漢語的影響而發生融合同化,完成了“類型轉換”,轉變為與漢藏語同一體系的孤立型語言⑦羅美珍:《試論臺語的系屬問題》,《民族語文》,1983年第2期;倪大白:《中國的壯侗語與南島語》,《中央民族學學報》1988年第3期;戴慶廈:《從藏緬語看壯侗語與漢語的關系》,《中央民族學學報增刊》,1990年第11期。。有學者還提出“黎語中的一些南島語詞,是獨特的,與壯傣、侗水的不同,是黎語的底層詞,而不是它們共同的底層詞或借詞”①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
所以,雖然黎語屬于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但黎語的底層詞保留著一些南島語詞,它反映了黎族先民與南島語先民的密切關系,從中也透露出黎族與臺灣原住民高山族的親緣關系。
其二,海南和臺灣兩島少數民族的族源問題一直是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專家們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學者們從考古發現、生產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加大了對黎族和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力度。
在考古發現方面,海南島的多處石器文化遺址和臺灣的新舊石器、陶器,都與祖國大陸同屬一個文化系統,其“文化的創造者和文化內涵均屬于大陸古越族之前的古人類和古文化,且組成一個完整古文化系統,有力地證明黎族、高山族與大陸古越族同一來源”②司徒尚紀:《淺論海南黎族與高山族同源異流》,2002年臺灣少數民族海南省親交流活動理論研究會論文。。
在生產活動和內容方面,諸強如采集、狩獵、捕撈、樹皮布、刀耕火種、農耕、種棉、紡織和產品的分配方式等等,黎族與高山族都有很多的相同和相似性。樹皮布是南島語族主要的古文化特征之一,黎族與高山族在古代均會制作樹皮布,制作方法大同小異。同樣,兩島的少數民族都喜歡狩獵,獵前舉行祭祀儀式,保佑獲得獵物,獵獲后平均分配,且見者有份。黎族與高山族紡織時大都是采取坐地式,利用腰織機來進行紡織。由此專家們認為:遠古時代的海南島和臺灣島都是屬于南島語族文化影響的范圍,或者可以說是南島語族先民在遷徙過程中,都有部分人在這兩個島居住了下來。
在風俗習慣上,黎族與高山族的相同性更多。如文身、干欄式居屋、少女房(隆閨)、貫首衣、谷倉、酸魚酸肉(魚茶)、自由婚戀、族外婚、不落夫家、嗜食檳榔、父子聯名、打草結為標志、血緣氏族、村峒組織、互不隸屬的部落王國、長老村老制等。
在宗教信仰上,黎族有敬雷崇蛇的習俗,臺灣高山族亦如此。黎族流行蛇祖傳說,有“蛇女婿”、“蚺蛇青年”等人蛇婚配故事,高山族也有自稱為蛇的子孫,崇拜百步蛇。此外兩族都相信萬物有靈,認為日月星辰、風云雷電、河水山林等都神靈而加于敬仰。
其三,黎族和高山族的親緣關系,在人體的基因研究上也得到了證實。1999年,相關專家采集了中國臺灣5個少數民族和海南黎族人的血樣,通過DNA研究發現,中國臺灣的阿美、泰雅、布農、排灣4個民族男性的主要Y染色體類型與黎族男性的主要染色體類型完全一致。據此,中華民族史研究會2001年10月在海南省海口市主持召開的“瓊臺少數民族學術文化研討會”,與會兩岸學者都一致認為:中國臺灣的阿美、泰雅、布農、排彎等先住民和海南黎族都是古越人的后裔,海南黎族和中國臺灣先住民自古以來就是“親戚”③史式、黃大受:《臺灣先住民史》,九州出版社,1999年。。又據《海南日報》新華社海口電:2001年10月31日(莊裴、胡辛)載:“中國遺傳學所進行的一項DNA研究成果表明,海南黎族與臺灣四個少數民族有著共同的祖先——七千多年于浙江河姆渡的古代百越人,因此他們是兄弟‘關系’。”
從以上三個方面,不難看出海南黎族與祖國寶島臺灣原住民族高山族親密的族際關系。
(三)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相關民族的族際關系。壯侗語族、南島語族在當今分布的范圍極其廣泛,除了我國的華南、西南地區和臺灣地區外,東南亞至大洋洲、印度洋這一廣闊地域的越南、泰國、老撾、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國均有分布。黎族先民與壯侗語諸民族、南島語諸民族的先民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關系,由此推之,黎族與東南亞等地區的國家不少民族有親密的族際關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民俗文化方面,更是表現出黎族與東南亞部分國家民族的族際關系。如“儋耳文化”,在東南亞的泰撣民族,沙勞越山區的達雅克人,婆羅洲的依班人,菲律賓的英哥羅人,也喜大耳環、銀項圈。這些民族的儋耳習俗,與黎族的儋耳習俗很相似,這說明了他們相互有文化上的交往,抑或是文化傳承的結果,又如文身文化,在東南亞幾大語族的相關民族中都曾與黎族一樣都流行文身習俗。這些都說明了他們相互間有文化的交流,抑或是文化傳承的結果。
綜上所述,黎族多方面的族際關系,表現出了黎學研究具有“族際性”和“國際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