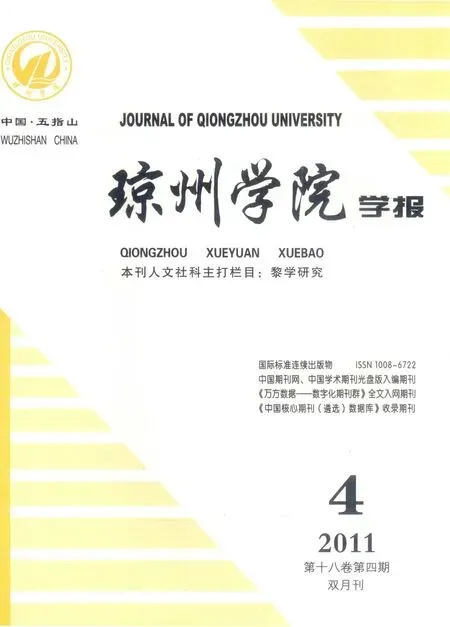黎族原始氏族社會簡述
高澤強(黎族) 陳立浩
(瓊州學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海南 三亞 572022)
黎族的原始氏族社會經歷了母系氏族社會和父系氏族社會,黎族的“合畝制”及村、峒組織就是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形成的。這些制度文化源遠流長,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仍存在某些殘余。
一、母系氏族公社
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黎族的遠古祖先以血緣為紐帶,組成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是當時社會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經濟單位,也是社會制度的基礎。由于當時婦女在生產中不但成為主要的經濟生產者,而且在紡織、制陶和家務勞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公社凡處理重大事情,如生產活動、宗教活動、集會、議事、外交等大多是由輩份高、年歲大的婦女來主持。這種情況在宋代的文獻中曾有記載,如“其俗賤男貴女有事則女為政”、“遇有事婦人主之,男不敢預也”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在黎族“合畝制”仍有母系氏族的殘余,男女有著嚴格的自然分工,婦女們專門從事稻田里的插秧、除草、收割、儲藏、加工等工作,婦女還被認為是唯一能夠掌握紡織和制陶技術的勞動者。“合畝制”地區在開始插秧或收割的時候,要由“畝頭”的妻子先做一種宗教性的儀式后,“合畝”內的其他婦女才能下田插秧或收割。
在婚姻方面,黎族的遠古祖先和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先民一樣,都經歷過舊石器時代的血緣婚和血緣家族階段,這在黎族地區流傳的洪水神話有著充分的反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看到血親婚配的弊端,從而排斥族內婚,族內婚被社會譴責,族外婚得到社會的承認和肯定。族外婚是人類自身發展的一次偉大變革,它使人類自身發展的優勝劣汰達到了一個高度,從而更進一步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當時對偶婚盛行,婦女在氏族中和社會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而受到尊敬,母權制成為社會的基礎。
黎族在母系氏族社會時期,還以某些動植物以及一些虛擬的特定物來作為血緣集團的稱號,如龍、水牛、羊、芭蕉、番薯、竹子、水田、陶等,這些都是氏族的圖騰標志。
二、父系氏族公社
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男性逐步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者,婦女退居次要地位,黎族社會隨之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過渡。從黎族地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來看,當時的人們已過上定居的生活,有自己的村落。他們居住在靠近河流或海灣的平原臺地和沙丘上,使用裝上木柄的石斧、石錛、石鏟砍伐樹木,鉆木取火,開拓荒原,進行農業發展史上稱為“刀耕火種”的燒墾農業。這時,還出現了“牛踩田”的耕作方式,由三四個人把幾頭牛乃至幾十頭牛趕到水田中,讓牛朝著同一個方向繞著水田走,直到將水田的泥土踩爛,然后用長木棒將泥土平整,就可以插秧苗了。從海南島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常伴有漢代器物出現這一情況來看,在部分黎族地區特別是沿海平原地區,父系氏族公社最遲在漢代或較早些時候就已經形成。
此時在婚姻上,隨著原始農業的不斷發展使男子占居主導地位而使婦女退為次要地位,婚姻也從對偶婚向以體現父系特征的一妻一夫制過渡。
秦漢時期,金屬器特別是鐵器傳入海南島被用于農業上,使黎族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的燒墾農業迅速向鋤耕農業邁進,鋤耕農業漸漸占居主導地位。而燒墾農業在“合畝制”地區仍然較為普遍,有的地方還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
三、黎族地區的“合畝制”
“合畝制”是黎族特有的生產和社會組織,它既是黎族最早的一種社會制度,又是黎族社會中最具民族特色一種社會形態。從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關系來看,“合畝制”屬于原始社會末期的一種生產方式。“合畝[kam55ma:u55]”為海南方言記黎語,“合”意為“合在一起”,而“畝”則為“同一個血緣集團”之意,全意是“合在一起的血緣集團”。“合畝”也稱為“紋茂”,這個“茂”和“合畝”的“畝”,以及黎族地區中常出現的地名如“毛陽”、“毛道”的“毛”,他們的意思是一樣的,意即“家族、氏族”,可延伸為“姓氏”即“黎姓”。由于是同一個血緣集團的“合畝”共同生活共同勞動,所以黎語常稱為“翁堂沃共”、“翁堂沃達沃昂”,意即“大伙在一起做工”,“大家一起種田、種‘山蘭’”。
“合畝制”地區分布在昔日保亭、樂東、瓊中和白沙交界的毗連地帶,即當時的毛道、毛陽、番陽、紅山、通什、暢好、南圣、毛岸、毛感等9個鄉(鎮)。這一帶峰巒重疊,“深林密菁”、“懸崖阻絕”,歷史上曾是“外人不復跡”之地。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相當緩慢。
(一)“合畝制”的基本特征。“合畝制”的組織基礎是血緣關系,同血緣的“合畝”可稱為親屬“合畝”,主要由父子、兄弟、叔侄、堂兄弟、岳父、女婿、舅父、外甥等直系或旁系血親組成。部分“合畝”有非血緣的窮困人員參加,人們稱這類“合畝”為混合“合畝”。“合畝”有大有小,小的約6戶,大的有幾十戶。
一個“合畝”有一位“畝頭”,由“合畝”中最有能力的長輩擔任,他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已婚(亡妻后尚未續弦者不能當畝頭)、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和傳統知識、懂得領導和指揮生產、能夠舉行生產前后的宗教儀式。畝頭有“帶頭犁田的老人”之意,也即“犁第一路田的人”的意思。畝頭是“合畝”內一畝之長,他按傳統的風俗習慣來領導“合畝”,負責組織計劃和領導指揮全畝進行生產,畝眾對畝頭絕對服從。不論是“合畝”內部還是“合畝”外的一切大小事,畝頭都要出面協商、調解和處理,對怠工的畝眾有權批評教育,對外則代表“合畝”。犁田、收割、選地等農事活動要由畝頭領頭做,畝眾才下田耕作。畝頭的妻子也是畝內婦女勞動生產的帶頭人,拔秧、插秧割稻、捻稻等要由畝頭妻子領頭,婦女們才跟著下田勞動。畝頭和畝眾一樣參加集體勞動,收獲后分配由畝頭掌握,勞動產品分配比較平等。
“合畝制”地區的生產有嚴格的性別分工。男子負責犁田、趕牛踩田、挑擔、砍山、點穴(種山蘭);婦女負責拔秧、插秧、割稻、下種(山蘭種) 等。老幼則按體力大小分工,老人平時看管水田里的水,照顧幼兒,稻谷成熟時負責趕鳥;小孩則負責放牛或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由于男女之間的自然分工成為傳統的習慣,一般男不幫女,女不幫男,但都是共同勞動,同出同歸。
“合畝制”地區對勞動產品的分配原則是按戶平均分配,對人口多少勞動力多寡都不加照顧。分配前先將5種類型的糧留下:一是種子(留下作為來年稻種);二是“稻公稻母”(收獲時由畝頭保管留做備荒或待客用的谷子,實際歸畝頭所有,人們認為如不留下“稻公稻母”給畝頭,則來年不會得到豐收);三是“留新禾”(收割時先留10~12把稻谷約有24斤給畝頭煮飯釀酒,人們在畝頭家吃了新谷后畝眾才能開始吃新糧,有祈福豐年之意);四是“聚餐糧”(留谷幾十斤,交畝頭釀酒,待來年插完秧后全體合畝成員共飲);五是“公家糧”、“青年糧”(留“公家糧”的數量由大家商定,需要動用也由大家商定,畝頭可以用它來待客,凡結婚、蓋房或者有困難的“合畝”成員也可以動用此糧。有的“合畝”還設有“青年糧”,一般是勞動力強的給24把約48斤,勞動力弱的給12把,當年要辦婚事的青年也留72把以備釀酒)。除去以上留糧后,無論畝頭、畝眾都按戶平均分配。親屬“合畝”的分配比較平均,混合“合畝”對外來戶可能少分一些。人口多的戶,如果糧食不夠用時,可向畝內其他戶借或懇求畝頭分一些“稻公稻母”,這些借糧可以還也可以不還。在不妨礙集體勞動的情況下,“合畝”內成員可以從事以戶為單位的個體勞動,砍山種植旱稻雜糧,并在房前屋后種植各種水果疏菜,其收獲歸各戶所有。
(二)“合畝制”的發展演變。隨著社會的發展,“合畝制”發展演變呈三大類型:第一類,“合畝”由有血緣的親屬組成,這類“合畝”規模很小,一般是幾戶人家組成。其原始社會殘余較多,原始社會的特色較鮮明。“合畝”內生產合作共耕,產品按戶平均分配,畝頭和畝眾一起參加勞動,沒有剝削現象;第二類,“合畝”的組成以血緣關系為主,但卻包括一些非血緣關系的外來戶,畝眾中有了龍仔、工仔。同第一類“合畝”比,這類“合畝”規模也不大,一個“合畝”大體也只有幾戶人家。“合畝”的畝頭一般都較富裕,畝內還出現一些富裕戶,他們在分配中往往多占產品,或者向“合畝”內外貧苦成員放債、出租土地等,產生了輕微的剝削;第三類,“合畝”的組成有一定的血緣關系,而非血緣關系的外來戶較多,龍仔、工仔要占一半以上。這類“合畝”的規模比第一、第二類大,一般的六七戶,大的則有十戶以上。畝頭不參加生產勞動,有的只參加輔助勞動,但分配時占大量產品,不按戶平均分配。畝頭通過租佃、高利貸和處罰等方式,進行嚴重的剝削。①陳立浩主編:《黎族“合畝制”研究》,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
上述第一類型的“合畝”應屬原生形態的,它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伴隨著時間的推移,依次演化出第二、第三類“合畝”。我們從三大類型“合畝”的對比中,看出“合畝”的血緣關系和所有制關系有著明顯的變化,展示出“合畝”發展演變的軌跡。從血緣關系看,其演變的進程是由強到弱,“合畝”的血緣關系逐漸削弱,地域關系不斷增強。在歷史上,“合畝”成員原來都是有血緣關系的。在第一類“合畝”內,成員全是以血緣為紐帶,依據血緣關系而組成的,它是血緣親屬組成的“合畝”。但是,隨著“合畝”的發展,“合畝”又出現了新的分化趨勢:血緣親屬從遠至近,逐漸從“合畝”內分離出去。所以,“合畝”在分化中產生的一代代的“新合畝”,便接收了越來越多的非血緣關系的龍仔、工仔等外來戶。這樣,原來的血緣削弱了,地域關系隨之加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合畝制”地區進入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時代,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若干“合畝”聯合組建成一個個的農業合作社。至此,黎族社會的“合畝制”完成了數千年的歷史使命。②陳立浩主編:《黎族“合畝制”研究》,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
四、黎族社會的村、峒組織
歷史上村、峒組織是黎族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也是黎族人民的聯系紐帶,不同的村、峒代表著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血緣集團。峒體現部落關系,而村則體現血緣關系,黎族的原始村落是由同一血緣關系的人群組成的。
(一)村組織。黎族的村落是指純粹的自然村莊。村莊在黎語中哈方言稱為“抱[bau11]”,杞方言稱為“番”,潤方言稱為“方”,臺(加茂)方言稱為“芬”。黎族村落的組成有兩種情況:一是由單一姓氏(父系)構成,另一是由多種姓氏組成。第一種的黎族村莊是在同一個血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同村基本都是同姓,不能通婚,這類村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已經很少;第二種的黎族村莊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經濟文化交往日益頻繁,加上戰亂等各種因素,人們遷徙不斷,因此才使單純的血緣村莊注入了更多其他血緣集團的成員,這類村莊占多數。黎族的村與村之間經常往來,互通友好,村民與村民之間在生活、生產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黎族村落有這樣的共同特點:第一,村落規模不大;第二,選址多依山傍水,靠近耕地;第三,村內村外、庭前院后的空地都被利用起來種植各種熱帶作物,富有熱帶村落風光;第四,較大的村落是長期定居下來形成的,村落整體布置已有較為固定的模式;第五,一般的村落都在村四周設置障礙物,外邊人很難進入村內,具有防備護村作用。
黎族地區每個村莊都有村頭,黎語一般稱“奧雅[ao53za53]”,“奧”是人,“雅”是老,“奧雅”就是“老人”之意。“奧雅”這個稱謂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年老而秉公辦事、平時常替人解決糾紛的一般老人,這種老人很受村人尊重,村中凡偶有爭吵糾紛事情,多由他們出面處理,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可把自己的父親母親尊稱為“奧雅”;另一種是指在舊社會中有權有勢、政治上有地位的總管、團董或鄉長、保長一類的人。“村頭”黎語稱“俄抱[gwau11bau11]”或“俄番”、“俄方”等。黎族村寨中每一個村至少有一名以上的村頭。與峒長、哨官、頭家以及后來的團董、鄉長、保長、甲長不同,村頭不是選舉產生也不是委任。村里凡有輩分最長、明事理、能為群眾處理糾紛,并具有一定組織能力的人,就自然會被群眾公認為村頭,他們多為自然形成。這類村頭一般有以下特點:輩份高、明事理、辦事公正、有組織能力、能說會道、有威望、見識廣等等。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階級社會在黎族社會確立,封建官府看到村頭在黎族群眾中的威信,因此在一些村頭中委以重任,使這些村頭有的后來變為地方政權人物,兼具雙重身份,更有甚者發展到與封建統治階級勾結一起獨霸一方,剝削黎族百姓,逐步蛻變為統治階級的成員。
(二)峒組織。峒是歷史上黎族社會獨具特色的一種社會組織,它是由多個黎族村落所組成,一般一個小峒相當黎族的一個小部落。在未被封建王朝統治的地區,峒是維持黎族社會內部正常秩序和推動黎族社會發展的社會政治組織。黎族峒的組織歷史悠久,對黎族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峒”黎語稱為“kom55”,原意是指“人們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漢語音譯為“弓”或“峒”。在封建王朝實施統治與管轄的黎族地區,峒已與封建統治政權的基層組織融為一體,成為封建統治政權基層組織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在歷代黎族反封建斗爭過程中,峒的組織又明顯表現出其軍事組織性質。從“峒”的原來組織形式和職能看,它應是黎族的一種古老的氏族部落組織,是黎族遠古祖先由采集、游獵生活向定居的原始農業生活過渡后漸漸形成的。
黎族峒組織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共同的地域。每個峒有固定的地域,其地域一般以山嶺、河流為界,有的地方要立碑、砌石,有的地方則種樹、栽竹、插木板、埋牛角等等作標志。第二,血緣紐帶一般是峒組織的基礎。峒有大峒和小峒之分,一個大峒往往包括幾個小峒。每個小峒最初是由同一血緣集團的人組成的,內部嚴禁通婚。第三,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行動準則。凡同住一個峒內的人,都是峒的成員,每個成員對峒的疆界有保衛責任;峒內成員間有相互援助和保護的義務,要共同負擔械斗時向外請援兵的費用;峒內成員在峒頭(又稱峒首或峒主)的選舉、罷免時有權參加。峒內的社會秩序主要靠以上的習慣法來維持。這樣使黎族社會的發展有了自己的原始規范性,同時也賦予了它對外具有較強的防御能力。
黎族社會發展過程中,峒是一定地域內最高的社會政治組織,而“峒首”自然是一峒中最高的首領。一峒之峒首,是從各自然村的“村頭”中篩選出輩份最高、知識最豐富、家族影響力最大以及德高望重的人來擔任。在血緣關系較為單一的村、峒,凡雜居的外來居民一般不能當“村頭”、“峒首”,只有當外來居民占有相當的比例時才可以參加選舉“村頭”、“峒首”。峒首由男性擔任,負責處理峒內日常出現的一些事務,如主持紅白事、調解村民的民事糾紛和對外關系(包括調解、議和等)。在封建統治階級對黎族地區的統治過程中,封建統治政權從最初對峒組織的排斥,逐漸轉變為利用峒組織,最后使峒組織成為推動和加速黎族社會封建化進程的組織工具。黎族地區在封建化的過程中,峒首被封建官府委以重任,峒首由原來峒的首領逐步演變為地方政權人物,具有雙重身份,成了黎族社會的上層人物。峒首的職務都是世襲的,父死子繼,無子或子幼則由兄弟繼任。
“峒”作為黎族古代社會政治組織,逐漸被封建中央王朝所認識和利用,封建王朝對黎族由以征剿為主轉為征剿與招撫并施的治黎政策,從而開辟了黎族峒組織與封建統治制度相結合的道路。
隨著社會的發展,黎族地區峒的組織也在發展演變,一是峒內不同血緣集團增多了,二是峒內經濟、文化和宗教的相互影響,于是地域的社會聯系逐漸代替了原先血緣紐帶的關系,小峒慢慢地擴大為大峒,大峒隨著時間推移又慢慢地分化為若干個小峒。峒作為黎族社會中最早的政治組織,從最初表現為血緣關系逐漸發展到血緣和地緣相結合的社會組織,并逐漸強化了地緣關系、經濟關系在峒中的地位,從而使峒組織更好地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同峒兄弟”的意識,成為千百年來黎族人民緊密團結的思想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