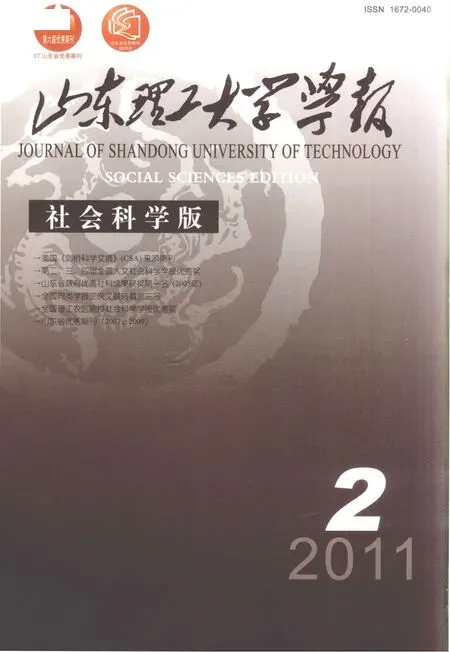大蒙古汗國早期自由工商業法律制度考析
綦 保 國
(西南政法大學 研究生院,重慶 400031)
大蒙古汗國早期自由工商業法律制度考析
綦 保 國
(西南政法大學 研究生院,重慶 400031)
在大蒙古汗國建國初期,基于蒙古社會早期財產權的普遍私有制,大蒙古汗國早期的工商業幾乎都是屬于私營性質。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持、鼓勵私營工商業經濟自由發展的政策與法令;這一時期的有些政策、法令甚至對整個元代的工商業經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大蒙古汗國;工商業;法律制度
早期的蒙古社會,人們很少擁有工商品或者奢侈品。太祖搶得富有的塔塔兒人的銀搖籃和織金床單被認為是“了不起的大事”。志費尼曾經描述:“他們當中大異密 (筆者注:部落首領)的標志是:他的馬蹬是鐵制的;從而人們可以想像他們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樣了。”[1]23盡管如此,一些小規模的家庭手工業是必需的,“他們的婦女制作各種東西:皮袍、長袍、鞋、裹腿和用皮做的各種東西。”[2]19甚至出現了專門的手工業工匠,太祖的“四狗”之一者勒篾的父親札兒赤兀臺老人就是一個“背著打鐵的風匣”到處游食的工匠。商業貿易也時有發生,最早的記載是一次奴隸實物貿易,太祖的十一世祖朵奔篾兒干一次打獵時,用鹿后腿換來了一個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的奴隸。[3]44在成吉思汗的部落統一戰爭時期,蒙古部落與回回商人之間的商業貿易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規模。據《元朝秘史》記載,成吉思被王罕驅迫至巴勒渚納海子時,“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兒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3]9
隨著成吉思汗時期的統一戰爭和對外征服戰爭,蒙古部落迅速崛起,大量的搶掠,使人們變得十分富有,各種工商業品及奢侈品的需求不斷增長,工商業經濟在這一時期有了顯著的增長。早在成吉思當初被擁立為乞顏部首領時,他就成立了專門的手工業部門,“古出古兒管修造車輛”。古出古兒制造了一種可以代步的鐵車,成吉思送給速別額臺一輛,“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并告訴他:“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到成吉思稱汗,建九腳白旗做皇帝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手工業工匠嚴重不足,成吉思下令:“于各官下百姓內,抽分著,……做千戶管者”,將古出古兒管理的手工業部門擴充到一千戶。[3]112在商業貿易方面,據《史集》記述:“由于蒙古部落是游牧民,遠離城市,他們十分珍視各種織物和墊子,關于同他們通商可以賺錢的消息便遠播開去了。”[4]258志費尼也指出:“成吉思汗統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環境,實現繁榮富強,道路安全,騷亂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圖之地,那怕遠在西極和東鄙,商人都向那里進發。”[1]90
由于早期蒙古社會財產權的普遍私有制,大蒙古國早期的工商業幾乎都是屬于私營的性質,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態度也非常積極、非常開放。事實上,大蒙古國早期出臺了一系列支持、鼓勵私營工商業經濟自由發展的政策與法令;這一時期的有些政策、法令甚至對整個元代的工商業經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發展手工業的主要政策與法令
(一)保護手工業勞動力、惟匠屠免的政策
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之后,蒙古社會對工商品及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連年征戰,兵器、戰車等戰爭器械的補給也日益重要。由于早期蒙古社會以游牧經濟為主,尚無精良的手工業生產,熟練的專業化的工匠十分稀缺,完全不能滿足此時的社會需要。因此,蒙古統治者很早就意識到保護手工業勞動力的重要意義,在對外的歷次征戰中,他們都采取了唯匠屠免的政策。
根據志費尼記載,他們將花剌子模的訛答剌城夷為平川,“那些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蒙古人把他們虜掠而去,或者在軍中服役,或者從事他們的手藝”。在此之后,拖雷征服馬魯,亦下令:“除了從百姓中挑選的四百名工匠,……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婦女和兒童,統統殺掉”。[1]99在中原戰場上,木華黎征東平時,“廣寧劉琰、懿州田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后。’除工匠優伶外 ,悉屠之 ”。[5]2930再有 ,“保州屠城 ,唯匠者免 ”。[6]55
(二)維護掠奪工匠的私有合法性,實施免稅免役政策
在對外征服戰爭中,蒙古將士像掠奪并占有財產一樣地掠奪并占有手工業工匠。國家不僅承認這種掠奪人口的合法性,而且還免除這一部分私屬人戶的國家賦役義務,以完全供其領主役使。
這一政策在元代的戶令中仍然有充分的反映。例如,至元八年 (1271)三月的《戶口條畫》就明確規定各投下貴族擁有的私屬人口不納國家“差發”,“諸附籍漏籍諸色人戶,如有官司明文分撥隸屬各位下戶數,曾經查對不納系官差發,別無經改者,仰依舊開除”。這里的諸色人戶,自然包括手工業工匠。關于“諸色人匠”的專門規定更為詳細,“諸投下壬子年元籍除差畸零無局分人匠,自備物料造作生活于各投下送納,或納錢物之人,依舊開除外”。“諸投下蒙古戶并寄留驅口人等習學匠人,隨路不曾附籍,每年自備物料或本投下五戶絲內關支物料造作諸物赴各投下送納者,充人匠除差”。[7]622由此可以看出,不僅在投下設置的局院里工作的手工業工匠是除差的,就是“畸零無局分人匠”,或者“寄留驅口人等習學匠人”,其制造的工業品“于各投下送納”的,都算作投下的私有人口,不承擔國家賦役。
(三)提高手工業者地位,鼓勵手工業造作
中原文化,士農工商,以工商為末業,歧視手工業工匠、抑制民間手工業發展。與之形成鮮明對照,蒙古統治者十分重視手工業的發展,鼓勵平民從事手工業造作。由于太祖十分看重能工巧匠,有技藝的匠人在當時處于一種特殊優越地位,甚至比儒者還見用于國家。史載:“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儒者耶律楚材也不得不自稱為“治天下匠”,可見當時匠者之重。
據《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繼承者》記載,窩闊臺的諸多事跡表明他十分重視民間手工業,并鼓勵平民從事手工業造作活動。例如:“一窮人,無以為生,亦不習任何生業。彼以鐵片銳其鋒為錐,安于木柄之上。……家財鮮少,而食口甚繁,故帶此錐來獻合罕。……彼予此不值一文之每一錐一巴里失。”就是這樣一個“游手好閑”之徒,造作的“錐”質量又極劣,原本“不值一文”,但窩闊臺卻給予重獎“每一錐一巴里失 (筆者注:貨幣單位)”。[8]110再如:“一外人攜來箭二支,跪于前。彼等詢其情況。彼言:‘我為矢人,負債七十巴里失。如能令國庫代償此數,我將每年納箭萬枝。’合罕言:‘此窮漢之困境使彼完全錯亂,有以如此眾多之箭而但得此數額之巴里失。可予彼現金一百巴里失,俾使彼有助于其事業。’……彼載巴里失于車而去。”[8]89在這一事例中,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當時的軍器并不是官方專造;二是窩闊臺明確鼓勵矢人造作,即“使矢人有助于其事業”。可見當時太宗窩闊臺對私營手工業的肯定態度和鼓勵傾向。
二、發展商業貿易的政策與法令
(一)開放的商業貿易政策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結束蒙古各部落之間的戰爭狀態,為商業貿易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大量的回回商人輾轉于西亞、中亞與蒙古各部落之間,他們追求商業利潤,“哪怕遠在西極和東鄙,商人都向那里進發”。成吉思對回回商人與蒙古部落之間的商業貿易持完全開放的態度,他甚至頒布一條札撤 (筆者注:法令):“凡進入他的國土內的商人,應一律發給憑照,而值得汗受納的貨物,應連同物主一起遣送給汗”。[1]125
成吉思汗本人不僅直接與回回商人經常進行商業貿易,而且他還委托回回商人代表自己從事商業貿易活動。這種商人與蒙古貴族聯手經營商業貿易的“合伙”關系,蒙古語稱之為“斡脫”(or-toq)。自大汗到諸王、公主、后妃都有自己的“斡脫”。那些回回商人得到被委托的“斡脫錢”,便獲得了“奉旨經商”的通行證。[9]48-50據《史集》記載,成吉思一次吩咐后妃、宗王們和每個異密[各 ]派兩、三名“斡脫”帶著金銀巴里失去花剌子模國去進行商業貿易,“[當時 ]集合起了四百五十個伊斯蘭教徒”。[4]259可見當時的“斡脫”貿易已經形成相當大的規模。
不惟如此,根據費志尼的記述,當時回回商人在蒙古汗國極受尊敬,并享受十分優厚的生活待遇,“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尊敬地看待穆斯林,為照顧他們的尊嚴和安適,替他們設立干凈的白氈帖”。[1]91回回商人的貴賓待遇,進一步表明了蒙古統治者對商業貿易的開放、鼓勵政策。
(二)建立與維護商業貿易交通設施的法令
對于陸路貿易來說,安全順暢、四通八達的商業貿易交通網絡是十分重要的。成吉思汗很早就希望達成這一事業,“有一天成吉思汗坐在阿勒臺山上,掃視了 [自己的 ]帳殿 (斡耳朵)、仆役和周圍的人們,說道:‘我的箭筒土 (豁兒赤)、衛隊多得像密林般地烏黑一片,我的妻妾、兒媳和女兒們像火一樣地閃耀著、發紅,……我要賜給他們多草的牧場放牧牲畜,下令從大路上和作為公路的大道上清除枯枝、垃圾和一切有害的東西,不得長起荊棘和有枯樹。’”之后,他又在給花剌子模國王——算端的外交國書中明確說道:“為了在兩國溝通協作一致的道路,要求 [我們拿出 ]高尚明達[的態度來 ],擔負起患難相助的義務,將 [兩國之間的 ]道路安全地維護好,避免發生險情,以使因頻繁的貿易往來而關系到世界福利的商人們得以安然通過。”[4]359
成吉思汗曾經命令:“為盡快得知國內發生的事變,必須設立常設的驛站。”驛站的設置不僅是為了保持政治通信的暢通,也為商業貿易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正如《世界征服者史》所描述的:“他們的領土日廣,重要事件時有發生,因此了解敵人的活動變得重要起來,而且把貨物從西方運到東方,或從遠東運到西方,也是必須的。為此,他們在國土上遍設驛站,給每所驛站的費用和供應作好安排,配給驛站一定數量的人和獸,以及食物、飲料等必需品。”[1]34驛站的設立不僅保障了道路交通的暢通,而且為客商的生活必需品的獲得提供了方便。
事實上,早在驛站設置之前,為了保障過往商人的商旅生活需要,成吉思汗的《大札撒》規定:“騎馬經過正在用餐的人旁邊,下馬后,不必得到允許便可以共同進餐,而且用餐主人也不得拒絕。”為了防止毒害過路商客,法律還規定:“禁止人們食用提供者不預先親自品嘗的食物,即便提供者是那顏 (筆者注:部落首領)、授受者是犯人也同樣處罰。”[10]85
(三)保護商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大蒙古汗國時期的 13世紀,如果說海上貿易最大的風險是自然災害,那么陸路貿易最大的危險在于盜匪的偷盜與搶掠。馬克斯·韋伯在研究中世紀歐洲陸路貿易時曾經記述:“老伽圖和發祿因為道路上常有賤人出沒,且多歹徒,所以告誡大家不要使用,又因為對于旅客亂敲竹杠,所以勸告大家不要在道路附近的任何旅店投宿。”[11]108商人的生命財產經常受到威脅以及陸路運輸費用的高昂一直是制約中世紀陸路貿易的重要因素,也是中世紀海上貿易一直優于陸路貿易的重要原因。
蒙古部落原本生活在蒙古草原,是典型的內陸經濟,商業貿易以陸路為主,而且他們視搶劫為豪勇與高尚之舉,搶掠成風,這種狀況極大地阻礙了商業貿易的發展。顯然,這種狀況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因為在他統一蒙古草原之后,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史者評論:“當時成吉思汗已經將叛賊、歹徒從[哈刺 ]契丹和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區上肅清了。他在路上設置了崗哨,使得商人能平安通過”;“成吉思汗統治后期,……道路安全,騷亂止息”。[4]359
事實上,為了制止搶劫與盜竊,成吉思汗制定了處罰極重的法律。據《黑韃事略》記載:“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12]69犯搶劫、盜竊罪者,不僅處以極刑——死刑,沒收其家屬、財產,而且主奴“連坐”,足見其防范之嚴、處罰之重。
對于殺人者的處罰,成吉思汗也制定了專門的《大札撒》,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規定保護回回商人的生命甚于保護中原漢人。《大札撒》規定:“殺人者若支付贖罪金,即可免除 (死刑),殺回教徒者支付四十金巴里失;殺中原人者支付一頭牡驢。”[10]87這樣的規定,在《史集》中也有記載:“成吉思汗的偉大札撒在實質上也與此相符:它規定一個木速蠻 (筆者注:回教徒)的血的價值為四十個金巴里失,而一個漢人僅值一頭驢。”[4]359
不惟如此,蒙古統治者的法律還規定:“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回回商人被搶奪盜竊,可以將損失轉嫁給當地百姓,以致“前后積累,動以萬計……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9]48-50有的回回商人,甚至或因經營不善,詐稱被劫。《黑韃事略》徐霆疏:“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于州、縣民戶。”[12]79
上述保護商人的規定,甚至影響到元初賽典赤在云南的治理。至元十二年,賽典赤為云南行省左丞,當時“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為行者病”,賽典赤命令:“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及之”,[5]3456從而為云南的商旅往來掃清了障礙。
蒙古統治者盡管樂于從事戰爭搶掠,但對一般商旅的生命財產安全卻提供了周到的法律保護。事實上,殺害與搶掠他們的“斡脫“商人不僅會引起他們的憤怒,而且會帶來可怕的戰爭。正是因為花剌子模訛答剌城的“海兒汗”殺害并掠奪了成吉思組織的四百五十個“斡脫”商隊,成吉思汗“獨自登上一個山頭,脫去帽子,以臉朝地,祈禱了三天三夜”,并策劃組織了中世紀最大的商業復仇戰爭,將花剌子模從地球上抹去了。
(四)以優惠價格采購商人貨物的政策
蒙古統治者為鼓勵商業貿易,經常以優惠的價格購買商人的貨物。成吉思汗曾經下令以每匹“咱兒巴甫埸”(織金絲綢)給一個金巴里失,每匹“客兒巴思”(素棉布)或“曾答納赤”(彩色印花棉布)給一個銀巴里失的價格購買馬合木·花刺子迷、阿里·火者·不花里及玉速甫·堅客·訛答剌里三個回回商人的商品,并邀請他們作為自己的“斡脫”和使者出使花剌子模。
窩闊臺汗的慷慨、寬仁之名更是遍及世界。他曾經命令:“彼等之貨物,無論好壞,全部收買,付予全部所值”;“不論數額如何,均可增百分之十付與”。窩闊臺汗的大方優惠甚至引起了廷臣的不滿,一日,廷臣因貨物之價已超過其實有之值,請不須增付百分之十。窩闊臺說:“商人與國庫交易,為圖利耳!彼等確曾以費付爾等必者赤(筆者注:官吏)。我所清償者,乃彼等對爾等之債欠,免使彼等蒙受損失而離我之前耳!”[8]111由此可見蒙古統治者對商人的厚愛。
正是因為上述政策、法令及保障措施,各路商客在廣闊的蒙古草原上自由地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并獲取了豐厚的商業利潤。志費尼描繪說:“商人、投機者、尋求一官半職的人,來自世界各地,都達到他們的目標和目的后歸去,他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滿足,而且所得倍于所求。多少窮人富裕起來,多少貧民發財變富,每個微不足道的人都變成顯要人物。”[1]93
[1][伊朗 ]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 [M].何高濟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2][英 ]道森.出使蒙古記 [M].呂浦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3]鮑思陶點校.元朝秘史[M].濟南:齊魯書社,2005.
[4][波斯 ]拉施特.史集 (第一卷,第二分冊)[M].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5]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
[6]劉因.靜修先生文集[M].四庫全書本.
[7]元典章[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
[8][波斯 ]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繼承者 [M].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9]翁獨健.斡脫雜考[J].燕京學報,1941,(29).
[10]吳海航.元代法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11][德]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 [M].姚曾廙譯,韋森校訂.上海:三聯書店,2006.
[12]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 [M].王國維箋證本,文殿閣書莊,民國 25年版.
DF09
A
1672-0040(2011)02-0044-04
2011-01-07
綦保國 (1974—),男,湖南衡陽人,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仙桃職業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副院長,主要從事法律史研究。
(責任編輯 鄭 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