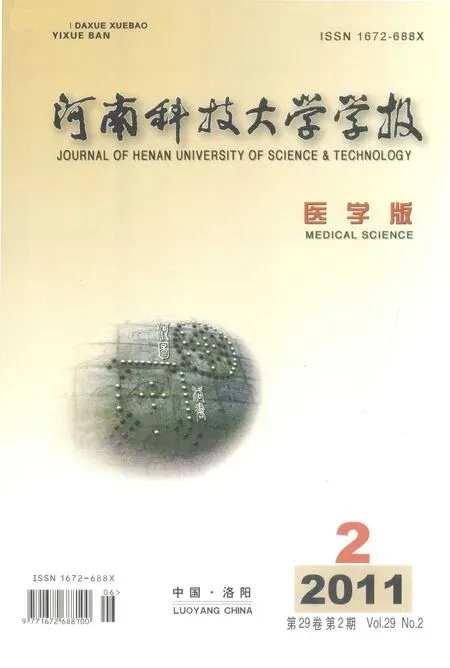強化轉化醫學理念在燒傷醫學研究中的應用
雷萬軍,龐新躍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醫學迅速發展并取得顯著成就,不僅醫學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而且衛生服務系統和醫療保障制度也相繼建立并發展完善。醫學研究遠比任何一種生命科學研究更為復雜,如果沒有臨床醫生的努力,沒有臨床醫學的突破,任何重大疾病研究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突破。如何用臨床問題指導基礎醫學研究,并把基礎醫學研究的成果轉化應用到臨床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上去是科學家和臨床醫師長期的追求。
1 轉化醫學的概念及提出背景
1992 年美國《科學》雜志首次提出從實驗室到臨床(bench to bedside,B2B)的概念,1996 年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第一次出現“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一詞[1],2003 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正式提出“轉化研究”這一概念,轉化醫學又稱“轉模”或“轉譯”醫學,其有關研究通常稱為“轉化研究”或“轉化科學”,國內習慣稱“轉化醫學”。轉化醫學意義及價值已引起全球范圍的重視,各國開始制定實施各種計劃,鼓勵發展轉化醫學。
2006 年NIH 設置了臨床與轉化醫學基金(CTAS),旨在改善國家的生物醫學研究狀況,加速實驗室發現用于患者治療的過程,有效縮短疾病治療手段的開發時間,鼓勵相關單位參與臨床研究,對臨床和轉化研究人員實施培訓。美國預計到2012年,NIH 設置的臨床與轉化科學基金資助機構可達60 家,資助基金5 億美元。
NIH 21 世紀“工作路圖”包括3 個核心領域:①探索并重新認識新的科研思路和途徑;②培養和建立一個新的為未來醫學發展的研究團隊;③重新設計臨床研究事業。法國衛生部門啟動臨床研究項目,英國健康研究戰略協調辦公室(OSCHR)確定轉化醫學研究戰略。為了促進轉化醫學的發展,目前世界上各主要的核心期刊都開辟了轉化醫學專欄,同時還出版了《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Translational Medicine》和《Translational Research》等3 本國際性專業雜志。
轉化醫學的背景源于臨床實踐滯后于科學發現和技術研究,進入21 世紀后,醫學界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以腫瘤為例,1971 年至今美國用于腫瘤防治方面的研究經費多達2 000 億美元,但卻只收獲了156 萬篇與腫瘤相關的研究論文,其中80%的文章研究使用的是小鼠、果蠅和線蟲。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并沒能真正推動腫瘤防治的進步,癌癥導致的死亡率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2 轉化醫學在我國的發展情況
轉化醫學在我國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2010年12 月18 ~19 日由中華醫學會、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與醫學學部聯合提議召開的“加快中國的醫學模式轉換,促進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為主題的第S13 次香山科學會議上,50 余位多學科、跨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臨床與基礎研究結合的基礎研究向臨床醫學轉化等中心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我國燒傷學科專家柴家科教授出席會議并就燒傷醫學的問題做了重要的發言。
中科院院士、衛生部長陳竺教授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作了題為《推動轉化醫學發展,應對人民健康挑戰》的主題評述報告,陳竺說,轉化醫學的目的是為了打破基礎醫學與藥物開發和臨床醫學之間固有的屏障,轉化醫學的核心就是在從事基礎科學發現的研究者與了解病人實際需求的醫生之間建立起有效聯系。在我國轉化醫學已成為國家在生物醫學領域里一個重大的政策。
轉化醫學是一個致力于克服基礎研究與臨床和公共衛生應用嚴重失衡的醫學發展的新模式。目前我國還沒有較大規模的專門轉化醫學中心,但多年來,不少大學、醫院科研機構和生物醫藥公司之間開展的合作,應歸于轉化醫學。國內已經起步或開展轉化醫學方面工作的主要有復旦大學、廈門大學、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上海交大、中山大學等,初步建立了相應的臨床轉化網絡和配套體系等。
轉化醫學事實上強調的是理念的轉變,轉化醫學研究主張打破以往研究課題單一學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一個學科要想發展壯大,吸收不同領域的技術合作是必經之路,并由此來解決那些原本界限模糊的“結合部”問題。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包括客觀和微觀、生理和病理、預防和治療、人文和社會等因素[2]。
3 目前醫學研究主要存在的問題
轉化醫學就是從實驗臺到病床,再從病床到實驗臺的連續過程,主要包括:①將基礎醫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應用于臨床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中;②針對來自臨床醫師的觀點和假設,設計基礎研究實驗并加以檢測和驗證,強調是實驗臺到臨床間的相互連接,即雙通道效應。也就是基礎研究人員給臨床醫師提供用于疾病醫療的新工具,將基礎研究的成果轉化為能夠為臨床所使用的技術;另一方面,臨床研究者對疾病的特征進行觀察,提供反饋意見來促進基礎研究。
目前,臨床醫師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醫生技術水平單一化,缺乏多學科知識以及專科劃分過細等,臨床上遇到的困難,不了解如何利用現有的基礎研究成果去解決,同時也缺乏引導基礎研究為臨床服務的理念。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基礎和臨床研究涉及的范圍太廣,分類太細,所以基礎研究者缺乏同時也難有太多的臨床知識,臨床醫師鑒于其工作性質則對基礎研究的了解,尤其是一些新的相關基礎研究也同樣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基礎研究人員和臨床醫師想要涉足對方領域需要構建復雜的基礎和臨床醫學知識。另外,即便在學科門類齊全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內,即便有文、理、工、醫及相關學科群的優勢,其相互間的融合也有在傳統上的屏障和相互銜接的缺陷,尤其在醫學與非醫學各專業學科的結合上。其次,不少富有經驗和事業心的醫師也能提出不少甚至很有前景的課題和項目,但缺乏經費支持,或涉及多學科以及技術交叉性平臺而知難而退。
臨床醫師不僅僅基于豐富扎實的臨床實踐,而應該從自己的優勢和比較優勢尋找合適的切入點,與同行和其他學科更多地交流合作,不斷開闊自己的視野,尋求新思路和研究新領域。同時應處理好課題權益分割,實驗路徑選優,知識產權保護,互為信任,資源共享,成果轉化,以及成果發表,專利、成果等利益沖突問題[3],因為這些都嚴重影響著轉化醫學領域的發展與合作,會導致一個非常有前途和潛力的項目得不到相互關注與配合,導致課題半途而廢。
4 推動轉化醫學發展的幾個重要方面
4.1 樹立團隊科學的理念一些重大疾病的研究復雜性已經遠遠超越了人們的預料,臨床的問題最終已經不能由單一專業的科學家來完成,以癌癥相關研究為例,需要不同技能和學科背景的專業人員緊密合作才有可能徹底揭示環境、生活方式、遺傳因子、分子機制對癌癥發生的相互作用。
4.2 搭建學科交叉的開放式研究平臺把實驗室發現的有意義結果轉化為能提供臨床實際應用的手段,需要有強的穩定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設施和平臺,對研究項目的協商和跟蹤也要有多學科介入的機制,同時要建立基于平臺建設的標準化數據收集系統和可以把多方緊密聯系起來的信息網絡的框架。
4.3 培養新一代具有轉化醫學理念和能力的科學家一方面增強基礎研究人員對臨床知識的重視和尊重,另一方面,提供臨床專家進入實驗基地探索基礎研究的機會,使雙方均能不斷熟悉對方的語言。
5 燒傷醫學研究中轉化醫學理念的運用
在第S13 次香山科學會議上,柴家科教授談到,我國燒傷醫學研究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需要針對具體的臨床難題,與理、工、醫各相關學科的研究人員形成更廣泛的交叉融合。轉化醫學的理念必須時刻體現在專業發展中,燒傷學科像是一項系統工程,挽救生命——恢復形態——重建功能——走向社會就是這項工程的鏈條,這其中有大量問題需要研究、實踐、再研究,只是救了命,根本沒有完成治療過程。
5.1 康復醫學是一門涉及多個專業的綜合性應用學科隨著大面積深度燒傷臨床治愈率的提高,燒傷康復治療日益顯得突出和重要,這一點雖然大家具有共識,但實際效果上就顯得非常之薄弱。①燒傷臨床醫師缺乏或缺少比較扎實的康復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技術;②重治療輕康復,治療與康復分離的現象很普遍;③缺乏燒傷康復規范指南,就目前發表有限的康復論文來看,其資料零散,更缺乏系統性追蹤資料,尤其缺乏與相關專業人員的交流與合作,基礎研究薄弱。燒傷康復醫學應加強與生物醫學工程技術人員、計算機智能技術人員等進行密切的跨學科合作來推動和提升我國燒傷康復研究的水平。
5.2 中西醫結合問題中西醫結合開拓和發展應是我國特色的燒傷治療技術,以現代科學技術的新進展來深入探討祖國傳統醫學之寶,不僅是繼承和發展的問題,同時也是豐富現代西醫的實踐和理論問題。然而真正意義上的中西醫結合研究存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缺乏或缺少專業技術人員從事真正的中西醫結合的研究,任意夸大或否定其療效的現象較為突出。中西醫結合原創思維的內涵挖掘不夠,特色淡化,基礎與臨床應用研究滯后,適合于中西醫結合自身特點的研究與評價方法與標準體系尚未建立。
5.3 突發事件與災害也是對燒傷科學的一個挑戰以化學事故為例,化學事故影響人的健康有多種途徑,主要包括:爆炸效應、火災效應、化學中毒效應。化學物質可通過皮膚、眼睛、呼吸道、消化道進入體內,對不同的化學品,這些途徑有不同的吸收率,吸收率要受接觸的濃度、時間、溫度、濕度、氣壓、風向以及人員的年齡和機體狀況影響。對機體內部來講,化學中毒效應與化學品的急性毒性和生物有效劑量有關,損傷可以是局部的(即皮膚、眼睛、呼吸道等)或全身的,有些反應可能即刻出現,有些效應可能是遲發的,有些是進行性加重,致畸致癌會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后出現。未知的化學新品越來越多,其復雜的效應給燒傷早期急救帶來了嚴重的考驗,因此,沒有相關專業科學技術人員的介入,救治不力或延誤治療等是難以避免的。
5.4 組織工程組織工程的概念起始于20 年前,組織工程發展到今天,離不開各個學科領域的精誠合作,這其中主要包括臨床醫學專家,材料和機械科學、生物力學方向的工程師、分子生物學家,生物數學和計算機專家等。組織工程研究的核心是種子細胞、生物材料及組織工程化組織構建,組織工程的研究是新世紀富有前景的項目,皮膚、骨及軟骨的臨床應用已顯示出可喜的臨床療效,腦損傷、脊柱損傷、糖尿病的早期細胞治療,也都取得了可喜的療效,組織工程化皮膚若能得到完善和發展,對燒傷治療來講將是重大突破,因此這方面的參與式介入有著廣闊的前景。
我省地處中原,人口眾多,燒傷布點較均勻較普遍,病例數較多,臨床研究資源較豐富,從事專業人員較多,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隨著新世紀醫學科學技術水平的快速發展,如何進一步提高我省燒傷外科學專業的臨床救治與科研水平,充分發揮多學科知識和技術的交叉滲透,促進基礎研究成果轉化成醫療實踐,力爭在國內燒傷領域做出有影響的高水平質量的具有創新性的成果,有待深入探討和努力。
[1] James Geraghty. 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J].The Lancet,1996,348(9025):422.
[2] Horig H,Marincola E,Marineola FM.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anslational research[J]. Nat Med,2005,11:705-708.
[3] Joiner KA. The not-for-profit form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Kerr revisited?[J].J Transl Med,200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