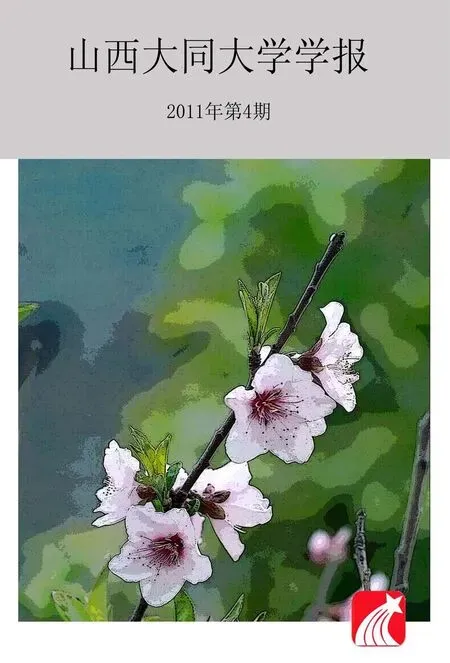以天人關系看孟子“仁政”的烏托邦
劉華軍
(1.南京大學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3;2.中共淮安市委黨校,江蘇 淮安 223000)
以天人關系看孟子“仁政”的烏托邦
劉華軍1,2
(1.南京大學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3;2.中共淮安市委黨校,江蘇 淮安 223000)
不同于孔子,“仁”在孟子學說中被降格。“仁”乃人心,由“心”推出“性”,由“性”乃事天,這是孟子的天人關系。孟子又以人性為出發點,認為“仁政”實乃“心政”。由于孟子對于天人關系次序的理解失當,即便是主張土地、稅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上與當時的現實相距太遠,孟子的“仁政”也只能是他心中的烏托邦。
孟子;天人關系;心路歷程;烏托邦
研究先秦儒家思想有兩種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學之本體論和方法論來對照,同者取之,異者舍之;一是為上個世紀初中國許多哲學家提倡的以儒家之方法研究儒家之思想。研究孟子之思想當然不能局限于自身,也決不能簡單地以西方哲學為準繩。
一、孟子的天人關系
孟子在《盡心章句上》中有兩段議論:一是“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二是“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研究孟子思想中的天人關系不外乎以這兩段論述為材料。因此,對這兩段論述的正確理解就成了能否確切反映孟子真正意圖的關鍵。
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對第一段話的理解是這樣的:“性在于心,盡其心則能知性;人之性乃受於天者,實亦即天之本質,故知性則亦知天。天性一貫,性不外心”。[1](P173)他在這里將孟子的“知其性,則知天”理解為“人之性乃受于天者,實亦即天之本質”,這就將孟子“由性知天”轉變成“由天知性”。這種轉變合理與否尚不去理論,但卻很難找到令人信服依據。
張岱年將中國古代哲學中所謂“天人合一”思想一分為二來解釋,一為天人相通,二為天人相類。他認為,孟子的觀點應屬于“天人相通”的范疇。他對“天人相通”的解釋是這樣的:“天人相通的學說,認為天之根本性德,即含于人之心之中;天道于人道,使一以貫之。宇宙本根,乃人倫道德之根源;人倫道德,乃宇宙本根之流行發現。本根有道德的意義,而道德亦有宇宙的意義。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即在認知心性與天相通。人是稟受天之性德以為其根本性德的。此種天人相通的見解之最初倡導者,是孟子。”[1](P173)孟子思想當屬于“天人相通”。對于“天人相通”一說,難說其是非。可是兩千多年前的孟子是否和今天的人們一樣地理解“天人合一”,或者他的理解是否能夠達到如此高的程度,頗值得懷疑。孟子贊成人性與天性相通,但是孟子的出發點是人性而不是天性,它是用人性來得出天性。在他的理論進路中,人性是天性的基礎,若對此沒有深刻地把握,理解孟子思想中的天人關系就會偏向,對于孟子其他思想的理解就會在無味的思辨中糾纏,理不清頭緒。諸如孟子關于人性的界定,在歷史上爭論紛紜,最終不得不使后人對這樣的界定和爭論產生質疑。也許這樣的界定本身價值并不大,然而以人性為基礎的推論的穩定性也將會受到威脅。
馮友蘭亦說:“孟子之所謂天,有時似指主宰之天,……有時似指運命之天,……有時則指義理之天。……性之所以善,正因為性乃‘天之所與我者’,人之所得于天者,此性善說之形上學的根據也。”[2](P163~165)可以看出,他和張岱年并沒有甚么區別,同樣反推出孟子的出發點是天,“天人關系”乃居人性論之上。可是,他又說:“‘萬物皆備于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頗有神秘主義之傾向’。”[2](P163~165)這里的問題是對神秘主義的理解。馮友蘭對這種神秘主義作出的解釋是:“專指一種哲學承認有所謂“萬物一體”之境界。在此境界中,個人與“全”(宇宙之全)合而為一,所謂人我內外之分,具已不存”。[2](P163~165)很顯然,馮友蘭將孟子思想里的“天人關系”理解為“天人合一”。馮先生還將這種神秘主義和佛教的觀點結合起來,為能夠得出孟子的觀點是“天人合一”和“萬物為一體”尋找理由,因為“蓋盡恕與仁皆注重在取消人我之界限,人我之界既消”,所以結果一定是“我與萬物為一體”。其實,馮先生也對他自己這種解釋有所懷疑,一方面,“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另一方面,“此解釋果合孟子之本意否不可知”,也只因“宋儒之哲學皆推衍此意”罷了。[2](P163~165)
胡適沒有講孟子主張的“天人關系”是什么,但他卻從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看出,孟子強調的是個人的位置。這種個人的位置到底是指個人在自然之中的位置,還是個人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胡適沒說,孟子也沒說。孟子總是強調“王”要與民同樂,孟子的“仁政”可以稱為是“民政”,孟子似乎更注重的是人在社會中的位置。[1](P215)若從這一意義來看,同樣可以說明孟子的天人關系首先在人而不是天。
二、孟子“仁政”的心路歷程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這句話可謂孟子思想之真實寫照。“心”是孟子考慮問題的基礎,也是孟子思想的前提,“政”才是孟子要解決的問題,“政”應該是孟子之“心”的歸宿。人之“心”當然可分為各種各樣的“心”,孟子之“心”是“不忍人之心”。“不忍人”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同情和憐憫,“不忍人之心”就是指人的同情之心和憐憫之心。同情心構成孟子立論的基礎,這有點像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的同情心和憐憫之心,它同樣也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基礎。
人為什么有“不忍人之心”呢?孟子認為皆由“怵惕惻隱之心”導出,而“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并且它“非所以內交與孺子父母”,“非所以譽于鄉當朋友”,“非所以惡其聲”,(《公孫丑上》)“非外鑠于內,我固有之也”。(《告子上》)既然“怵惕惻隱之心”非證即知,不言即明,同樣“不忍人之心”也不須證明而人皆有之。所以在孟子看來,同情心是與生俱來的,是不言而喻的。
在此基礎上,孟子進一步推導出“四端”。“四端”即所謂仁、義、禮、智。由“惻隱之心”得出“仁”,由“羞惡之心”得出“義”,由“辭讓之心”得出“禮”,由“是非之心”得出“智”,由此“四端”而達到“仁政”。仁、義、禮、智四端是實施“仁政”的必要條件,君王若能夠很好地運用此“四端”,則能達到所謂“仁政”,即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孟子在這里僅僅將“仁”限定為同情心、“不忍人之心”和“惻隱之心”,這種同情之心來自于執政者,所以“仁政”的實施關鍵在于執政者擁有同情心和愛民之心。與此同時,孟子也給“君王”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必須加強自身的修養,因為“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上》)
在此基礎上孟子又提出“與民同樂”的觀點,“施仁政與民”。“仁政”的實質就是“民政”,在《孟子》一書的《梁惠王篇》以及《公孫丑篇》的部分章節大都是在談論所謂“民政”。孟子認為,只要統治者能夠做到“省刑罰,薄稅斂,深根易耨”,(《梁惠王上》)“是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公孫丑上》)使“民”能夠心悅誠服,則可“無敵于天下”,進而能夠“王霸”于天下。這正好和孟子生活的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的現實緊密相連,能夠滿足當時各諸侯國君王們的心理欲求。
孟子言性善,這是他政治哲學之基礎。孟子說人性是善的,反對性不善論,也反對性亦善亦不善論。在孟子看來,人只有性本善,才能有“惻隱之心”,才能有“不忍人之心”。當然,如果性本非善,那么“惻隱之心”和“不忍人之心”則無從而來。如果沒有“不忍人之心”,又何談其“不忍人之政”,也就沒有什么“仁政”了。到此,孟子之整個思想脈絡已很清晰。
三、理想主義的“仁政”
對于孔子來說,“仁”是天和人之間架起的橋梁,“仁”普遍存在于每個人的生命之中。孟子與孔子不同,孟子將天與性相通,由性而事天。“天存孟子的人性系統之中,是人性的終極根源,亦是宇宙大化善的流行”。[4](P91)可是孟子更向內收,由心的作用驗證性人性皆善,心性合一,將天的善機轉向人的內心加以證成。孟子的“仁”發端于心,甚至將“仁”歸并為心之一端,明顯地把仁的內涵縮小了許多。由這里也可推知,仁學與孔子儒學有實質性區別,這也可能為后世心性學術(尤為宋明理學)的肇始。
孟子講“仁者,人心”,但是“仁”其實非此意。孟子在這里有一個誤區,這個誤區可以用孟子的解釋作為例證。孟子說:“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孫丑上》)大多數文本對這句話的注釋是:仁是天(賦予人的)最尊貴的爵位,是人最安定的住所。而《孟子注疏》曰:“仁則得之于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這種解釋頗為中肯,仁之實質含義亦可窺見一斑。尊、爵都是古人祭祀時用的器皿,“安”意是靜,“宅”意指所托,并不能簡單將“安宅”理解為住所,這很難把握“仁”的原意。古人是想通過祭祀活動建立與天的溝通途徑,尋找人所能達到的寄托,“仁”實乃這種意愿的表達。這確是孔子的“仁”之意。孟子在這里說了,但卻沒有徹底地貫徹這種精神,在現實中孟子將“仁”用偏了,于是“心政”成了孟子政治學說的核心。一方面,王之所以可以王,必須要有“心”,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乃為仁心,由王的表率作用所體現,同時尚需“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媷”。另一方面,民之有恒心,則王可以王;民之恒心由民之恒產所決定,所以孟子主張推行“井田制度”。
在孟子政治思想的論述中存在著明顯的邏輯上的不合理。我們說“仁”的基礎是“禮”,《孟子》中也有關于“禮”之論述,而仁學想建立的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的人倫關系,其核心是要建立長幼尊卑上下等級關系。孟子將“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歸咎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楊墨之言的問題也恰恰是在于模糊了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尊卑關系。“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滕文公下》)可是孟子所主張的“仁政”卻要求統治者能夠做到“與民同樂”,凡事以民眾的意愿為標準,“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梁惠王下》)在今天看來,實施“仁政于民”的必要條件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如果在等級森嚴的狀況下,要想施仁政于民,與民同樂,可能性非常小,現實中也不會有什么可操作性,孟子的理想國也只能成為理想中的烏托邦。由于孟子的理想和當時的現實相差太遠,因此他只能退居山野,著書立說,聊以自慰。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當時之始,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眾連橫,一共發危險,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推而與萬張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5]即使孟子也設計了許多具體的實施細則,這些細則有些在今天看來也有一定的意義,然而這些并不是當時的諸侯君王所需要的,因為他們需要的是“霸道”,而不是孟子所謂的“王道”。
[1]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1.
[3]胡 適.中國哲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翁志宗.論語、孟子政治論述之研究[M].臺北: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出版社,2002.
[5](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74.
〔編輯 趙立人〕
U topia by M encius t o S ee‘B enevolent G overnance’by R elationship between M an and M ature
L IU Hua-jun1,2
(1.Departmentof P 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93;2.MunicipalPartySchoolofCPC,Huaian Jiangsu,223000)
D ifferent from Confucius’,Benevolence in Mencius theories was degradation.Benevolence is a kind of mental constitution by which nature ofman can be deduced.To nourish one's nature is the way to serve Heaven.Taking human nature as the reasoning starting point,Mencius asserted‘benevolent governance’,is‘heart governance’.Though Mencius claim ed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 such as land and tax policies,only that is utopia because his understan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wrong,and because his republic contrast sharply with his reality.
Mencius;relationship betweenman and nature;mentality;utopia
B222.5
A
1674-0882(2011)04-0011-03
2011-06-30
劉華軍(1971-),男,江蘇連云港人,在讀博士生,講師,研究方向:科學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