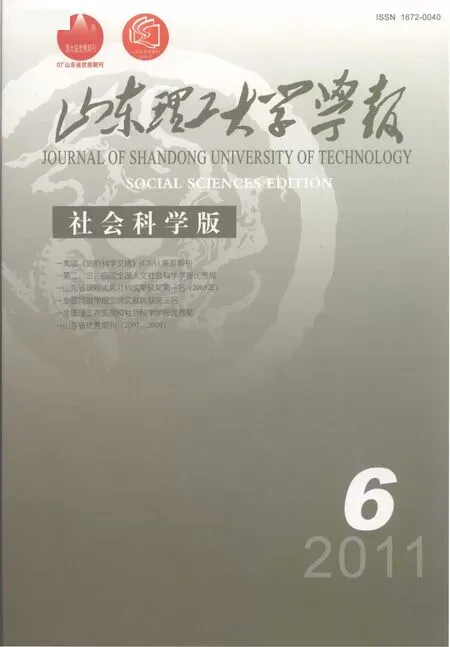從邊緣到中心:第六代導演的皈依之路
賈夢,張玉霞
(1.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北京100024;2.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從邊緣到中心:第六代導演的皈依之路
賈夢1,張玉霞2
(1.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北京100024;2.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第六代導演剛登上中國電影舞臺時,在體制內很難獲得拍攝影片的機會,為了進行拍片實踐,他們不得不走過一段長時間的“地下時期”,在這段時期內,他們的影片大都具有一種邊緣化的色彩。待經歷了一段“地下時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聲譽后,他們又思考如何獲得體制的認可,研究觀眾的接受心理,拍攝觀眾樂于接受的影片,讓更多的觀眾來欣賞、認可他們的電影。由此,從邊緣到中心,第六代導演走了一條艱難的皈依之路。
第六代導演;邊緣;中心;電影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影壇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一批風格獨特的年輕導演繞開中國電影的既定規則,另辟蹊徑,自成佳境。學術界給予了不少關注,對這一電影現象,目前學術界大體有兩種意見,黃式憲、鄭洞天、戴錦華、林少雄等人稱其為“第六代”導演,倪震、尹鴻、賈磊磊等人稱其為“新生代”導演。筆者在這里也采用“第六代導演”這個稱謂。一般認為,第六代導演是以北京電影學院85、87屆學生為主體,包括中央戲劇學院部分畢業生在內的電影導演群體,有人認為也應該把一些拍攝紀錄片的創作者歸入第六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群體包含的范圍也在逐漸增大,如北京電影學院93級的賈樟柯也被劃入這個群體。
張元的《媽媽》拉開了第六代導演的創作序幕,自此出現了大量的“第六代”影片,如張元的《北京雜種》,胡雪楊的《留守女士》,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婁燁的《蘇州河》、《西施眼》,管虎的《頭發亂了》,路學長的《長大成人》、《非常夏日》,張揚的《過年回家》、《洗澡》,賈樟柯的《小武》、《任逍遙》、《站臺》、《世界》、《三峽好人》,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扁擔·姑娘》、《極度寒冷》、《十七歲的單車》,金琛的《網絡時代的愛情》,施潤玖的《美麗新世界》,王全安的《月蝕》、《圖雅的婚事》,等等。
一、邊緣化書寫
第六代導演顯然沒有第五代導演那樣幸運。他們登上電影創作舞臺時大部分人都沒有享受到體制的便利,這個特殊群體中的很多人都沒有獲得進入電影廠的機會,有的即使是進入電影制片廠,由于第五代導演創作的繁盛,他們也很難獲得獨立拍片的機會;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在政治、社會領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國家對于電影事業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娛樂方式的多元化又分流了大批的電影觀眾。第六代導演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拍攝影片的問題。因為沒有名氣和經驗的他們獲得電影制片廠投資拍片的機會很小,國家也不可能拿出錢資助。最終,他們只能采取一種別樣的方式:獨立制片或者稱為地下制片。“地下制片”是一個非常形象的描述。早期,第六代導演拍攝的大部分影片都采用這種方式。可以肯定的是,通過這種“地下活動”,第六代導演得以進行拍片實踐,并且通過國際影展,在國際上獲得了一定的聲譽。如張元的《媽媽》獲得了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評委會獎和公眾獎、柏林電影節最佳評論獎、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影評人大獎。這次獲獎對于第六代導演來說是一個莫大的鼓舞,對第六代導演的創作實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類似于第五代導演早期的境遇,他們也開始了“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創作之旅,同時他們由于經濟原因而產生的對于西方文化的認同感也在發生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不僅認同西方國家的文化,而且對于西方人所認同的東方文化也持贊同態度)。中國的電影觀眾也逐漸開始關注第六代導演。
二、邊緣的表現
(一)邊緣人物書寫邊緣鏡像
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具有一種“邊緣化”傾向,這種邊緣化特征主要體現在影片內容上。他們的電影一般是以城鎮為背景的,但在影片中出現的又不是人們所熟悉的高樓大廈、便利的交通、繁華的商場、舒適的住所,而是人們很少注意的雜亂的建筑工地、拆遷中的樓房、骯臟的旅館等。影片中的人物角色,也選擇了小偷、妓女、搖滾歌手、智障兒童等,多為以前電影中所不常見的生存于城市邊緣的人物形象。這些鏡像的出現與第六代導演的特殊身份有著密切關系。第六代導演登上中國電影舞臺之初,是地地道道的“邊緣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沒有進入國家電影體制,即使是少數進入體制之內的導演,也很難獲得獨立拍片的機會,就更不用說獲得國家的資金了。作為導演群體中的邊緣角色,第六代導演一旦獲得拍片的機會,就必然會在影片中表現出自己的獨特的情感與見解,用一種邊緣的視角來表現邊緣人物、邊緣場景及特殊情感。影片中這些邊緣人物正是第六代導演用以表達自我的一些特殊符號,“第六代中很大一部分人自己處在社會的邊緣,在他們的作品中透射了他們自身的生命體驗”。[1]張元《媽媽》中的智障兒童,《小武》中的妓女、小偷,《北京雜種》中的地下搖滾樂手,這些人物都處在社會的邊緣,很少有人來關注他們。第六代導演卻將這些人物角色作為影片敘事的中心,并且在表現這些人物時,大都展現了他們生存中不幸的一面,這也正是第六代導演邊緣生存狀態的再現。
(二)邊緣沖擊中心的張力
第六代導演也把表現邊緣人物和邊緣場景的創作方法作為突破第五代導演的一種方式。第六代導演曾直截了當地宣稱:“中國電影需要一批新的電影制作者”,[2]26這批新的電影制作者當然指的就是他們自己。作為享受著“特殊權力”的人群,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占有著常人難以獲得的資源: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這個中國唯一的電影專業院校。他們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也是基于這樣一種期待:將來成為中國新一代的電影導演。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又不是邊緣角色,而是地道的中心人物,至少可以說是中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作為中心的邊緣部分,第六代導演面臨的問題是在這個團體中很少有發言權,很難獲得拍電影的機會,只能采取獨立制片的形式來進行影片拍攝。張元籌集到了資金,拍攝完成了《媽媽》,賈樟柯、王小帥等人同樣也是用這種方式開始了自己的創作道路。《媽媽》表現的是被人遺棄的婦女和她的智障兒子的故事;《小武》描寫的是關于小偷小武的愛情、親情和友情的故事;《北京雜種》講述的是地下搖滾歌手的生活狀態。第六代導演拋棄宏大的歷史結構,將關注點轉向日常人物,是對第五代導演宏大敘事的一種反叛。第六代導演采取這種方式表現自己的創作風格,來突破第五代導演架設在他們面前的障礙。作為對中心的沖擊,第六代導演早期的創作實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國際上頻繁獲獎,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不幸的是,早期很多獲得國際大獎的影片在國內無法獲得公映的機會。可以說第六代早期的電影是以犧牲體制認可的代價來換取生存的空間。
三、關于邊緣的解讀
(一)紀實的邊緣,而非真實的邊緣
很多學者稱第六代導演的拍攝手法為紀實主義手法。這與第六代導演經常運用的長鏡頭的處理方式有很大的關系。長鏡頭的紀實性造就了一種真實的感覺,但筆者在這里卻要強調另一點:紀實不等于真實。王海鸰在《大校的女兒》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把一個人七年的錯誤、毛病一一挑出來做一種片斷組合,這人當然是一壞人;但要是做一種相反方向的組合呢?結論就會截然不同。傳記就是這樣寫出來的。人一輩子沒有誰能做到只做好事或只做壞事。片斷組合法高明就高明在,既可達到目的,又能保證句句屬實。”第六代導演也是在運用這種特殊的組合方法,他們將某些邊緣人物不幸的一面集中起來做片斷組合,這種片段組合表現出了邊緣人的某些生活側面,但卻蒙蔽了其他的側面。如果一部影片只表現出其中的一個方面,那這部影片可能是紀實的,但卻很難是真實的。這其實包含著導演的一種傾向性,“在我看來,影像其實就是意識形態,也就是你的世界觀,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不管你跟世界抱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你所作的實驗,冷漠的或是熱情的,僵化的還是生動的,都會泄漏作者的動機”。[3]238第六代導演拍攝的影片中,大多都表現了邊緣人的不幸或無奈。《北京雜種》中的地下搖滾歌手不停地居無定所,《小武》中小偷愛情、親情、友情的喪失,《安陽嬰兒》中下崗工人的落魄、黑社會老大的身患絕癥,等等,都是在表現邊緣人物的不幸或者無奈。將邊緣人不幸的片斷組合起來就表現出了邊緣人的不幸,這種處理方式其實是第六代導演對于生活、對于社會的感悟,表現了他們的邊緣化視角。當然,通過這種視角反映出來的影像不等同于真實的世界,邊緣人物也并不是真實的邊緣人物。
(二)對于“東方主義”視野的迎合
關于第六代導演關注的大都是邊緣人這一問題,有學者曾指出第六代導演也如第五代導演那樣是在迎合西方的期待。戴錦華認為:“一如張藝謀和張藝謀式的電影提供并豐富了西方人舊有的東方主義鏡像;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選,再次作為‘他者’,被用以補足西方自由知識分子先在的、對90年代中國文化景觀的預期。”[4]407在西方有一種“東方主義”的理論,所謂“東方主義”并不是東方實實在在的景象,而是西方人對于東方的一種獨特的認知。當然這種認知很多時候是并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在他們眼中,東方還是落后的、不發達的、不民主的。第六代導演拍攝的影片中大量出現了破敗的場面和搖滾樂手、小偷、妓女等邊緣人物形象,這些鏡頭的出現正迎合了“東方主義”者的期待。另一方面,西方人對于地理名稱的命名也是有意味的,“后殖民理論家發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語言,發現了‘遠東’、‘近東’、‘中東’是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5]近東、中東、遠東的劃分是西方根據距離的遠近而劃分的,而處在遠東地區的中國當然是邊緣的。在邊緣的世界里西方人所樂于看到的當然就是邊緣的景象。第六代電影中大量出現的邊緣人物:小偷、妓女、民工、地下搖滾歌手、街頭流氓等等正是邊緣景象的理想闡釋。當西方人看到的景象與預想的景象一致時,就覺得這些影片是好的,應該來看一看,甚至是投它一票讓它獲獎。這種評獎策略的實施,一方面是對影片水平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對于中國電影導演做大電影產業的一種麻痹。這種麻痹導致的結果就是,“當時的態勢正是幾乎所有的外國電影和大公司正竭力進占充滿潛力的中國電影市場,而一些‘第六代’卻與此走出了相反的路線”。[6]186
四、艱難的皈依之路:向中心靠攏
第六代導演通過自己特殊的地下時期,一方面已經在國際上大有收獲,在國內也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說當時幾乎所有的外國電影和大公司正竭力進入并占領中國電影市場,這對于第六代導演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于是,如何獲得國內觀眾的廣泛認可并占領中國本土市場,就是擺著第六代導演面前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畢竟我們的電影是為中國觀眾拍的,為的是給國內觀眾看”。[2]26
對于第六代導演來說,反叛或出走只是他們獲得生存的一個權宜之計。他們這么做的最終目的是在第五代導演壟斷中國電影市場的情況下獲得一線生存的機會,他們選擇的也正如第五代導演早期曾做過的那樣,由國外向國內滲透。第五代導演采取那種策略正當其時。當時,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之初,在與西方交流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民族的自卑情緒,認為西方的東西就是好的。第五代導演也正是抓住了觀眾的這一心理,拍攝了一些能夠迎合西方期待的影片,結果在西方大受歡迎并能夠頻頻獲獎,其中張藝謀是獲獎大戶,陳凱歌在西方也多次獲得大獎。第六代導演初登中國電影舞臺,自然受到了前輩們的影響。通過由國外向國內滲透的方式,第六代導演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這種效果已經很難與第五代導演比肩了。因為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高,人們的心理也由80年代末的自卑逐漸轉向自尊。另外,“墻內開花墻外香”、由外而內的策略是第五代導演炒過的冷飯,再來拿它做文章,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
對于第六代導演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回歸國內,從本土做起,抓住中國的觀眾。而要抓住中國的觀眾,首先必須能夠獲得公映的機會,“沒有一個導演希望自己的電影僅以紙質媒介來傳遞,不能在影院上映自己的影片的確是一個折磨人的事”,[3]272這就必然要與國家的有關的電影管理部門發生聯系。而這些部門又是第六代導演在早期所“得罪過”的部門,但當時“得罪”這些部門主要是程序上的問題,影片的內容基本上不是問題,“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比較優秀的所謂中國地下電影,很多都具有一種探索現在的人們存在價值的精神,構不成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6]129因此,當第六代電影在程序上漸漸向電影體制靠攏時,相關部門也表達出了一定的寬容和理解。
對于國家電影體制來說,不僅不會拒絕第六代導演的皈依,而且還歡迎第六代導演的皈依。因為,體制外操作對體制的尊嚴來說是一種威脅,而且體制外制作的電影在內容上也可能會出現一些對于體制不利的或不良的內容,所以,中國電影從體制上也實施了一些促成第六代導演皈依的措施,“隨著時間的演進和電影管理部門的主動努力,多數第六代導演與體制的關系已不再是劍拔弩張,張元、賈樟柯、王小帥分別在1999年和2004年被電影局恢復了導演資格。其間被解禁的還包括因《蘇州河》獲禁的婁燁”。[7]得到體制的認同,第六代導演的回歸總算完成了一個階段。但在第六代導演面前有個更為艱巨的任務,這就是如何吸引中國廣大的觀眾來觀看他們拍攝的影片,這才是回歸過程中他們所要面對的最大的問題。皈依后,王小帥拍攝了《十七歲的單車》,“只是遺憾的是,回歸后的這次創作,還沒有產生影響。這使一些‘第六代’的個人創作道路,再次增加了某些不確定性”。[6]194
如何獲得觀眾,這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導演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使是大師也需要贏得觀眾的認同,否則就會影響自己的創作。擺在第六代導演面前的同樣也是這個重要的命題。同時,電影的制作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資,資本的屬性決定了電影投資者必定會注重電影的利潤。利潤的獲得和觀眾的數量一般來說是成正比的,因此如何獲得最大數量的觀眾就是電影的投資人最為關注的。這對于習慣于拍攝個人化電影的第六代導演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雖然他們的影片在很多國際電影節上獲獎,但“由于影展的評委只有十幾或幾十人,而且教育程度較高,滿足他們的口味主要體現在題材的選擇以及藝術水準兩方面”。[8]244然而當要面對廣大普通觀眾時,就必須要考察好觀眾的審美欲求,生產適合觀眾審美口味的電影。在當前環境下,能反映觀眾的生活,能使他們在觀看時獲得解脫、凈化、放松、娛樂的電影是一種很好的選擇,畢竟“電影已經淪落為‘風塵’,成為‘墮落天使’。觀眾買票進入電影院,首要需求是消遣、娛樂、尋找夢幻”。[9]83而第六代導演執導的大部分影片都不能提供這種體驗。第六代電影中的很多場面不夠壯觀、好看,也沒有大牌明星的加盟,故事也多采取平鋪直敘的方式,雖然說思想上有一定的深度,對生活也給予了深刻的反思,但主題的沉重性、形式上的粗糙往往使觀眾望而卻步。因此觀眾也就不太愿意買票進電影院觀看第六代導演拍攝的電影。這對于作為產業來說的電影就是不利的,畢竟電影不單單是一門藝術,它還是一種產業。第六代導演中的一些人還沉浸在藝術電影或個人電影的創作道路中,很難走出來。但我們也看到了第六代導演群也在分化,一些導演開始嘗試拍攝商業電影,路學長拍攝了電影《卡拉是條狗》,獲得了近千萬的票房收入。路學長聘請了葛優、夏雨等明星,是影片的一大看點。影片將視角對準了北京的一個普通人老二,影片中既有世俗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充滿了愛心和人情味。影片表現了一個普通人的煩惱,又表現了他簡單的快樂和幸福。觀眾在電影中多少找到了類似于自己生活的痕跡,因此這部影片獲得了觀眾的廣泛認可。《卡拉是條狗》的這些做法是值得其他第六代導演借鑒的。對于第六代導演來說,他們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必須要去適應觀眾的口味,才能真正占領中國電影市場。
[1] 呂曉明.90年代中國電影景觀之一——“第六代”及其質疑[J].電影藝術,1999,(3).
[2] 陳犀禾,石川.多元語境中的新生代電影[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
[3] 程青松.看得見的影像[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4] 戴錦華.霧中風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張建軍.后現代語境中的《莊子》[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5)
[6] 吳小麗,徐甡民.九十年代中國電影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7] 侯庚洋.流變中的第六代[J].藝術評論,2006,(12).
[8] 周黎明.好萊塢啟示錄[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9] 陳曉云.中國當代電影[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J90
A
1672-0040(2011)06-0075-04
2011-09-07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基金項目“影視藝術與文學比較研究”(06BWZ004)的相關研究成果。
賈夢(1987—),女,山東淄博人,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影視藝術研究。
(責任編輯 楊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