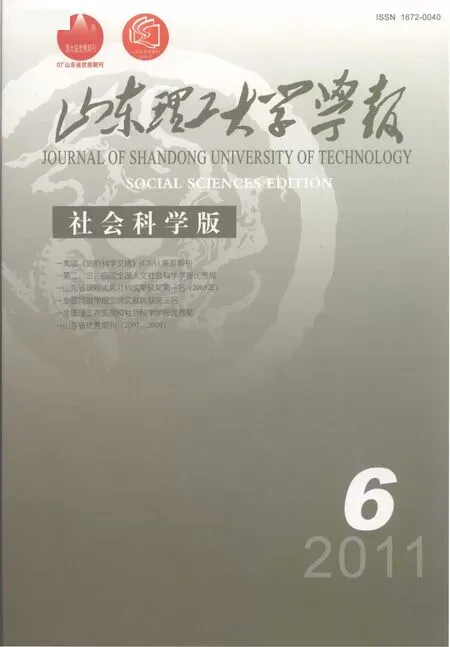中國人軀體化心理問題文化探源
高媛媛
(山東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山東濟南250100)
中國人軀體化心理問題文化探源
高媛媛
(山東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山東濟南250100)
在西方文化的視域中,中國人的心理問題常以“軀體化”的形式得以表現,被當作是一種不良的反應“軀體形式障礙”加以研究。但是深入中國文化就會發現,所謂“軀體化”的心理問題是由于中國文化的不同于西方的身心觀、不同的語言使用和體驗方式以及不同的身心關系的處理和操作方式造成的,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方式,把“軀體化”的概念原封不動地照搬到我國是不妥當的。用“軀體化”和“心理化”來劃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把“心理化”視為理性化進程在個人身上的體現更是缺乏說服力的。
心理問題;軀體形式障礙;軀體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
所謂“心理不適的軀體化反應”是指人們在發生心理問題時,不是以焦慮、恐懼及情緒變化等心理化的方式呈現,而是以頭痛、腰痛和胸痛等軀體癥狀的方式呈現。“軀體化”一詞是本世紀初Stekel創用的,當時是指“根深蒂固”的神經癥籍以引起軀體性失調的那種假設過程。[1]后來Katon等認為軀體化是籍以軀體癥狀表達精神不適的一種現象,是表達與應付社會和個人煩惱的手段。Lipowski則稱它是個體在心理應激反應下,一種體驗和表達軀體不適和癥狀的傾向,這種軀體不適和癥狀不能用病理發現來證實。
在第43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的ICD-10《國際疾病分類第十次修訂本》(1990)中,軀體化被列為軀體形式障礙的一種。作為一種臨床現象,它表現為某種身體上的癥狀而又不能從醫學角度對身體疾病做出客觀的解釋,軀體化有以下臨床特征:患者體驗和表達軀體不適與癥狀;這些軀體不適與癥狀不能用器質性病變來解釋;患者將軀體不適癥狀歸咎為軀體患病;患者據此向醫學各科求助。一般認為,這是對心理社會應激獨特的反應,即患者主要是用軀體方式而非心理方式做出反應。[2]129-135
一、中國人心理問題的軀體化表征
人們的心理不適為什么會以軀體化的方式表現出來呢?Stekel等人采用精神分析的觀點給予了心理學的解釋,他們的看法是,軀體化是一種“退行性行為”,是一種“潛意識愿望被壓抑的產物”。在其后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中國人和西方人在軀體化的表現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中國人在心理出現問題時,更習慣向醫生或咨詢者陳述身體上的各種癥狀,并希望醫生或咨詢者幫助其祛除這些癥狀。
臺灣學者曾文星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1975年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門診病人有70%的人主訴身體不適,其中更有40%的人,其惟一的主訴就是身體不適,而無任何心理或情緒上的主訴;而到1986年,前者為72.9%,后者為37.2%。大陸學者陳建華等1995年調查了前來綜合醫院心理咨詢門診求詢的853名患者,結果發現這些人在來心理咨詢門診前都曾在普通醫學科(即通科)就過診,平均次數為2.5。這些人不堪軀體癥狀的痛苦,才來心理門診求助,在咨詢時,他們單以軀體癥狀為主訴的人達53.1%。[3]肖世富等在1993年對上海市兩所綜合性醫院普通內科門診390例病人進行隨機調查,結果發現,慢性疼痛癥狀、頭昏、乏力等軀體化癥狀常常是心理障礙病人就醫的主訴。相比之下,西方人軀體化癥狀的比例就低得多,如美國Rochester地區以身體癥狀為主訴的只有20%左右。[4]
這種情況使學者們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社會文化,他們嘗試用社會文化的差異來解釋上述現象,其主要觀點是:首先,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更鼓勵人壓抑情感,在人際互動中盡量避免直接表露愛恨之情,身體癥狀的呈現不會造成對他人的傷害;[5]其次,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非個性化”的,大多中國人的“自我”很難成為一個客體,故在心理問題發生時,難以出現人格化的情感體驗,而只是關注身體反應。[6]此外,更值得關注的還有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Kleinman的觀點。他認為,軀體化的呈現在于一種社會文化沒有突出主體的人的地位,在對事件和身體狀態的前因后果的理解上更多地歸結為身體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于是人在不滿、懊喪、失望、壓抑等各種情緒發生時,便更多指向自己的身體(me),表現為生理的興奮與抑制,或其他與主體的人無關的因素。[7]
相對于軀體化,Kleinman提出了與之對應的“心理化”的概念,并指出,心理化其實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進程在個人身上的體現,因為心理化意味人們對事件和身體狀態的前因后果的理解上更多地歸結為主觀因素,意味著各種情緒更多地指向“主我”(I)”,而不是“客我(me)”,這是對人的主體地位的凸顯。據此,他認定,心理化和現代化緊密聯系,軀體化是歷史地和文化地存在于心理化之前的,而心理化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也就是說,軀體化和心理化分別成為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8]
應當承認,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探討心理不適的軀體化表達問題,并對其進行跨文化的比較是恰當的和必要的,軀體化決不是一種簡單反應方式,它作為一種特定的“癥狀”表達方式具有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需要進行深入的挖掘和探索。前面提及的觀點,有些雖不乏啟發意義,但我們認為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沒能真正揭示出中國人軀體化高于西方人軀體化的社會文化的深層原因。其二,將軀體化和心理化作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分野、把心理化視為理性化進程在個人身上的體現是值得商榷的,這可能本身就存在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同時,斷言軀體化歷史地和文化地存在于心理化之前的看法也缺乏足夠的依據。[9]
二、中國人軀體化心理問題的文化淵源
從社會文化的視角出發來考察中國人軀體化反應,深入挖掘其中的社會文化內涵,我們會發現,中國人出現所謂“軀體化”的心理問題主要由于如下方面的文化淵源。
(一)不同語言的使用和體驗方式
與西方人使用符號文字不同,中國人使用象形文字,不同的語言會對神經過程產生不同的影響從而影響大腦的意義理解和信號傳遞。符號文字主要由左半球區域進行加工,漢字則由左半球和右半球同時進行加工處理,[10]而兩個半球在功能上是有分工的,與左半球相關的是邏輯—線性,和右半球相關的是構型。由自幼使用象形文字建立起來的概念和形象的溝通回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漢語使用者為什么會自然地把符號和形象結合起來,并聯合運作,這同時也說明并強化了一種文化傾向和體驗方式,即與相關載體脫離的單純的心理問題是不存在,當心理問題表現的載體被述說時,相應的情感不適也同時得到了表達。
(二)不同社會文化中的身心觀
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二元對立一直是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圖式,而身心二元論是這種思維圖式在身心關系上的體現。“我思故我在”,人的本質被規定為“思”,也即思想。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對身心關系上一直是與此不同的另外一種理解,也即“形神合一”、“形神相即”,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對身心關系的表述是實體指涉也就是身體指涉,譬如“修身”一詞也涵蓋了“修心”的意義。不同的身心關系的理解,強化了不同的體驗方式和表達方式。[11]
(三)不同社會文化中對身心關系的處理和操作
身心關系的處理和操作主要體現在醫學傳統和醫學文化中。身心二元論決定了西方身體醫學和心理醫學是兩種獨立發展的醫學體系,西方生物醫學的傳統模式更加傾向于從器質病變程度來推斷疾病的嚴重程度,使得一切診斷手段都更多地著眼于生理器官是否出現問題,而這一醫學模式明顯無法解釋許多因為身體整體的功能性病變而出現的癥狀。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和醫學傳統中,人們更加傾向于接納“身心醫學”這樣的術語,把心理現象和生理現象視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把身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因此在西方醫學中的某種軀體化表現,在這里可能就是另一種解釋——整體的身心系統不適。如此對身心關系的處理和操作的差別也同樣強化了不同的體驗方式和表達方式。
由此可見,由于社會文化傳統的不同,人們對于癥狀的體驗方式和表達方式也不同,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軀體化”是一種不良的反應(軀體形式障礙),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它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方式,把“軀體化”的概念原封不動地照搬到我國是不妥當的。用“軀體化”和“心理化”來劃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把“心理化”視為理性化進程在個人身上的體現更是缺乏說服力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軀體化心理問題也為我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特別是本土心理治療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領域和方向。
[1] Z.J.Lipowski,楊玲玲.軀體化的概念及其臨床應用[J].國際精神病學雜志,1989,(3).
[2] 世界衛生組織.ICD-10神經與行為障礙分類:臨床描述與診斷要點[M].范肖冬,汪向東,等譯.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3] 陳建華,周淑榮.綜合醫院心理咨詢門診中精神障礙患者的軀體主述[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5,(3).
[4] 肖世富,嚴和駸.內科門診病人心理障礙的調查研究[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3,(4).
[5] Cheung,F.et al.Somatization among Chinese Depression in General Practi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1981,10.
[6] 李強,高文珺,龍鯨,白炳清,趙寶然.心理疾病患者自我污名及影響初探[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0,(3).
[7] Kleinman.A.Neurasthenia and Depression:A Study of Somatization and Culture in China[J].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1980.6.
[8] Kleinman.A.Writing at the Margin:Discourse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M].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9] 汪新建,呂小康.軀體與心理疾病:軀體化問題的跨文化視角[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
[10] Tan,L.H.,et al.The Neural System Underlying Chinese Logograph Reading[J].NeuroImage,2001,15(5):836-846.
[11] 汪新建,王麗.以心理治療反思社會文化[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
B84
A
1672-0040(2011)06-0095-03
2011-07-07
本文系山東大學自主創新基金項目“中國人‘軀體化’心理問題治療方式的本土化研究”(2009GN073)的相關研究成果。
高媛媛(1979—),女,山東濟南人,山東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講師、哲學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后,主要從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責任編輯 李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