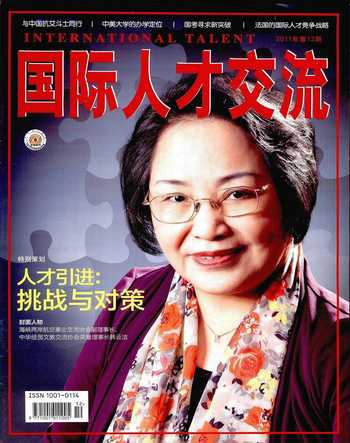馬丁.哥頓:與中國抗艾斗士同行
張曉
馬丁說,他不是巨富,也不是專家和醫生,只是普通人,有個很小的私人基金會。能在退休后做一些有用的事,而不是商業上的事情,這令人喻悅。
他曾任瑞銀華寶銀行副行長,但現在他是貝利·馬丁基金會主席。1996年,他的一位華裔朋友因艾滋病去世,萬分痛苦的他拿出積蓄創立了貝利·馬丁基金會,資助中國開展艾滋病防治。
2011年國慶節前,他榮獲了中國政府“友誼獎”,并受到溫家寶總理接見。
他就是馬丁·哥頓(Martin G0rdon)。
“相比蓋茨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我們只是一個很小的慈善組織,共有4位理事,其中1人在北京,3人在倫敦,這意味著我們決策迅速,每年用于慈善的錢只有約10萬英鎊。”
自2000年,基金會設立了貝利·馬丁獎,獎勵在中國為預防及控制艾滋病、關愛艾滋病人做出突出貢獻的醫務工作者。第一位獲獎者是青島大學醫學院的張北川,而后的獲獎者分別是來自北京、武漢、云南、新疆等地的醫護人員。
“我們與受資助者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系。”采訪中,他一直在描述自己和張北川及武漢的桂希恩這兩位教授的經歷,更多的是對幾位中國醫生、護士的稱贊。
從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國際友人的真誠與高尚。
我與張北川
“我和張北川已經是14年的老朋友了,他用一種正確的中國方式在中國做了正確的事隋,人們相信他。”
張北川在自己的博客中記述了與馬丁·哥頓的交往,開篇這樣寫道:“1997年5月,倫敦晨曦醫院(即著名的倫敦查爾森·威斯敏斯特醫院)醫護專家組成的一個訪華團訪問北京。在前往北京的班機上,有位乘客突患急癥,空姐通過廣播焦灼地求助。率領這個團隊的馬丁·哥頓先生告訴空姐,‘我們有16位醫護人員可供你們任意選擇。”
記者提及這個飛機上的突發狀況,馬丁·哥頓先生哈哈大笑:“的確,的確,當時乘務員問,‘飛機上有沒有醫生?我大聲說,‘我們這兒有16位呢。”
貝利·馬丁基金會資助了這個團隊的訪問,并資助約120位中國醫生參加“中英/英中艾滋防治研討會(北京)”。這個英國專家團隊中,有數位英國艾滋專家,他們是貝利·馬丁基金會的英方顧問。之后基金會每年在中國舉辦針對艾滋病治療與護理的學習班。
就是在這一年的秋天,張北川『收到了貝利·馬丁基金會的第一次捐贈。正是有了這一支持,張北川完成了我國符合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規定樣本量的對我國男同性戀者/男男性接觸者的首次科研調查。
“我與張北川的初次見面是在1998年夏天,他讓一位翻譯給我讀了幾位同性戀者給他的來信,他們的痛苦讓我忍不住流淚,人們能這樣把心里話告訴張北川,可見他是如何替這些患者著想了。”
“讀完那封信,馬丁立即向我{tit捐贈。我希望馬丁對捐贈指定用途,他說,只要你認為有利于工作,由你決定。”張北川在博客中也回憶兩人的首次見面。
2001年2月,張北川成為第一屆貝利·馬丁獎的獲得者,馬丁·哥頓和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等一行專門到青島舉行頒獎儀式。可見馬丁·哥頓對張北川的工作極為肯定。但張北川當時在國內卻頂著巨大的壓力,他的工作被很多人誤解,甚至是打壓。
實際上,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早在1999年就撤銷了性健康中心門診,實際上剝奪了張北川行醫資格,他不得不搬離醫院,搬到地下室搞研究。對于這次頒獎之際的見面,張北川回憶:“看到我辦公的環境極其簡陋,他未置一詞,只講到要再次向我捐贈,并詢問捐贈是在會議上公開給我還是私下給我合適。我提出公開捐贈即可。這類捐贈由我還是附院管理合適?我詢問曾毅。曾告,不必交附院,自己管理,賬目清楚,向馬丁有說明即可。”
2002年,馬丁·哥頓注意到中國的艾滋流行態勢愈趨嚴重,他增加了對張北川的資助。而張北川則把馬丁的捐贈轉給比他更需要資助的朋友們。“我用馬丁的捐贈支持了北京、哈爾濱、沈陽、大連、西安、蘭州、烏魯木齊、重慶、青島、南京、武漢、廣州等十幾個城市的人士。”
“從馬丁身上,我看到了被某些國人遺失的或陌生的高尚。在中國現代醫學史上,多位給中國以重要幫助的外國友人的名字,如星光閃耀。我深信,馬丁在中國的工作,將使他的名字,也融入這群星之中。”張北川這樣寫道。桂希恩:給患者微笑與關懷
武漢大學教授桂希恩是2003年度貝利·馬丁獎的獲得者。
1999年,桂希恩以真實的數據揭開了河南省的艾滋病問題,發現了中國艾滋病第一高發區一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
“為了治療艾滋患者,他甚至把他們帶到家中,因為當時醫院都不敢接收這樣的病人。”
“其實艾滋患者最害怕的就是周圍人的冷漠,他們大都非常孤獨。曾經有一位來自云南大理佩吉健康中心的艾滋患者,在給我的卡片上寫道:身體的病痛我還可以忍受,令我最難堪的是別人冷漠的面孔。”
“最近幾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溫家寶總理都會會見桂希恩醫生和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桂希恩醫生也和我談起過溫家寶總理和他見面的經歷。”
“有一次在鄭州,桂醫生被告知第二天早上7點準時到達酒店大堂。第二天,他準時到達,卻看到很多警察,一位警察引導他走向一輛車,桂醫生登上車才看到溫家寶總理。當時溫家寶對車里的兩位河南省領導說,你們坐到后邊去,桂醫生坐到我身邊來,我得和他好好談談。”說到這兒,馬丁·哥頓哈哈大笑。
“然后他們一起去了一個艾滋病村,路上看到有人身體不好,就停下來了解情況。艾滋病感染者需要的就是關懷。”王克榮:倫敦晨曦醫院
2005年5月12日,國際護士節,地壇醫院皮膚性病科護士長王克榮,眼含熱淚從馬丁·哥頓手里接過2004年度貝利·馬丁獎的證書。她成為榮獲此獎的第一位中國護士,此前的4位獲獎者都是醫生。
馬丁·哥頓在授獎詞中表示,艾滋病人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痛苦既來自醫學上還難以治愈,更來自社會的歧視。護士的關愛對艾滋病人的心理影響尤其重要。中國有129萬名護士,獎勵王克榮,就是要彰顯護理工作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價值。
正是出于對護士工作的高度認可,基金會每年資助若干名中國醫護人員到英國的醫院學習培訓,而不僅僅是醫生,王克榮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2002年,王克榮就被選派到英國倫敦晨曦醫院學習。晨曦醫院是一所現代化綜合醫院,其所屬的圣·斯蒂芬中心是英國最著名也是接待病人最多的艾滋病治療中心。
在那里,最讓王克榮感慨的,是點滴細節中反映出來的對病人的尊重。
候診室里飄著輕音樂、咖啡香,患者靠著沙發看雜志,使人恍惚覺得這里不是醫院,而是誰家的客廳和國內強調醫護人員儀表、服裝規范不同,醫院里看到的人,基本都穿著便裝,毛衣襯衫牛仔褲,醫患之間唯一的區別,是工作人員胸前掛著標志身份的胸牌。他們認為,這樣來就診的人會感覺更平等和放松,更有安全感。
就診室的房間都不大,醫生與患者都是—對一,門可以從里面鎖上。
在國內抽血都是病人躺在床上,護士站著操作,居高臨下。而在這里護士是蹲在地上操作,與病人面對面平視。護士在抽血過程中始終和病人談話:你抽過血嗎?緊張嗎?知道什么時間取結果嗎?多壓一會兒針眼,等等。醫生查房也不是站著進行,而是坐在病人床上,拉著病人的手詢問情況。
至今,貝利·馬丁基金會已資助20多名中國醫護人員去英國交流,晨曦醫院和圣瑪麗醫院都積極參與,接待中國醫護_人員的來訪。
同時基金會還資助英國醫院的專家來中國各地組織研討會,北京、貴州、云南、廣西、廣東、新疆、四川、山東、河北……這個名單還將不斷增加,“我們會謹嗅地在新的省份建立合作伙伴,一旦確定,我們的關系將十分穩固。”馬丁·哥頓說。
中國緣分
在基金會的網站上,導航欄第一項就是貝利·馬丁獎,緊隨其后的是佩吉健康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護理艾滋病人的中心,依托大理市第A民醫院,是馬丁·哥頓與當地政府各出資50%在一所醫院舊址的廢墟上建起來的。
佩吉既是一位來大理的志愿者護士的名字,也是馬丁母親的名字:“我的母親出生在中國的長春,外祖父和祖父都是醫生,外祖父曾在中國行醫,我的舅舅1915年出生在青島。”
馬丁·哥頓與中國的淵源還不僅僅來自母親這一方:“二戰期間,我的叔叔參軍來到了中國廣西,他負責收集日軍的行動情報,并報告給盟軍。他和我說,他當時天天都在路上跑,可當時廣西到處都是山、河,沿途的道路根本稱不上是一條路。現在我去廣西開展艾滋病防治,到處都是高速公路。”
馬丁·哥頓早在上世紀很早來就來中國擴展銀行業務,他認為,之前的工作經歷對后來的慈善工作非常有幫助。“我之前對中國的理解和認知,對我從事慈善工作非常有幫助。比如,大部分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非常相似,友好而誠懇。”
“剛開始在中國做慈善時,很多金融界的朋友給了我很大幫助,他們了解我,也信任我,都樂于幫我介紹醫學界的朋友,原中國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女士給我介紹認識了陳敏章。他們的信任是我一直非常珍惜的,信任是一種很特殊的東西,他們信任我,我也從不讓他們失望。”
“比如周小川,我們已經認識幾十年了當時他還不是什么大人物哦,這么多年我們還是好朋友。”
籌款從來就不是問題
“籌款是不是您的一項重要工作?”記者本以為會得到肯定的回答。
“籌款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我從來不去請求別人捐款,幾乎所有給我捐款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這一點在最初的時候讓我驚喜。”
“基金會開展工作的早期,我只是打算依靠我自己的經濟能力,資助一些人員交流。沒有想到的是,我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都愿意出錢資助我們基金會。當我在銀行工作時的同事向基金會捐款時,確實令我驚喜。多年來這些來自各界朋友的捐款,都是出自朋友們的自愿而非我們的請求,這些捐款使我們在中國開展的工作遠遠超出我們開始的設想。”
“我們也不希望突然得到大筆捐贈,如果我一下給某人資助很多錢,比如蓋茨突然想給我100萬美元,我并不希望真的得到它。我希望基金會一步一步地逐步成長,每年給我們捐款的人都在逐步增加,我們資助的項目也在逐步增長。我希望慢慢做,必須把錢給值得信任的人,我要確信受資助者能夠很好地使用這筆錢。”
馬丁·哥頓認為,基金會正在“走向一個遠遠超越金錢價值的境界”。
“您付出了自己的積蓄,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那您在中國又收獲了什么呢?”這是記者的最后一個問題。
馬丁·哥頓當即回答:“友誼”。
“我到中國每個城市,都有朋友在機場迎接我,白族的、彝族的,我在中國有很多很多朋友。對于生活來說,如果沒有朋友,那這個城市對我來說就毫無意義。現在,我在中國的很多城市都有很多朋友,青島大學醫學院的張北川、武漢大學醫學部的桂希恩、北京佑安醫院護士長福燕,我到哪里都像在家里一樣。”
采訪當晚,馬丁·哥頓到佑安醫院,與醫護1人員、艾滋患者一起吃晚飯。他說,這是他們的一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