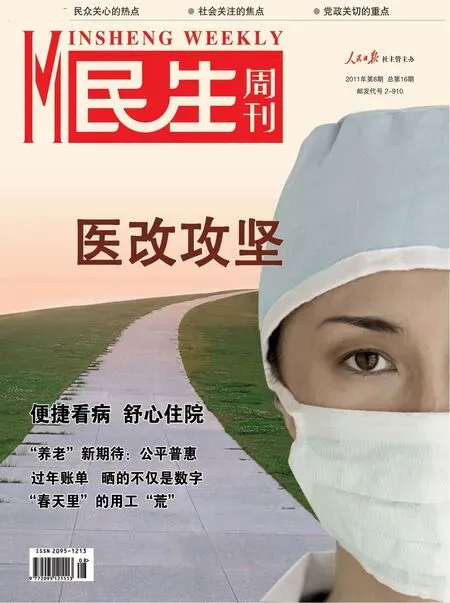“索道醫生”鄧前堆
“索道醫生”鄧前堆
鄧前堆怎么也沒有想到,他這樣一位普通的鄉村醫生,會因為一條一百多米長的索道而突然出名。而鮮為人知卻讓人感動的,則是在這個平凡崗位上,他堅持行走在怒江大峽谷深處的28年。
兔年的新春佳節,中央電視臺在新聞節目中,報道了云南省福貢縣石月亮鄉拉馬底村鄉村醫生鄧前堆的感人事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做出重要指示,要求中宣部、交通部和云南省把宣傳先進典型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盡快幫助鄧前堆實現“希望村子里修一條能通車的橋”的樸實心愿。電視臺的報道和中央領導的指示,不僅讓鄧前堆這位普通的鄉村醫生快速進入人們的視野,也讓媒體的目光聚集到了怒江大峽谷的那個偏遠的村寨。
“當醫生要溫柔”
1964年,鄧前堆出生在怒江州福貢縣石月亮鄉,怒江東岸的一個傈僳族村寨。事實上,他是怒族。因為生長在傈僳族村寨,又是家中次子,其父母依照傈僳族傳統,叫他阿鄧,“前堆是父母隨便叫的”。
1983年,鄧前堆從福貢縣第二中學畢業后,因為一場大病與給他看病的鄉村醫生友向葉結緣,經過鄉衛生院批準,他成為友向葉的學徒,正式跟著友醫生當起了鄉村醫生。
“當醫生要溫柔。”鄧醫生回憶,師傅在教授他醫術的同時,還時常教誨他,醫生對病人要溫柔、有耐心。“有時候病人治療幾天不好發點脾氣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向師傅學醫但未正式上崗前,鄧前堆還得到在鄉衛生院學習半年的機會。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他在工作中不斷自學,并能學以致用。幾年后,引薦他當鄉村醫生的友師傅當了村干部,他就成為了拉馬底村的骨干鄉村醫生。
在馬底村委會所轄的6個村民小組,每逢有行動不便或患有急病的病人,他都要挎上藥箱出診,而且“隨叫隨到”。如今的村民都親切稱他“鄧醫生”。
在簡陋的拉馬底村衛生室桌上,記者看到,鄧前堆在2004年被云南省衛生廳授予“全省實施世界銀行第七個衛生貸款先進個人”,2006年被福貢縣衛生局授予 “2006年度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先進個人”,2005年和2006年連續兩年被石月亮鄉中心衛生院授予“優秀鄉村醫生”, 2009年被評為“石月亮鄉優秀黨員”。
用藥過敏刻骨銘心
仔細回憶自己28年來行醫的點滴,有兩次治療讓鄧前堆印象最深。
他當醫生第二年的一天中午,一位姓趙的村民到診所看病,當時友師傅恰巧不在。趙主動提出要打一針青霉素。“青霉素會過敏,我不敢用,就告訴她說沒有青霉素了。”趙又要求使用與青霉素差不多的藥物。在她的堅持下,鄧醫生就給她注射了慶大霉素。
打完針,病人走出診所大約50米就暈倒在地。趙的女兒急忙跑來告訴他病人暈倒后,他立即給趙喝了一瓶葡萄糖,并迅速跑去找友師傅。
“我當時被嚇壞了,如果病人死了,我也活不成了。”師徒二人回到診所后,病人逐漸好轉。后來,趙的女兒才說,她的母親吃慶大霉素藥片一直都過敏。
此后,他給病人打針吃藥,更加謹慎。至今,沒有再發生過病人藥物過敏的事件。
還有一次夜間出診也讓他至今記憶猶新。10年前的一個傍晚,村民鄧扒才在地里干農活時不慎從陡坡上滾下摔傷右眼。“當時,眼珠子都掉出來了。右眼角有一個大窟窿,眼眶里全是泥土。”他溜索過去見到傷者的第一個反應是,讓家人立即把傷者送往治療條件好的福貢縣人民醫院或石月亮鄉衛生院。但傷者家屬因為貧困,加上傷者體重140多斤,過溜索也是難題,只能就地治療。

“我當時確實不敢治。”后來,在村領導和10多位村民的保證下,他給傷者進行了治療。最后,在傷者的右眼角縫合了4針。“我手都在發抖,擔心一不小心就會戳到眼球。”清洗、消毒、縫合、包扎、輸液,一直折騰到深夜才告一段落。鄧前堆回到家后仍然心有余悸,“主要是擔心病人感染和失明。”第二天他趕到病人家里看到鄧扒才情況良好,生命體征正常,并沒有感染的癥狀,這才放下心來。后來他又連續溜索過去給傷者輸了10天液。最后,鄧扒才的眼睛總算保住了。
行走在怒江大峽谷,翻山越嶺是家常便飯。28年來不間斷地“上門出診”,鄧前堆從未收過一分錢的出診費,僅僅按規定收取醫藥費而已。
打個電話就溜索過江
2002年,鄧把家從山上的培建村搬到山下的公路邊,距離他上班的村衛生室大約500米。他家三間小平房,依一塊巨石而建。“蓋房子花了2萬多塊,現在還欠著6000多元的債。”家里除了一臺早已過時的小電視機、一臺DVD機和幾件破舊的家具外,無其他財產。靠邊的一間伙房,連后墻都沒有,內設著一個簡陋的灶臺,用來煮豬食,還有一個簡單的火塘,用來做飯。整個廚房光線昏暗,有一半的空間是一塊巨大的巖石。
鄧前堆說,去年他妻子在山上找豬草途中摔斷過3根肋骨,如今體弱多病,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16歲的兒子范志新初中畢業后在家務農,女兒范志花初中畢業后也去了四川一位親戚家打工。
鄧前堆讓他兒子把央視報道他溜索過江為村民看病的光碟放進家里的DVD影碟機。看到身邊的人上電視,他的家人和在他家里看電視的兩個小男孩對著電視一邊“點評”一邊大笑。問及上電視的感受,這個47歲的漢子臉上流露出一些羞澀,靦腆地說了一句傈僳語。多次詢問是什么意思,一個小男孩才翻譯說是:“太高興了。”
按照福貢縣衛生系統設置,每個村委會的村衛生室至少要配備2名鄉村醫生。在拉馬底村衛生室除了鄧前堆,還有一名女醫生李梅英。李梅英雖然也是本地人,但因從小生長在怒江西岸,沒有溜過溜索。2005年,她當上鄉村醫生后,曾做過幾次溜索,但都有人帶。“一個人很害怕,不敢過。”
因此,村民的疾病預防、衛生保健、計劃生育政策宣傳等重任就落到了鄧前堆的肩上。不僅每月底要固定溜索過江去為村民打疫苗,如果村里有人患疾病,不能過江的,他都要親自溜索過江治病送藥。28年來,一直如此。以前通訊不便,村民會讓年輕人來請。現在60%以上的村民都知道他的電話號碼,只要打個電話,他就要溜索過江。
“還要當鄉村醫生”
當鄉村醫生的20多年間,他的工資從最初的20元,逐漸增加至120多元。到2009年7月份,他的工資才增加到342.5元。除了工資,對于需要輸液觀察的病人,還能向每位病人收取4元的治療費和3元的觀察費。在感冒、痢疾等常見病高發季節,每月能有四五百元收入,平時每月只有三四百元。這樣,他每個月有六七百元收入。雖然期間也有人勸他放棄鄉村醫生,到外地打工,每個月至少也能掙1000多元。但他覺得,當鄉村醫生能實實在在為村民減輕病痛。現在,村民見到他都會主動打招呼,路過哪家都會熱情挽留他喝杯茶水。
他所負責的拉馬底村,計劃免疫健康建證率達100%,接種率達98%,孕產婦住院分娩率達90%以上。他累計出診5000多次,步行約60萬公里。
鄧醫生說,現在他最想學習外科,特別是“骨折復位法”。他說,拉馬底村位于怒江兩岸,山高坡陡、險壑縱橫,村寨之路狹窄艱險。村民不僅種地容易摔傷,上山找柴火、豬草也容易摔傷骨折。如果自己全面掌握了骨折復位的技術,到時候就不用動員病人下山進城了。
“骨折復位不好,就會影響別人一生。”他雖然學習過骨折復位的理論知識,但沒有實際操作經驗,至今不敢接骨,“連脫臼都不敢治”。
據李梅英介紹,幾乎每天都有村民到拉馬底村衛生室看病。少則五六人,多的時候有二三十人。人多時,她和鄧醫生兩個人忙得團團轉,“連飯都顧不上吃”。
雖然工作很忙、工資也不高,但鄧醫生表示,自己已經干了大半輩子鄉村醫生,無論如何都會堅持下去。“出名了,還要當鄉村醫生。”
(本刊綜合報道) □ 編輯 劉文婷 □ 美編 龐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