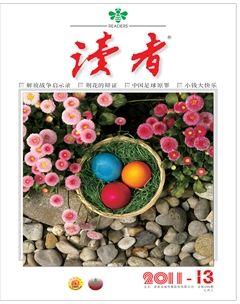葉公超:最是文人不自由
蕭瀟
葉公超出身書香世家。他中學時代即留學美、英、法。曾是著名詩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詩集。后入英國劍橋大學,獲碩士學位。在英國他得到羅素的賞識,還與著名文論家艾略特亦師亦友,并首次把艾略特的作品引入中國。
那時北大英才云集,但葉公超憑著劍橋碩士的文憑,昂首步入英文系。這一年,他才22歲。下面的學生大多比他年長,廢名就比他大四歲,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兩歲。這是他的兩個得意弟子。梁遇春學習起來玩命,廢名逃課也很拼命。
葉公超小小年紀就去了美國,英文了得,但中文底子沒打好,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不夠深。胡適贊他:“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說得更好,就是外國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見得說得過公超。”但聞一多卻戲謔他為“二毛子”。葉雖不以為忤,內心卻大受刺激,對中國文學藝術猛力進修,不久即翻然一變,成為十足的中國文人。他上課時口銜栗色大煙斗,一派英國紳士派頭,加之一口流利的英文,學生聽得耳朵都長了,下課后還不愿離去。特別是那些純情女生,個個如癡如醉,恨不得即刻以身相許。
葉公超的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偶爾有人提問,他就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大家相安無事。有學生問,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匯》里查不著,怎么辦?他說:“那個《詞匯》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
葉公超脾氣壞,尤愛諷刺挖苦人:“他最注意發音,如果發音有誤,照例須挨罵……即使是女同學,如發音惡劣,亦不稍假以辭色,直言斥諷,入木三分。”他教錢鐘書時,也是這派頭。他挖苦錢鐘書說:“你不該來清華,應該去牛津。”
葉公超的才子脾氣比他的教學方法更出名。他名士派頭很足,有時路上學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他似沒看見;有時學生沒看見他,他卻隔著大馬路大呼學生的名字。他考試評分非常嚴,令人提心吊膽。有個學生有點小才氣,比較狂傲,在閱“莎士比亞”這門課的試卷時,葉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盡管他的試卷答得沒有什么可挑剔的,但葉就是只給他58分。那學生去找他,想請他多加兩分。葉見之,明知其意圖,卻只是很熱情地給學生煮咖啡,和他興高采烈地談國家大事。談了足足兩小時,就是不給他討分數的機會,哪怕幾秒鐘。學生無奈,以為沒戲,只好悵然離去。葉見他欲走,嘴上說“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鐘時,卻追上去和學生握手,主動說給他把分加上去,但同時提條件說“以后上課時不可囂張”。
葉公超偏愛述而不作,不立文字。他參與了《新月》雜志的編輯,最后三四期,因文稿匱乏,他只好自己動筆,刊出的幾乎全是他的文字。1933年,葉公超與聞一多等創辦《學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華的高材生,季羨林也在其中。有一次季的散文《年》受到葉的垂青,獲得發表,這下把他美得不得了,緊接著又寫了篇《我是怎樣寫起文章來的》,期望也得到葉的首肯。可沒料到,葉大發雷霆,鐵青著臉大吼:“我一個字也沒有看!”季嚇得目瞪口呆,趕忙拿了文章走人。
魯迅與新月派一向勢同水火。1936年魯迅逝世后,葉公超花了幾周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重讀了一遍,發表了萬字長文《關于非戰士的魯迅》,高度贊揚魯迅在小說史、小說創作和散文上的成就。他甚而批評他那小圈子里的“哥們兒”——胡適、徐志摩的散文不敵魯迅的。這種由衷的揄揚,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適都十分惱火:“魯迅生前吐痰都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么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不以為然,強調:“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上的成就。”最后的歲月,他寫的絕筆《病中瑣記》的最后一章《評論魯迅》,他還說想把當年的《關于非戰士的魯迅》找來讀一讀。他始終認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成就”。
葉公超原本無心仕途,甚至反對文字議政。但1940年的一天,他突然離開昆明赴香港,自此從中國文壇消失了。
原來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信件穿山越水,飛到了葉公超手上,叔父葉恭綽蒼勁的筆跡赫然入目。叔父在信中,焦急地說了上海的事態,他擔心姨太太潘某貪婪撒賴,可能圖謀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內的全部財產,因此叮嚀葉公超火速赴滬,設法保全毛公鼎。他強調:“過去日本人和美國人兩次想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沒答應。這是國寶,決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他星夜兼程。果不其然,潘某向日本憲兵隊告了密。日本人立刻派兵把葉宅包圍得嚴嚴實實。在葉宅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騰了大半天后,連鼎的影子也沒找著,氣急敗壞之際,便以“間諜罪”的罪名把葉公超拋進大牢,又不分晝夜,對葉公超先后7次提審,2次鞭刑、水刑,逼其說出藏鼎的地方。他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卻守口如瓶。他甚至做好了死的準備。然而他沒能就死。
情勢漸緩之后,葉公超密囑家人仿造了一個贗品繳上去,以蒙敵聽。當他形容憔悴地走出牢房時,已然被整整關押了49天。翌年,他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毛公鼎運出大陸,終于使這一珍稀國寶一度脫離了虎狼之區。
日寇這一打,沒把他的性命打掉,反把他對政治的興趣給“打”出來了。經此生死風波,他心態一變,決意應承友人的延攬,辭教從政,自此涉入外交界。葉公超在清華園與友人談及蔣介石時對其并無好感,那時壓根沒想到自己將來會入蔣的彀中,一度還成為重臣。這個曾對政治不屑一顧的人,這個因劍橋背景和語言天資而有些恃才傲物的人,一踏入政界,竟能憑借純正的牛津口音、叼著煙斗的英國紳士派頭,馳騁外交戰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方是紳士,他比紳士還紳士;對方是流氓,他也會說比他更臟的臟話。這讓在瓷盤上作畫的葉公超贏得了“文學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譽。
蔣政權敗退孤島后,驚魂未定,前路未卜,正是在葉公超手里,簽訂了《中美共同防御條約》,這對蔣政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保證,為臺灣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后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基礎。葉公超也因此成為蔣介石時期任期最長的“外交部長”。任“大使”期間,他極受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器重,也成為麥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語受到眼高于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的賞識。他應邀發表演講,“不看講稿,出口成章,手揮目送,亦莊亦諧。有時聲若洪鐘,排山倒海;忽然把聲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竊竊私語,全場聽眾屏息靜聽”。演講完畢,三四百位聽眾起立鼓掌,數分鐘不息。在場的多位名教授都贊許他的英語是“王者英語”,聲調和姿態簡直可以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相媲美。恰在此時,在北京有人問留英多年的朱光潛:“中國誰的英文最好?”朱想了想,說:“可能還是葉公超。”
葉公超的英文確乎已到了令人連嫉妒之心都沒有的地步。他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語”與世界各國政要觥籌交錯,可謂意氣風發。他熟讀《孫子兵法》,并將其靈活自如地運用在外交上,十分有效。
不管葉公超的外交才能如何,還是改變不了臺灣“外交部”逐步淪為“斷交部”,以致像“王小二過年”一樣的凄慘局面。蒙古于1946年元旦脫離中國宣布獨立。蔣介石對此一直反對。對中國百余年的歷史屈辱,他更是刻骨銘心。1961年聯合國大會討論蒙古入會案時,葉公超為擴大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勉強同意蒙古入會。蔣知道后勃然大怒,質問:“是做‘美國大使還是做‘中華民國大使?”嗣后,蔣介石一個急電,把葉公超召回“述職”。葉公超不知內幕,連辦公桌都沒有整理,只帶了幾件襯衫、領帶,提起皮包就飛回來了。他原指望三日即歸。誰知“總統”將其召回,卻不召見。安理會復會日期轉眼將至,他急于返美。但到第三天他才被冷淡地告知:另有安排,不必再回美國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此行就是他職業生涯的終點。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賓館繞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自此他被禁止出境長達16年。
被逐出政壇后,葉公超的生活日趨沉悶。1962年春天,他應英千里、梁實秋等的邀請,到臺大、師大兼任教授。他在臺大外語系開的“現代英美詩選”是選修課,時間安排得并不好,可是第一天聽課者就將教室內外擠得水泄不通,場面之熱烈前所未有。3月13日下午,還沒到兩點鐘,教室就已爆滿,聽課的很多是旁系的學生,他們特來一睹他的風采。在學生的翹首企盼中,他準時出現,依然是風度翩翩,如同出席記者招待會或演講會。他沒帶任何講稿,天馬行空,首先問大家中國詩的起源,然后一直講到英美現代詩,講到狄金森、艾略特等代表人物,如數家珍。
自離開聯大,20多年過去了,此番重上講臺,葉公超也不由得感慨:“還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有人問:“假如生命可以重新來過,你打算如何?”葉公超不假思索地答:“我再也不做同樣的事!”
新聞媒體報道葉公超任教的消息,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當局不高興,結果他只教了一個學期,就被迫永遠離開了講臺。昔日的風流倜儻也一掃而空,老態畢顯。
在最后的20年,他雖有“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虛銜,實則無“政”可“務”。他自嘲說:“身邊有特務,政事不準問。”被困之中,他的后20年以練書法和繪畫打發時光。他對好友梁實秋說:“好怒而寫竹,喜則繪蘭,閑來狩獵,感而賦詩。”
他喜歡畫竹,所畫雪竹尤富“不勝故國山河之感”。友人向他求畫,他在畫上的題字是:“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云處總無心。”此時,葉公超已不再“以罵會友”,而是“以畫會友”,他和張大千、臺靜農都是好友。
葉公超的書畫作品曾兩度在香港展出,一時轟動香江,可惜兩度他都未能躬逢其盛。他晚年時,書房中掛的是他指定何懷碩畫的:“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
蔣介石辭世后,葉公超的日子稍顯寬松,還被繼任的蔣經國聘為“總統府”資政。但他依舊被困在孤島上,不準去美國與親人團聚。“我會被困死在這個島上。”他浩嘆。
直到1977年12月,有人向蔣經國建議讓葉公超出去走走,蔣當即表示:“只要擔保他按時返國,似無不可。”葉因此才有機會再次踏上那熟悉的土地。在最后的時光,他時常在醫院走廊上散步,愁眉苦臉,動輒要哭。他指著家中的一幅《煙波江上一翁》說:“這老頭就是我。”
1981年中秋之際,葉公超異常想念家人,但他們都遠在美國。中秋夜,他興致勃勃地揮毫書寫蘇東坡的《赤壁賦》。11月17日,收到宋美齡從美國寄來的黃褐色純毛背心和消化餅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語。次日晚,葉公超在病榻上對記者說:“我希望能再活個三年五載,整理一些少年時寫的作品。”不到兩天,他就走了。臨終之際,身邊沒有一個親人。
(史姆摘自《傳記文學》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