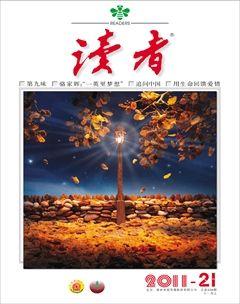莫慌做鐵石心腸的船長
2011-05-14 13:11:02蔣方舟
讀者·校園版
2011年21期
關鍵詞:生活
蔣方舟
高中三年,大學三年——今年是我一個人生活的第六個年頭。雖然滿眼都是熟人朋友,見面打招呼,笑著說些應景的話,但也不算進入彼此的世界。大家在談論著什么,都以為我已經離開了,我才甕聲甕氣地在角落里說幾句話,大家驚得一個冷戰,仿佛我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冷風。
海子有詩:“明天,明天起來后我要重新做人……揮霍我自己的青春,然后放棄愛情的王位,去做鐵石心腸的船長。”越是離家萬里,所在的城市越是大而不當,鐵石心腸的決心就越堅決。這樣心態的人越來越多。我也一直想繃出冷漠的老臉來,才半天就“撲哧”泄氣——還沒有揮霍過什么,那就莫慌做鐵石心腸的船長。
社會早遠去了溫良恭儉讓的文化,而變成了緊張的“武化”氛圍,人人肋骨磨肋骨,撞得生疼,溫暖變成了某種守株待兔也等不來的東西。人像原始人一樣,赤身裸體生活在一個冰冷無比的世界里,冷得要死,凍得生病,只能自己琢磨能暖和起來的辦法,笨拙而試探性地開始鉆木取火,過程漫長得貌似徒勞,但有足夠的耐心就會有火星。
宿舍樓下有個小保安,可能是比我還小的女孩,每天晚上裹在軍大衣里值夜班,我上樓看到她總是覺得非常凄苦。后來好幾次,我半夜下樓,都看到她和隔壁樓的男保安調笑打鬧,男保安看她冷,買了個煎餅要喂她吃,她左右躲閃。他們是一對兒,但只能等到三更半夜,全樓的人都睡了,監視器也累了,才能擅離職守,幽會一會兒。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