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桂冠上的“江浙現象”
王家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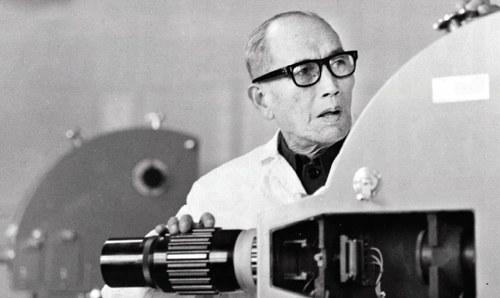
2011年初,87歲的內科血液專家王振義老先生,因其在白血病治療研究中的創新性地提出“誘導分化療法”,從國家主席胡錦濤手里接過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證書。
這項設立于2000年的獎項,每年度不超過兩位獲獎者。過去十余年,吳文俊、谷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這些獲獎者,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按照籍貫統計,18位獲獎者中,來自江浙滬地區的人數最多;其中江蘇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總數的約四成。今年獲獎者王振義院士,就出生于江蘇省興化市。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華東師范大學人才學教授葉忠海認為,由于地理環境、經濟及民風的不同,各地往往呈現出不同的人才景觀。“籍貫或出生地是他們年少時的成長環境,隨后的求學經歷也與此相關。”
科學界的“江浙現象”
在國家最高科技獎獲獎者中,年紀最大的91歲,獲獎時的平均年齡為81歲,少時求學也大約在八十年前。他們大都歷經這一代杰出人才成長的路徑:曾就讀于新式學堂,進國內最好的高等學府,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其中江浙學人的成長經歷,更是一個時代文化教育狀況的縮影。
20世紀之初,江浙地區較內地更早進入現代文明,西方現代技術與當地工農業融合。當地人的求學方式和教育理念也因而發生改變,相應的技術學校興起,新式學校普遍講授算數理化。作為西學傳播的中心,上海形成中國最初的都市,東往上海念大學也成為一時的風潮。例如,今年獲獎的王振義是江蘇興化人,1948年畢業于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2008年度獲獎者徐光憲出生于浙江紹興,24歲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2000年首屆獲獎者吳文俊在上海出生,21歲時就從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畢業。
如果說,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人數尚少,不足以說明江浙地區人才輩出的話,那么,兩院院士的籍貫分布則更具統計學意義。《2009中國兩院院士調查報告》顯示:在1955年至2009年間當選的中科院與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計算,江蘇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這三地總共占兩院院士總人數的四成以上,達41.19%。實際上,早在1948年,考古學家夏鼐就發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指出,以出生地來計算,第一屆院士以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最多,均為17人,二者共占全體院士的42%。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高級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獨占鰲頭,乃至于直到如今,在人們的印象中,帶有吳儂軟語“腔調”的普通話還是科學、人文大家的另一種“標識”。
江浙地區學風濃厚,自南宋以來就是有名的“才子之鄉”。據統計,明清時期該地區共產生了202名狀元。浙江學者沈登苗認為,“江浙從經濟中心過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數百年,這樣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續周期也很長,仍能釋放百年的熱量。”
江浙地區上百年的人才延續和聚集,成為近現代中國的一道令人稱奇的人文景觀。其中江蘇無錫的鴻聲鄉更有“院士之鄉”的盛譽。當地的錢氏家族自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國學大師錢穆以來,涌現了錢偉長、錢令希、錢臨照、錢易、錢俊瑞等杰出的科學人文大家。
人才與地域
清華大學2007級電子工程系學生朱峰還記得,他的高中母校蘇州中學的實驗樓就是的錢偉長題的字。低他三級的師弟、2010級軟件學院吳曉陽也自豪地說:“母校圖書館的兩面墻上,掛的全是出自蘇州中學的科學家肖像。”
和他們一樣,當年19歲的錢偉長,正是從這里考入清華,北上求學。
錢偉長以外,蘇州中學還先后走出了激光與非線性光學家姚建銓、工程力學家錢令希、物理化學家吳浩青、中國現代光學奠基人龔祖同、計算科學奠基人馮康、高分子科學家錢人元等大師級的人物。
而江浙地區出生的院士,更不勝枚舉。人才與地域之間,真是那么密不可分?
“人才地理”關系研究始于1923年,地理學家丁文江發表了《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一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葉忠海說,“這個‘地不僅僅指自然地理,還有經濟形態,民風習俗,甚至是家族傳統。無論是書香門第的沒落,還是商幫望族的發家,都有‘地的影響。”他將人地關系分為小環境和大環境,“小”即是家庭與社交環境,“大”則為地區和國家環境。
中國人講究家道傳統,祖輩的影響最為直接,歷史上多有子承父業的佳話。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均是書法大家,北宋楊家將四代人戍守北疆,而晉商、徽商、閩商等商幫家族更是延綿了數百年。
地區環境則是抽象的因素,人們多以籍貫為例。同一籍貫的人,由于地區經濟、文化傳統、教育環境相似,其行為氣質也有相近。剛、柔、憨、狡等詞匯被用來形容不同的個性氣質,它們也將人們引向了迥異的術業傾向。民間有言:中原多俠客,江南多文人,嶺南則多術士。
放在歷史的維度上,地域特征與群體氣質也多有變遷。
近現代歷史學者普遍認為,和唐宋以來經濟中心轉移的方向一致,人才聚集地逐漸從中原轉入長江流域,在南宋時形成了“蘇杭人才軸線”。
這不僅使得進士人數逐漸南多北寡,其民風氣質也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春秋戰國時,齊魯大地本是中華文化發源地之一,近代卻有了“山東出響馬”的俗語;西南古稱蠻夷之地,后民智開化,蜀人漸漸以詩詞稟賦揚名。
至鴉片戰爭,這個古老的國度不情愿地敞開了大門,中國地域人才分布,也有了新的坐標系。
“通商口岸不僅往來貨物,一個新的話語體系也隨之闖進來了。”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楊念群認為,各地域已經脫離了自給自足的語境,相當大程度上需要考慮外來西方話語的滲透。
美國漢學家柯文對此也頗有興趣。他認為,從地域角度而言,西方沖擊造成了中國“沿海”和“內地”的反差。沿海地區是商業超過農業,現代多于傳統,外向而非內向,因此,中國近代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產物。
然而,由于各地域固有的思維不同,各地對西學的反應也不盡相同。“內地湖南發起的是洋務運動,是從物質層面師夷長技以制夷;江浙人喜歡辦學堂、學西藝;廣東人的行動,則是要傳播新的思想。”楊念群認為,正因各個地區的人“分而治之”地接納了新觀念,才構成了近代中國多元而開放的人才局面。
人才地理流變
今天的名校,大多與清末的西學涌入有不可忽視的聯系。
當年的南洋公學地處租界,教師大部分留美歸國,所用教學全為麻省理工學院的原版教材。一百年后,在它的基礎上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學,先后走出錢學森、王安、吳文俊等人。在兩院院士中,有200余位都是交大校友。
但傳教士帶來的幾本西洋書籍,也僅僅是江浙地區科技人才興盛的助推器。
江浙自有其“考據之學”的淵源,歷史學者傅國涌認為,這一學科學本來就是研究社會運行規律,具有現代學科的考證方法,成為江浙一帶學術得以細分的基礎。早在乾隆年間,江浙舊式書院的課藝內容已經有所伸展,“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
及至19世紀末,租界的傳教士們建議開設現代專門學堂,所設科目相當細致,有“律法學堂、詞章學堂、醫理學堂、礦物學堂”。
因為研習西學西藝的水平不斷提高,上海龍門書院、求志書院等也逐漸改制為專門學堂。上海周邊紛至沓來的求知青年,所選課業也開始明顯向理工科傾斜。
因而,江南人才的類別也隨時代轉換而變化,杭州師大吳越錢氏家族研究所所長李最欣介紹,這從江浙錢家可見一斑:錢家宋代有秘書監錢昆,明朝有翰林院編修錢福,到了近現代,就多西學院士了。
如果說江浙人轉向理工科是“務實”的典例,同樣是沿海的嶺南地區則有“務虛”的情懷。
以香港、澳門為門戶,粵人不僅穿洋服、開洋葷,還以辦報紙、創學會的方式,首先傳播西方現代思想,呈現出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其影響不僅在仕大夫階層,連廣東“十三姨”也成為接受西方文明的浪漫形象,在電影中一再展現。
事實上,嶺南的理想主義氣質由來已久。其南部臨海、水網交錯,交通便利;北部則以山地形態為主,土壤沃饒。如此,嶺南地區農商發達,或謀得漁鹽之利,或耕織有余,世風奢靡,喜尚新奇。
國學大師胡樸安評價說,“粵人好大喜新……有能以新學說、新主義相號召者,倡者一而和者千,數日之內,全省為之相應。”
因而,太平天國運動以“拜上帝會”為名,一呼百應;康有為等人一脈相承,試圖以基督教新教改革為背景,建立“神權—世俗”的現代君主政體;孫中山,則帶來了五權憲法等共和思想,追隨者亦眾。
面對西方文明,嶺南人從其思維習慣,將文化變革作為價值取向,楊念群說,“正是理想主義的奔走呼號,成就了中國最初的思想啟蒙。”
人才分布總是在歷史與地理兩個維度上交錯,時至今日,因“籍貫”而產生的人才差異已遠不如百年前顯著,對人才的評價標準也更為多元化。
“人們需要的是自由發展,成才也不拘一格。” 傅國涌認為,人才的范疇不再拘泥于學術及研究領域,各行的佼佼者,只要有一技之長,皆可稱為“人才”。
沿著錢偉長當年的求學之路,從蘇州中學走到清華大學的吳曉陽,也并沒有為自己規劃一個純科研的未來。他的計劃是畢業之后創業。有趣的是,這個男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母校畢業名人不是科學家錢偉長,而是排球教練袁偉民。★
(本刊記者錢煒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