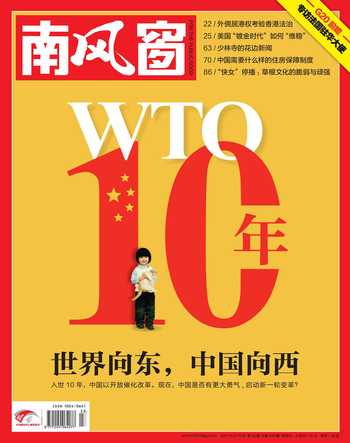改變“應對”策略,加速推進改革
徐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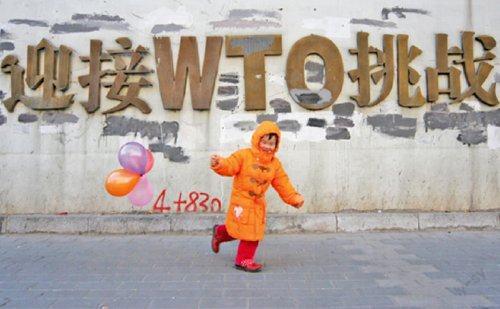


2011年11月10日,中國將迎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周年紀念日。在入世10年以后的今天,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并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然而,相比于所取得的經濟和貿易成就,我國參與全球貿易規則的動力和能力明顯不足,入世對于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和市場法制體系建設的推進作用似乎也正在弱化。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正在呈現新的發展趨勢,這種新的發展趨勢將使一國在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中的話語權不但取決于其經濟貿易硬實力的大小,更取決于其駕馭全球經濟貿易規則制定的軟實力的高低。就這些議題,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暨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王新奎接受了本刊記者的獨家專訪。
不要把“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過度政治化
《南風窗》:到目前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而美國、歐盟及其成員國、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認。事實上,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中國加入WTO 15年后,即2016年將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最近這一問題又被廣泛關注,源于溫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呼吁歐盟提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而歐盟迄今仍不承認。“市場經濟地位”到底對我們意味著什么?
王新奎: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并不是在中國入世的時候為中國度身定制的,而是有其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中長期發展的軌跡。眾所周知,無論是關貿總協定還是世界貿易組織,都是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成員方組成的,因此在關貿總協定或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協定文本里只有公平競爭或非歧視的概念,而沒有涇渭分明的“市場經濟地位”或“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但歷史的現實是,幾乎從關貿總協定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面臨一個如何處理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的貿易關系的問題,當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自身的角度出發,把這些國家一概稱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在二戰結束前后,發起建立“關貿總協定”的時候,美國和(前)蘇聯還是盟國,蘇聯也曾表示愿意加入關貿總協定。當初蘇聯是全球唯一的計劃經濟國家,為了吸引蘇聯加入關貿總協定,準備在關貿總協定中專門設立一章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條款。在當時,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還并不是一個貶義詞。后來,冷戰開始,蘇聯自己搞了一個名叫“經互會”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的多邊貿易體系與關貿總協定相對抗。但是即便如此,在關貿總協定體系內也仍然存在著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這是因為,有一部分原關貿總協定的創始國后來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如捷克和古巴,特別是50年代中期以后,越來越多的東歐國家,如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紛紛要求加入關貿總協定。在這一過程中,出于冷戰的需要,關貿總協定各締約方逐步發展出一套處理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貿關系的做法,從國內法上掃除與東歐國家發展貿易關系的障礙。
在當時,對東歐國家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待遇大致包括兩大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的內容是政治性的,即各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議會紛紛修改關稅法或貿易法,確定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市場經濟國家的標準,并授權政府在此法律框架內處理與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第二部分的內容是技術性的,即要求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東歐國家必須做出進口承諾、接受出口配額限制,后來又發展出更加技術性的所謂“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問題”。
中國加入WTO時,冷戰已經結束,并且中國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改革,有了有效的關稅制度和匯率制度,完全取消了指令性的進出口計劃管理。在當時,經過艱苦的“入門費”談判,最后對中國保留了一條與“非市場經濟地位”有關的歧視性的技術措施,即《議定書》第15條“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并且規定了自加入起15年后終止的硬性約束。
我認為,在這里有兩個重大的誤解必須澄清:第一,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并不是一項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而是成員方通過制定國內法確定的規則,這一規則不是多邊的,而純粹是單邊的;第二,也不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5年后,即2016年將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2016年僅僅是終止《議定書》第15條“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這一項技術性措施,中國是否能獲得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取決于各成員方是否修改其國內法,并沒有“自動”獲得一說。
《南風窗》:為什么對于歐盟仍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在9月20日對歐盟“表達了失望”,并認為“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決斷”?請問背景是什么?
王新奎:這有更深層的背景。我不知道你對經濟全球化是怎么認識的,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范圍內生產和發展的必然規律。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的頂端,全球市場必然由他們主導。經濟全球化主體是誰?不是主權國,而是全球性跨國公司。很多人認為我們這么大的貿易國家應該有全球利益,但在目前階段我們在很多情況下沒有直接的全球利益,或者說利益不清晰,因為我們沒有全球性跨國公司。為沃爾瑪供貨的加工廠,它有什么全球利益?沒有的,有全球利益的是沃爾瑪。當然我們最近這幾年企業走出去發展的步伐很快,但要形成有全球影響力的巨型跨國公司,還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過程。
于是,我們就在國際貿易談判過程中面對一個困境,人家的大量跨國企業在我們這里,他們的政府為他們的企業向我們提出的要價清單非常具體。而我們在他們那邊沒有跨國企業,提不出具體的要價清單,政府只能提原則性的政治要求,比如“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我認為這是為什么長期以來這一問題如此引起公眾和政府高度關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之所以主張不要把“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問題過度政治化,是因為,要向一個成員方提出給予“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要求,必須滿足以下三個要件:第一,這個國家必須有關于“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完整的法律;第二,這個國家必須有實施該法律的有效的行政法規及其措施;第三,這個國家必須與我們有實質性的一定規模的貿易關系。在目前,能滿足這一條件的大多是西方主要的發達國家。平心而論,從當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內所處的實力地位來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認同我們現在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不可能在政治上給予我們“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認為,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不需要別國的立法機構以頒布國內法的方式批準的,世界上沒有這個先例。單方面要求西方發達國家給予我們“市場經濟地位”,反而為他們提供了對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評頭品足的機會。更何況,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最終要通過一系列的技術性貿易措施來體現,當這些技術性貿易措施被陸續終止以后,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政治能量也將大大下降,這比我們主動向人家去要求市場經濟地位所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中國入世10周年之際的若干反思
《南風窗》: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周年,回顧走過的10年入世之路,您認為我們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王新奎:我認為有三點值得引起深思。第一,當初我們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有一個局限,我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只是一種可供利用的外部發展機遇,我們不過是利用這一過程來實現我們的現代化,而尚未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由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和接受全球多邊貿易制度安排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實際上入世以后才發現,我們本身也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了。當初說“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大于挑戰”,我們把入世看作是一個機遇。現在的問題是,你已經發展了,人家要你為他們提供機遇,我們卻還轉不過來。這是第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現在要補課,要充分認識經濟全球化。
第二,就是因為對經濟全球化認識上的不足,把入世看作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策略,因此在履行對WTO承諾的過程中,我們把基本的出發點放在“應對”上,而且,往往把這種應對限制在經濟貿易領域。我個人越來越覺得用“應對”這個詞不妥。議定書彰顯了國家的承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的第一頁就載有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的《批準書》,《批準書》有他的簽名并加蓋國印,并莊嚴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議定書中所載一切完全遵守”,但在履行承諾時我們卻說是“應對”入世。本來加入WTO是想給改革開放增加新的動力,但因為采取“應對”的策略,導致改革動力不足。
第三,整個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和我們國家的傳統觀念、文化觀念差異很大。首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是形式公平。我們國家的傳統觀念不是這樣,我們要求實質公平。其次,WTO規則是程序正義,我們不是,我們是結果正義。再次,西方強調契約關系。就是說它把《議定書》看作是一個合同,我們往往認為簽了合同就要相信我們有道德、誠信至上,西方人不這樣,他要制定一系列制度來制約,它會先假定你不道德。這些差別使人們對通過入世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必要性和功能性的認識出現動搖,甚至像當初我們因入世而制定的《行政許可法》—在中國法制建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法律,頒布后也沒有真正發揮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通過入世推進法制體系建設的極好機會。
充分認識多邊貿易體系扁平化趨勢
《南風窗》:伴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全球經濟的衰退,我們正面對更多的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而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也呈現新的特點。與此同時,人們的關注重點也從貿易自由化轉向氣候、環境與貿易等新議題,發達國家正試圖在這些與貿易有關的新領域構筑一種新的貿易規則,我們將如何應對新的貿易保護措施和貿易規則?
王新奎:WTO就是把各個國家的與貿易有關的政策法律措施約束在大家議定的范圍里。從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以后,WTO也做了不少工作,總體評價,這次金融危機沒有引起貿易保護主義大規模反彈,基本上所有國家都在議定的范圍里采取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和貿易爭端,都在規則之內,而且基本是公平的,誰都可以用。金融危機沒有導致貿易保護大戰,應該說全球多邊貿易體制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首先要肯定WTO的作用。當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是有的,我把它定義為可控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多邊貿易體系在,這個貿易保護主義是可控的。
從本世紀頭10年的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來看,人們對全球經濟的關注重點已經不是傳統貨物和服務貿易等現行全球多邊規則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問題,而是諸如氣候、環境與貿易、全球經濟信息化與貿易、勞工標準與貿易等充滿挑戰性的新議題。這一新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將使多邊貿易體系出現扁平化的趨勢,貿易規則的磋商、制定和實施將不可能在世界貿易組織單一的政府間平臺進行,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甚至非政府機構將參與到各類與貿易有關的規則的制定過程中來。這種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日益扁平化的發展趨勢將使一國在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中的話語權不但取決于其經濟貿易硬實力的大小,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取決于其駕馭全球經濟貿易規則制定的軟實力的高低。對中國這樣一個新興貿易大國來講,這一發展趨勢有使其在前一輪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確立的比較競爭優勢發生逆轉的危險。中央反復強調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走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就是這個道理。
《南風窗》:所以我們要從“應對”思維轉向“積極參與”思維,積極參與新的貿易規則的協商、制定?
王新奎:現在要制定規則,但制定規則當中你有多少發言權和主導權?比如,我們不能說碳關稅是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我們就不參與相關規則的制定,因為這是一個全世界的共識,要考慮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總體上我還是很樂觀,因為它和我們國家的發展趨勢相一致。我們從1986年爭取加入關貿總協定,到2001年加入WTO,這個過程和我們經濟的高速增長一致,所以我們獲得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第二輪的發展趨勢,又和我們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相一致。所以一定要通過擴大開放,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把全球多邊貿易規則的形成作為一種壓力和動力推動我們改革開放,這才是唯一出路。
在參與新的貿易規則制定上,應該說,我們會越來越積極,但我們也不能做我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難題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將是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貿易國就要承擔更多責任。這對我們壓力很大,我們實際的能力和表觀統計數據所反映的能力不匹配。所以,我們承擔責任也好,參與制定規則也好,需要實事求是,客觀評價自己。從增強軟實力開始,切切實實做工作,加速推進改革開放。
(沈翀一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