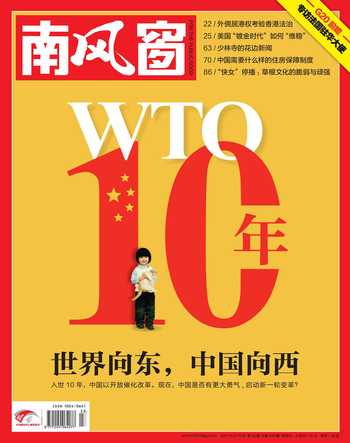從單純接軌國際到推動規則演化
梅新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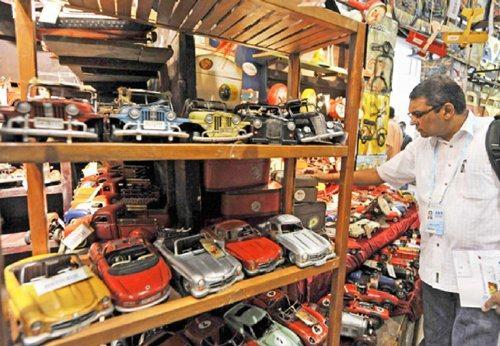

為什么要入世?
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之初國內資源不足,市場狹小,倘若僅僅面向國內市場生產,必然遭遇規模不經濟問題,這一點決定了中國必須開展大規模出口,依靠更廣大的國外市場實現生產的規模效益和高速增長。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苦于國內市場狹窄和資本積累不足,由此常常對一個能以平等身份進入的國際市場及其象征機構—關貿總協定(即現在的世貿組織)表現出比發達資本主義大國更為濃厚的熱情。早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宣布取消對華全面貿易封鎖、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以平等地位進入國際主流市場之時,周恩來總理就安排人員研究是否加入關貿總協定。只是因為研究結論是當時加入弊大于利方才作罷。其后,從1986年到2001年末,中國“復關/入世”談判歷時近15年之久方才完成,“談得頭發都白了”(朱镕基語)。
那么,我們付出如此重大努力換來的入世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何種利益與沖擊?對外部世界影響如何?時至今日,中國入世將屆10年,無論是對中國本身還是貿易伙伴,此舉的收益和沖擊都已得到了足夠充分的展示,評說正當其時。
就總體而言,可以判斷,入世10年以來,中國及其貿易伙伴走上了雙贏之路。
“入世效應”的噴發
對于中國而言,入世意味著中國對外經貿贏得了更可預見的發展環境,從而推動中國對外經貿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皆然,尤以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規模加速擴張表現搶眼。
更大規模的出口,更高的出口增速,意味著出口部門為中國國民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意味著中國產業贏得了更大的規模效益和更多的高成長機遇,因此有更大的概率鑄造非價格競爭優勢,超越曾經不得不高度依賴的價格競爭策略和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之類“優勢”。
出口貿易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得以徹底擺脫鴉片戰爭前夜以來困擾中國160年以上的國際收支逆差壓力,籠罩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頭頂的貨幣危機陰云散去,中國宏觀經濟由此贏得了良好的穩定性。雖然目前持續巨額貿易順差和天文數字的外匯儲備貌似已經給我們帶來了眾多困擾,但我們必須明白,胖子的煩惱與營養不良者的煩惱有著本質的不同。
出口貿易的持續高速增長,直接拉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2002~2010年間,始于西方國家IT泡沫破滅沖擊余波蕩漾之際,后來又遭遇次貸危機—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沖擊,而且一直遭受初級產品行情持續高漲的壓力,中國GDP增長率在這9年中仍然有5年超過10%,另外4年增長率也全部在9%以上。
就總體而言,入世之后中國國內產業遭受的沖擊不如入世前普遍擔憂的那么大。典型如汽車工業,入市前普遍擔憂這是面臨沖擊最大的制造業,實際結果是中國至今已連續數年位居世界最大汽車生產國和銷售市場,汽車產品出口突飛猛進。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重要原因之一是經過50年發展,到入世之時,中國國內市場規模已經躋身世界前列,這種“大國效應”使得企業界將生產集中于中國國內比進口更有利。
同時,也正是對“入世”后中國外向型經濟前景的樂觀預期推動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猛增。入世前夕的2001年,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排名第六位,2009年以來已經穩居世界第一,這為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贏得更大談判能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而加快改善中國在國際經貿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我們已經開始看到了這個趨勢。
毋庸諱言,中國對外經貿現狀多有不如人意之處,國內增值率較低,環境污染,出口企業勞工權益問題……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正視并努力解決。但無論我們為取得這些成績付出了多少代價,我們只能在以往成績的基礎上尋求突破和提升之路,不應也不能推倒重來。
10年后,對外開放的邊際效益開始遞減
入世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里程碑,但無需否認對外經貿發展、經濟開放度提高將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一系列沖擊和挑戰,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足夠警惕。而且,如果說原來建設開放經濟的重心是我方擴大對外開放,那么現在我們越來越需要向我們的貿易伙伴提出開放商品、投資市場乃至人員流動的要求了。正因為如此,筆者反對繼續使用“擴大對外開放”提法,主張改用“建設開放經濟”、“建設開放型經濟”之類提法。
改革開放初期,經過東西方陣營相繼推行近30年的封鎖,我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不多,當時海外的市場開放度已經足以讓我們規模尚小的對外貿易騰挪,除了港澳一帶的窗口公司之外我們談不上有上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無需動用我國有限的外交資源要求貿易伙伴進一步顯著擴大對我國商品和投資的開放。
也由于當時進口和引進外資規模甚小,對外開放商品、投資市場的副作用也還無從體現,更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引進海外資本以彌補資本和外匯缺口,引進先進技術裝備提高我國產業體系裝備水平,引進部分新式消費品滿足實行高積累路線20余年之后國民爆發的消費需求。因此,彼時僅僅強調“擴大對外開放”,已經足以增加我國從國際經濟體系中之所得。
時至今日,我國國內資本積累數量已能滿足需求,外匯缺口已成歷史,對外開放商品、投資市場的副作用(或者說我們必須為此付出的代價)已經非常明顯,即對外開放的邊際收益遞減而邊際成本上升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我們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給、銷售市場、投資市場)已經相當可觀,并且還在快速增長,貿易伙伴對我國商品、資本的開放度也屢屢觸及天花板,此時片面強調“擴大對外開放”無異于僅僅給自己施加約束,卻不要求貿易伙伴承擔任何向中國開放采購、銷售和投資市場的義務,因此并不合適,也有損外經貿主管部門在本國國民中的聲望。
但我們也要看到,入世10年來,中國經濟規模和宏觀調控能力已經成倍擴大增強,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意味著中國以間接調控手段化解外部沖擊的能力已經成倍提高。如同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所一再證明的那樣,中國絕不是外部沖擊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日益強有力的主動調控者。
與貿易伙伴共享繁榮
入世對中國利大于弊,這一點世人有目共睹,以至于國外不少人稱中國為19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國入世對貿易伙伴的影響如何?
毋庸諱言,海外在“中國外經貿增長對貿易伙伴的負面影響”這個話題上對中國頗有非議,某些輿論指責來自中國的競爭擠垮了進口國本土產業,使進口國產業結構趨向“非工業化”。這類指責以前僅僅來自發達國家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已經擴散到某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及先進制造業部門。
在某些論者筆下,中國似乎成了一頭貪婪積累貿易順差的怪獸,卻不肯為貿易伙伴創造機遇,但這種描述與事實相去甚遠。事實是在出口貿易空前擴張的同時,中國進口增速同樣領先世界。時至今日,中國不僅是世界頭號出口大國,也已經躍居世界第二進口大國。
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內消費連續10年保持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增幅,這一切為中國創造了旺盛的進口需求,而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又確保了中國的進口支付能力,從而使中國得以憑借強大進口能力帶動貿易伙伴經濟增長,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果實。
早在入世前的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就發揮了東亞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在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的穩定器作用進一步擴展到東亞之外。
美國實體經濟許多部門還在2008年以來次貸危機的余波中徘徊,農業部門則早已在出口拉動下步入繁榮,預計其今年出口可達1350億美元,比去年增加268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順差可創造475億美元的紀錄,比去年增加120億美元。而美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極在于亞洲,在亞洲的頭號增長極又是中國,以至于中國已經超越加拿大和墨西哥,躍居美國農產品頭號出口市場。
2009年,世界進口萎縮24%,中國進口只下降了11.2%。正是中國強大的進口需求又帶動多個國家和地區較快走出了蕭條,以至于在德國這樣的歐洲經濟火車頭,2009年下半年以來奇跡般的經濟復蘇也被不少輿論稱作是“中國制造”的。
與此同時,作為全世界最引人矚目的新興對外投資大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社會的拉動作用正日益顯著。在越來越多的東道國,中國投資得到了熱烈的擁抱;即使在對中國投資懷有更多政治猜忌的某些發達東道國,大開門戶迎接中國投資的呼聲也日益看漲。且不提多少發展中國家總統、外長向駐華大使面授機宜,“衡量你在中國工作業績的標準就是看你招攬來多少中國投資”,就是美國自治邦北馬里亞納群島,其總督也表示愿意向中國出租島嶼,招攬中國投資。
隨著中國國內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大面積提高勞動者工薪收入;隨著中國發展海外直接投資與隨之而來的產品返銷,中國對相當一部分制成品的進口還將持續快速增長。
中國進口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增長并非自由放任的產物,而是離不開政府相關政策的積極推動促進。中國早已結束了迫于外匯缺口壓力而不得不“千方百計擴大出口”的年代,轉而追求進出口貿易均衡增長,中國最大國際貿易交易會—廣交會的正式名稱已于2007年4月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改成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中國還在陸續制定實施一系列新的進口促進政策,擁有技術、質量、價格和服務優勢的貿易伙伴在中國市場上擁有日益廣闊的前途。
迄今,中國已經同16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簽署了10個自由貿易區協定,同129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同96個國家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中國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國資源持續推進工業化,中國也愿意通過進口、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讓貿易伙伴贏得機會分享繁榮;我們希望其它國家投桃報李,對中國人員、商品和資本給予更公正的待遇。
盡管存在爭議,中立客觀的觀察者都不會否認貿易伙伴受惠于對華貿易發展的事實。在各個進口國,保護主義政客們也不要誤以為靠敲打中國聚攏的人氣有多么堅實可靠;多數普通居民們即使表示贊賞他們主張限制中國制成品進口的激烈言論,但一旦走進超市“用錢包投票”時,他們還是會優先選擇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
我們無須諱言與貿易伙伴之間存在某些利益摩擦,要不然中國也不至于自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以來一直“蟬聯”各成員方反傾銷最大目標國,從2006年起又連年成為反補貼調查最大受害國。但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希望各貿易伙伴國能著眼于長遠利益,客觀評估對華經貿利害得失,與中國共同努力為國際經貿發展開創更可預見的發展環境,增進各方福利,中國愿與貿易伙伴共走雙贏之路。
創造更公正合理貿易發展環境
中國是近20年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而入世雖然總體上大大減少了中國貿易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但并未能夠完全消除,而且還把某些不平等待遇合法化了,這一點我們毋庸諱言,但需要全面看待。
在理論上,從其前身關貿總協定到現在的世貿組織,其宗旨是通過推動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各國人民福利,其條文開宗明義以無差別待遇為基本原則,各成員方理當享有一致的權利;事實上各成員方享受的權利并不平等,老成員方和新加入成員方之間存在一定落差。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接納新成員方要取得老成員方認可同意,有關條款規定新成員方入世需取得世貿組織153個成員中2/3多數票贊成,但迄今世貿組織一直奉行所有成員協商同意的做法。這樣,在與申請加入的國家和地區談判時,老成員方通常都會提出一系列的條件要價,不僅覆蓋外經貿領域,還越來越多地延伸到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經濟制度領域。這些條件要價往往采取對新成員方享受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權利施加額外限制的形式,從而在事實上形成了對新成員方的不平等待遇。中國入世談判之所以如此長路漫漫,俄羅斯入世談判之所以已經歷時18年仍未結束,關鍵就在于這是權利限制與反限制的博弈。
今年中國在原材料爭端中初戰失利,關鍵又在于《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一條“對進出口產品征收的稅費”規定中國原則上應取消適用于出口產品的全部稅費,盡管《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二十條明文規定,締約方可以為了保證供應國內工業等目的而限制原料出口;但《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一條剝奪了中國的這項權利。
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通常會增強世貿組織老成員“卡”新成員的內在動機,因為在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游戲規則”下,在貿易爭端中尋找外國替罪羊從來就比不無痛苦的內部結構調整更受政客們青睞,原因是前者可以立竿見影,后者遷延時日也未必能夠收效。西方經濟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單邊主義作風更使問題激化。
當年,關貿總協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解決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爭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2、23條確定了通過當事國之間的雙邊協商和包括其它締約國的多邊協調解決爭端的基本精神,后來又逐步發展起一套爭端解決機制,但美國向關貿總協定提出的第一起申訴就沒有嚴格遵守這一基本原則。1948年9月9日,在關貿總協定第二屆大會上,美國拒絕與古巴進行任何磋商,就在大會上強硬地要求古巴立即無條件糾正限制紡織品進口的新規定,并要求大會同意它采取報復措施。所幸的是,大會拒絕了美國的無理要求,決定建立工作組處理這一糾紛,從此確立了工作組/專家組工作模式,至今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所沿用。
對于一個尚不掌握國際經貿規則主動權且迫切需要外部市場的后發國家而言,為了給本國外經貿創造更加平穩可靠的發展環境,在總體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完全可以接受少數不平等條款,忍受一段時間對自己作為世貿組織成員權利的局部限制,畢竟全部得到比得到大部分好,得到大部分比什么都得不到好。
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永遠忍受對自己的不平等條款,大國尤其如此,這就需要新成員在入世之后積極參與新的多邊、區域和雙邊貿易談判,通過推動建立新的、更公平合理的規則,逐步矯正、替代原有的不平等條款。超越單純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推動規則演化”,這正是中國入世以來的新目標,中國在多哈回合全面啟動以來的努力和表現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社會實力對比的變化賦予中國更強大力量以推進上述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