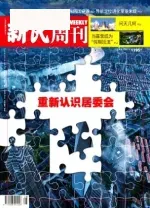誰在干擾法官依法獨立辦案?
游偉
法院審理案件受到各種法外因素的干擾,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也歷來備受社會的關注和詬病。每當有成為“公共事件”的審判不公案例呈現在輿論聚焦之下時,除了法官自身法律專業素養不足的因素之外,人們大多都更看到來自個人或者公權的影子。
人們通常基于生活常識或者工作經驗,強調法官應當堅守中立的立場,做到不偏不倚,因為中國還是一個法治初建的社會,綱常倫理的傳統文化淵源深厚并且不斷地獲得代代傳承。法官也是“人”,似乎也逃脫不了人際之網,而且現在越發講究世態人情,沒有更多的“特別之處”。因此,當審判的職業角色需要他保持客觀、理性并且公正地做出裁決時,人們首先感到憂慮的,自然是法官能不能在履行職務時,真正做到“超凡脫俗”,避免“人情案”、“關系案”,并勇于使自己變得“孤單”,甚至面臨“孤獨”乃至“孤立”。由于世風猶然、無處不在,人們一定可以想象得到這是一件非常艱難,倘若做到了也絕對可算是難能可貴之事。
從另一個方向,為了防范私情的蟻穴掏空法律的長堤,法律做出了不少預防性規定,比如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中都規定了法官審案“回避”制度。雖說飽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還是在不久之前下達了配偶或者子女是律師的法官,必須有條件地實行任職回避的規范性文件,還做出了對人情請托必須書面登記的規定。其目的,無非是想在案件審判和私情往來之間構筑一道制度“屏障”。現實地看,這些規定雖然不可能在生活實踐中完全阻卻已經日益嚴重的“關系案”、“人情案”,但它畢竟增加了“友情”操作的難度,增加了關系案的成本,應該還是會有正面的效果。
然而,法外因素干擾審判,遠遠不止“人情案”一種。根據筆者在基層兩級司法機關工作的經歷,法院內部上下級之間、地方黨政領導等以各種名義“關心”案件,甚至對案件處理進行“批示”的情況,對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審案的影響,比一般人情關系更為嚴重。而且,由于這樣的影響處于“體制之內”,一方面不容易為外界所知,也很少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和監督;另一方面,此類影響又常常借助法院內部事實上的行政關系,具有變相的“強制力”,審案法官更加難以直接抗衡。而法外因素以“群眾關切”、“服務大局”、“化解矛盾”或者“維護穩定”之類的名義介入案件時,法院不得不十分慎重,認真對待。
事實上,長期以來,法院內部尤其是審理案件的法官,一直面臨著來自上下左右、里里外外不時的人情和權力因素的干擾,不少法官忙于應付、“斗智斗勇”、身心疲憊。久而久之,自身都對司法的獨立與公正,產生了信念上的懷疑與動搖,重創了法官的職業尊嚴和獨立品格。這種狀態如果持續不改,必將積重難返,最終必將損害司法的權威,也影響法治建設目標的實現。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的若干規定》,其中明確規定,法院領導干部和上級法院工作人員“非因履行職責,不得向審判組織和審判人員過問正在辦理的案件,不得向審判組織和審判人員批轉涉案材料”。如相關人員因履行職責需要對正在辦理的案件提出指導性意見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或者由案件承辦人記錄在案,同時案件承辦人須將相關文字資料存入案件副卷備查。
筆者在基層司法機關任職時,曾主持探索涉案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對上級法院、黨政機關領導“過問(批示)案件”等情況實行內部登記制度,并實行一月一報。我也了解到不少法院合議庭法官為了“將來說得清楚”和出于“保護自己”的考慮,自行將涉案“指示意見”予以共同記載,以備查考。最高人民法院其實也早在2009年12月發布的《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中就曾規定:“建立健全過問案件登記、說情干擾警示、監督情況通報等制度,向社會和當事人公開違反規定程序過問案件的情況和人民法院接受監督的情況,切實保護公眾的知情監督權和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但真正依照這一規定執行的法院極少,也未見公布過“違反規定程序過問案件”的實例。所以,此次各級法院是否真能排除權力干擾或者對“因履行職責需要”指導案件的“意見”,予以登記入案,恐怕依然有待觀察。
(作者系知名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