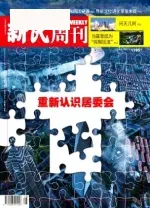微笑比英語更重要
劉迪(東京)

很多日本人認為,日本無法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其原因之一是自己不擅長英文,表達能力低下。
去年夏天,有家在“東證一部”上市的日本汽車零件公司登出廣告,以年薪6000萬日元招聘社長,其首要條件是“擅長英文”。據這家公司負責人透露,該公司決意出走海外,這是他們聘任懂英文最高管理人的理由。
聘懂英文的社長,這其實象征性地體現了日本企業界的憂慮。這20年間,多數日企與全球化絕緣,很多日本人認為,日本無法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其原因之一是自己不擅長英文,表達能力低下。對此,最近有些日本企業開始試行“文化轉型”,例如我們熟悉的網絡銷售集團“樂天”、休閑服銷售公司“優衣庫”的老板最近均下命令,今后公司會議一律使用英文。“樂天”集團最高經營者三木谷浩史更極端,他說,2年后,公司管理層中如還有人不會說英文,那只好讓其走人。
回顧日本近代歷史,這個國家一直存在“英語情結”。例如在明治時代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早稻田大學校長高田早苗都曾主張“英語國語化”。此后這種聲音不絕于耳。最近一次,則是2000年小淵惠三內閣時代。那時小淵曾成立一個叫“21世紀日本構想”的懇談會,討論引進“英文為第二公用語”問題。該懇談會在報告書中提出,提高國民英語水平應作為“日本戰略問題”。這個報告還提出,應讓所有“社會成員”掌握實用英語。不過,因為小淵病死任中,這個計劃也就胎死腹中。
當然,這種“英語公用語言化”浪潮并非沒有阻力。反對聲音中,有些意見也十分中肯,有人說,真正的國際化,并非只是一定要講英文,日本應該兼容并蓄,日本人也應學習其他語言。此外,還有人擔心,假如把英文規定為公用語言,就可能損害日本人的國語能力,甚至可能導致日本文化出現扭曲現象。
那么目前政界、商界中的英語公用語言化動向能否成為氣候?筆者以為,日本今后將堅持更開放的方向,但強制以英文為公共語言的做法卻難持久。這種動向,反映了日本官民對全球化落后現狀的焦慮。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假如真相信“英語等同世界語”這個神話,那么日本企業可能將在世界很多地區遭遇挫折。我們知道,即使是印度這樣一個把英語當作公用語言的國家,其真正能講英文的,也不過總人口的5%。而世界還有更多國家,英文并非其公用語。
另外也有日本學者指出,今天全球以英語為公用語的國家中,多數屬前殖民地國家,一個非前殖民地國家,把自己的公用語定為英語,這將讓全球恥笑。有人指出,今天全球日益崛起的經濟體,多數屬于非英語國家。假如真以為把英語定為公用語,就可解決全球化問題,這必將導致誤判。其實,筆者注意到日本有些跨國公司,采取的是適應各自公司特點的全球化語言戰略,例如小松制造所自2009年規定,該公司第一外語是中文,所有新職員一定要學好中文。
話又說回來,筆者并不認為日本官民在英文學習方面不下功夫。但可以說,日本在英語教育方面的投入產出比十分不佳。日本學生沒什么問題,問題出在他們的教學方法。雖然近年以來日本英文教育有所改進,但文法、應試中心的教育并無大的改觀。因此,日本缺的不是教育投入,而是實踐。日本高中生掌握的單詞,足夠應付日常英文交流,也完全可借詞典閱讀英文社科文獻。說白了,日本缺乏的不是英文教育,而是講英文的需求與環境。但不論日本政府還是日本企業,卻都未發現他們自己到底缺什么。這也可反過來理解,即日本是否真需要那么多國民整天講英文?
對這個問題,有個叫成毛真的日本人說,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英文其實與他們生活、工作并無直接關系。成毛說,真正需要懂外語的,只幾百萬人足矣。目前在世界各地,大約有100萬日本駐外人員,在日本國內,還有100萬左右外企人員。此外,就是國際機場、涉外飯店、出租車司機、餐飲業人員等需要懂點英文,不過在那些服務行業,所需英文水平并不很高。在成毛真來看,對日本服務業人員來說,微笑、手勢可能比英文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