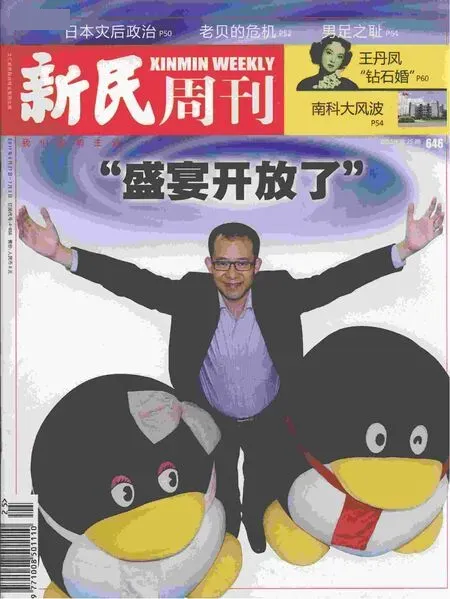向警予:她發起了中國第一場女權運動
王若翰



一雙沒有裹的腳。6歲入私塾, 8歲進入長兄在縣城開創的新式小學,16歲離開家鄉, 先后就讀于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師范和周南女校。21歲,學有所成的向警予本著“救國必先興教育”的思想,在家鄉溆浦開辦了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學堂,為更多中國女性解開了裹腳布。
她,是乳名“九九”的土家族少女,出身商賈之家,也是在家鄉湖南溆浦興辦新式女校的第一任女校長;她,曾橫眉冷對軍閥強權,說出“以身許國,終身不嫁”,也曾在赴法的航船上與革命同仁擦出愛情火花; 她,是為革命慷慨就義的婦女先驅,也是臨刑前面對兒女照片空自垂淚的慈愛母親。
在俠骨與柔情交錯的畫面里,一個有血有肉的女革命家形象就這樣躍然紙上,她是——向警予。
每每提到憂國的志士,總不外乎兩種描寫:慨當以慷的壯懷之舉,纏綿浪漫的愛情佳話。前者將俠義之士區別于庶人,塑造成一座豐碑,供人膜拜;而后者則又將其還原為有些有肉的性情中人,讓讀者從字里行間找到人性的共鳴。
在向警予身上,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一位執著、倔強、富有激情的女性。她喜歡讀《離騷》和《木蘭辭》,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巾幗英雄花木蘭為楷模。以至于說出:“將來我如做不出大事業,我要把自己粉碎起來,燒成灰!”每每這樣激烈地幻想便要大哭一場。在聽說袁世凱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后,她和同學們上街游行、演講,說到激憤處,甚至暈倒在講臺上。
前夫蔡和森在得知其就義的消息后,曾作文悼念,其中提到:“她抱‘獨身主義,要終身從事于教育來改造中國。”于是,這故事就從“獨身”開始吧。
“以身許國”的由來始末
說起革命者的“獨身主義”,曾在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被并稱為“湘江三友”的毛澤東、蔡和森和蕭子升曾共同立下過“終身不婚”的誓言。1918年的一天,三人一起來到岳麓山愛晚亭談古論今。當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毛澤東首先提議為尋求救國真理,甘愿終生不娶。對此倡議,蔡和森、蕭子升深以為然。
有趣的是,之后不過一年有余,蔡和森便與向警予喜結連理。更耐人尋味的是,向警予也曾說過“以身許國,終身不嫁”。而她的這番經歷,確實要比蔡和森更加傳奇。
向警予在家鄉溆浦縣城任校長時,曾被湘西鎮守副使第五區司令周則范看中,想娶她為二房夫人。當時的周則范還算是個新派軍官,但向警予鄙視軍閥的權勢,反對無愛婚姻。可無奈,向父雖是當地富商,但懾于周的威權,不敢拒絕,她的繼母更想借此高攀。豈料,早已接受婦女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竟只身闖進周公館,對位高權重的軍閥丟下一句:“以身許國,終身不嫁”,便挺直著腰桿離開了。
后來,為避免周的再次糾纏,向警予干脆離開溆浦老家,前往長沙,并加入了由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三人組織的“新民學會”。
“向蔡同盟”的愛情佳話
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相識,還要追溯到她在周南女校讀書期間。
一日,向警予正在操場上跑步,遠遠地發現一個小女生健步如飛,竟然跑在自己前面。她不禁暗暗納悶,體育本是自己的強項,怎么還有人比自己更厲害?正想著,這個女生卻向她走了過來, 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紹:“我叫蔡暢,是體育專科班新生,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自此,中國共產黨未來的革命歷史中,兩個赫赫有名的女性就這樣相識了。
通過跟蔡暢的接觸,向警予逐漸了解了她的家庭。蔡母出身名門,仰慕女革命家秋瑾,并以此為榜樣教育子女。而蔡暢的哥哥蔡和森那時已就讀于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
1919年,已經加入“新民學會”的向警予在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隨后,又組織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她同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
在駛往法國的“盎特萊蓬”號郵輪上。向警予、蔡和森兩人經常一起觀看日出,討論學習和政治問題。在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舊式婚姻,主張大膽追求新式愛情和理想的完美結合。經過了35個海上生明月的浪漫之夜,當郵輪停靠在終點站法國馬賽港時,他們倆都驚喜地發現,自己完全被對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愛情之舟揚帆啟航了。
盡管當時的中國社會,把男女之間自由戀愛看成傷風敗俗的事情, 但向警予和蔡和森卻選擇了勇敢地向這種陳規舊俗挑戰,他們毫無顧慮地公開了兩人之間的戀愛關系,用自由戀愛的實際行動沖破了封建包辦婚姻的牢籠。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向蔡”的浪漫愛情無疑是悲壯氣氛里的一抹亮色。
1920年5月,向蔡二人在法國蒙達尼市法文新司學校的一間木板平房里舉行了婚禮。當著幾十位中國同學,向蔡二人共同朗誦了他們編寫的《向上聯盟》,還將戀愛中互贈的詩作編印成書分贈給大家,結婚照上則是兩人共同捧著一本翻開的《資本論》,寓意二人結合的共同信仰是馬克思主義。
婚后,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這樣寫道:“我與警予有一種戀愛上的結合。”收到來信的毛澤東極為高興,于1920年11月26日致信說:“以資本主義做基礎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絕對要不得的事,在理論上是以法律保護最不合理的強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我聽得‘向蔡同盟的事,為之一喜,向蔡已經打破了‘怕,實行不要婚姻,我們正好奉向蔡做首領,組成一個‘拒婚同盟。”
盡管信中所說的“拒婚”,是指反對舊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愛情結合,不過,因一樁革命婚姻而引出“拒婚”一說,這也絕對是“前無古人”了。那時的蔡和森還在法國的豆腐公司打工,向的繼母聽聞二人婚訊,還一度氣急敗壞地諷刺向道:“現成的將軍夫人不做,卻去找個磨豆腐的!”
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為領導留法學生爭回里昂大學的入學權的斗爭而得罪法國當局,被強行遣送回國。不久,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國。1922年的4月,向警予夫婦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取名“蔡妮”。同年,向警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僅僅幾年的時間,他們夫婦倆就迅速成長為中國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的革命人物。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核心成員,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員,杰出的婦女運動領袖。夫婦倆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共同投身于革命事業,這在黨的早期奮斗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何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向蔡同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向蔡同盟”的佳話在黨內和許多進步青年中也迅速地傳播開來。
“女權主義”的倡導先驅
為花季少女解開裹腳布,為廣大婦女爭取參政權,為底層娼妓尋求獨立人格;誰說我輩不女權?
在蔡和森寫的《向警予同志傳》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自與和森戀愛及參加實際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種壓迫,以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來,仿佛是‘奇恥大辱。同志們愈說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個,她便愈不滿足。”
“婦女解放”是向警予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她與蔡和森自由戀愛結婚,后來這段婚姻又因二人生活習慣不同,以及向與當時中央宣傳部長彭述之的一段感情而宣告結束,這段感情經歷已經將向警予其人區別于拘泥封建禮教和世俗之見的尋常女子。
其實早在溆浦新式學堂開辦之初,她就和自己在周南女校讀書時的好友吳家瑛背著干糧,走進溆浦山區,一家一戶地給家有學齡女孩子的家長們做工作,以自己打破溆浦不準女娃入學舊俗的親身經歷,勸導父母們讓女孩兒接受教育。當時,婦女纏足的陋習在中國依然存在,向警予在任校長期間,曾親手為學生解開纏腳布,并陪同學生回家,向其父母闡述不裹腳的道理。并在教學期間,多次提及“男女平權”的概念,勇敢地向束縛了婦女幾千年的封建勢力發起挑戰。

1922年7月,在黨的二大上,向警予當選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撰寫大量文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中國婦女問題,號召廣大婦女團結起來,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
縱觀向警予的“女權”道路,既有為思想守舊的封建家長“普法”的執著,更有向中央上級爭取婦女權利的倔強。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北上前發表宣言,接受中共的“國民會議”主張。孫中山號召召開各實業團體、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等九個團體的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預備會,但沒有包括婦女團體。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層浪,婦女界要求參政權的運動開始如火如荼的進行。為了促使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 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等21個婦女團體成立“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她還在《婦女周報》上發表了《國民議會與婦女》一文,文中寫道:“本會的目的在促成國民會議,和參加婦女獨立的團體于國民會議。”
“婦女與男子不過性的區別,而其國民身份則無二致。”透過此話,可以想象發聲者是以一種怎樣高昂的姿態,為其所代表的廣大婦女爭取權益。
如果說為女性爭取受教育權利和參政權利,是在積極的方面做楷模,那么1923年,向警予一次關于娼妓問題的演講,則是在直面女性問題中的毒痂。
在演講中,向警予完全跳出封建倫理道德桎梏,對從事娼妓職業的女子不帶任何鄙夷和譴責。她指出:“娼妓制度不但辱沒女子的人格而乃人類共同的恥辱。至于娼妓本身所受種種無人道的殘酷,大家也可想象而得。”又提出:“娼妓制度所以存在的原因雖然復雜,而經濟一項實為主因。……我的意思還是從經濟上謀解決,一面運動廢娼,一面要做婦女的職業工作。”
面對毒痂,勇敢揭露并施以創藥,此為上上之策。由此可見,向警予的“婦女解放運動”已逐漸形成了一套詳盡完備的體系。
“殺身成仁”的壯懷激烈
1927年的武漢,是白色恐怖與紅色力量角逐的旋渦中心。由于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先后背叛革命,導致革命統一戰線破裂,國民大革命失敗。面對如此岌岌可危的政局,向警予卻婉拒了黨中央讓其轉移的提議,繼續留在武漢團結工人階級,宣傳革命精神。
據一位當時在武漢的工人回憶:有一次,黨中央派人來,通知向警予趕快轉移。向警予說:“我知道反動派對我很注意,可是武漢的工人需要我,多留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我請求黨中央,讓我留下來!” 后來,中央經過反復考慮,同意了向警予的請求,讓她擔任黨的地下刊物《長江》的主編。
在革命的洪流中,有中流砥柱的真正革命者,也有貪生怕死的懦夫。向警予在武漢擔任地下黨期間,負責地下交通員的宋若林在面對死亡的威脅時,表露出的是怯懦、背叛。
在出賣了夏明翰之后,宋若林親眼目睹了夏明翰慷慨就義的一幕,邪惡的槍聲擊碎了他的膽魄,很快,他又供出了向警予的住所。就在夏明翰就義的同一天,宋若林帶著一群武裝匪徒沖進了向警予居住的小樓,把向警予帶到了法國巡捕房的拘留所,一同被捕的還有其助手陳恒喬。
之后的幾天里,向警予被捕的消息,在國民黨反動派所辦的眾多刊物上被登載。其中,上海的《申報》甚至將“拿獲共黨要犯向警予”的標題放入了“國內要聞”。
武漢的早春,寒意料峭。而在法國巡捕房由鋼筋和水泥構成的拘留所中,陰森森的鐵門似乎永遠透不進陽光。只有指尖觸碰到貼身衣袋中一雙兒女的照片時,向警予的心里才會涌起一絲暖意,隨即,又是深深的苦楚。“妮妮、博博,媽媽再也看不到你們了。”被抓進來十來天了,向警予只被提審過一次。
在那次審問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著用流利的法語質問租界當局:“這里是中國的土地,你們有什么權利來審問中國革命者?你們把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忘記了嗎?你們法國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愛嗎?不是說信仰自由嗎? ”
無畏的革命精神令法國領事對向警予心生敬佩,并向當局提出:作為政治犯不該引渡。然而,法國殖民當局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畢竟串通一氣,隨之撤換了領事并將向警予交給國民黨桂系軍閥。
向警予就義的日子,正是1928年的5月1日,國民黨反動派選擇在這天處死向警予,意在打擊全國的工人階級武裝革命者。5時5分,牢門打開,一匪徒大聲喊叫向警予的名字。向警予神色自若,嘴角掛著微笑,從容走出牢房,身著在法國結婚時穿的油綠色旗袍。
去刑場的路上擠滿人群,向警予奮力高喊,做了最后一次演講:“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向警予,為解放工農勞動大眾,革命奮斗,流血犧牲!反動派要殺死我,可革命是殺不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動派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憲兵慌忙撲上去,拳打腳踢,不許她開口。向警予掙脫束縛,頭一昂,奮力高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
殘暴的匪徒掐住向警予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塊塞進她的嘴里,又用皮帶縛扎她的嘴巴和雙頰,阻斷她的喊聲。血,從她嘴角流出……
武漢,余記里空坪刑場。槍聲響了。向警予,年僅33歲。
后記
當晚,海員工人陳春和冒著生命危險,用小船將向警予的遺體運過漢江,掩埋在古琴臺對面的六角亭邊。
1928年7月22日,蔡和森聽聞向警予就義的消息,在莫斯科寫下了悼念向警予的《向警予同志傳》。當時,“向蔡”二人已離婚兩年,但在文中,蔡和森言辭真摯,催人淚下,其中有一句寫道:“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上,高度評價向警予革命的一生,說:“大革命時代犧牲了的模范婦女領袖、女共產黨員向警予,她為婦女解放、為勞動大眾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