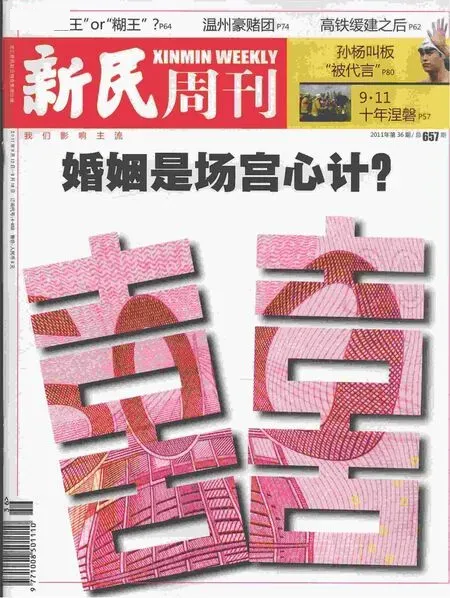十年反恐,安全了嗎?
邵樂韻

“9·11”恐怖襲擊的主要策劃者本·拉登已被擊斃。但是,沒人敢說美國反恐取得了徹底勝利。隨著“9·11”十周年紀念日臨近,美國各地反而“草木皆兵”了。
9月3日,美國國務院發布全球旅游警告,呼吁僑居國外或在外旅行的美國民眾保持警戒。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納波里塔諾表示,沒有確切或可信情報顯示,“基地”組織計劃在“9·11”事件十周年發動恐怖襲擊,但美國仍應保持高度警惕。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發布全國警告,“基地”組織可能利用小型飛機實施恐怖襲擊。
十年反恐,美國是否比以前更加安全?
從全球轉到本土
今年6月29日,美國政府公布了新的國家反恐戰略,“基地”組織及其分支和追隨者被定位為對美國最為重大的直接威脅。此外,美國土生土長的恐怖分子也是打擊重點。奧巴馬的國土安全及反恐事務顧問布倫南在宣布反恐新戰略時說,這一戰略標志著美國首次將本土作為反恐努力的最重要“戰場”。
布倫南還表示,在未來的反恐戰爭中,“最好的進攻并不總是向國外部署大規模軍隊”,而是對恐怖組織進行定點的、“外科手術式”的行動。
從小布什執政時期的“全球反恐戰爭”到奧巴馬的“本土反恐行動”,這既是對美國十年反恐作戰的全面總結,也是針對近期全球恐怖形勢變化所作的最新調整。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張家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回顧了美國的反恐政策演變。他說,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的反恐戰爭側重海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阿富汗戰爭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主要表現為打擊塔利班組織,以報復國內所受到的威脅;其次強調國際合作,組織同盟打擊恐怖主義。
第二階段是伊戰爆發,這也是小布什與整個世界走向分歧的起點。其反恐政策仍以戰爭為主,但是更多體現單邊主義色彩,咄咄逼人——反恐已經不光是美國的目標,而成為其重塑世界格局、實現政治戰略的推手。
然而整個國際恐怖主義形勢從2005年開始惡化,已被控制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勢急轉直下。到2007年初,小布什認識到反恐戰略的局限性,想從伊拉克逐步撤兵,與伊政府簽訂了撤軍計劃表,后被奧巴馬政府繼承。
張家棟說,2008年奧巴馬上臺后,“放棄了‘戰爭的概念,也基本不提‘反恐一詞,而用‘反極端主義等類似說法來代替,意為反恐降溫。”小布什曾提出口號“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都是美國的敵人”,這在奧巴馬看來,無疑是引火燒身——有些地方的恐怖組織并不反美,把全世界恐怖主義都作為自己的打擊目標,是平白樹敵。另外,即便是塔利班組織,也分極端派和溫和派,對前者要打擊,對后者則可談判。
過去兩年,國際社會和學術界對全球恐怖主義形勢也有了新認識。張家棟說,過去的視角是自上而下,把恐怖主義視為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通力合作應對威脅;但是現在很多國家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并非全球化,而是當地化、碎片化的,因此要用自下而上的視角來看。恐怖主義的新轉型逼迫各國地區跟著轉型,從關注國際到關注國內,從強調國際合作到強調國內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之間的合作。
美國反恐態勢的收縮也與本土的經濟和財政壓力有關。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機構(CRS)的計算,自2001年9月11日至2011年5月1日本·拉登死訊被公布的近10年時間里,美國已經為這場反恐戰爭付出了近1.3萬億美元。也有經濟學家估計,實際花費可能高達2.5萬億美元。
盡管反恐戰爭給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帶來了收益,但畢竟也損耗了美國的國力,加上一場金融危機的洗蕩,引發諸多社會內部矛盾,讓美國不得不攥拳收勢。在2012年總統選舉之前,奧巴馬的重中之重就是保證美國本土不會再遭恐怖襲擊。
未來潛在挑戰
“9·11”事件發生后,《今日美國》和蓋洛普民調機構工作人員連續十年對美國民眾進行了相同的民調測驗,主要問題包括:是否相信“穆斯林國家覺得美國是自己的敵人”、是否對美國政府反恐能力充滿信心、以及是否認為美國是反恐戰爭的勝利者等。
綜合調查結果顯示,2002年3月,71%的人認為“穆斯林國家覺得美國是自己的敵人”,最新數據為55%;“9·11”發生后不到一周,41%的人表示“非常信任”政府可以保障公民的安全,而現在則僅為22%;“9·11”后一個月,42%的人認為美國和其盟友將獲得反恐戰爭的勝利,期間民眾信心雖有滑坡,但最新統計仍回到42%,與十年前相同。
對“穆斯林”的恐懼和誤解,也顯示了這十年來,文明沖突依舊未解。雖然奧巴馬上任之初就欲積極緩和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然而,美國本土的“穆斯林恐懼癥”卻一次又一次置他于尷尬境地。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的報告也稱,“疏遠美國穆斯林社區不僅威脅宗教自由,也傷害了我們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
有人形容,接下來,是“一個國家對一種意識形態的戰爭”。張家棟說,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這也是奧巴馬極力想避免的。他在新的國家反恐戰略中措辭非常謹慎,沒有提到“伊斯蘭”或“穆斯林”的詞匯,想和這個群體修好,但是遭到了美國右翼勢力的嚴重抨擊。從過去的傳統看,美國走的不是與穆斯林合作的道路,“奧巴馬想走,但我認為他行不通”。
張家棟分析,目前美國國內有兩大趨勢比較危險,一是本土極端分子針對本國人的恐怖活動有增多趨勢。“一些美國的宗教極端分子到海外接受恐怖主義訓練,比如有新聞說9個也門裔的美國高中生跑到也門接受‘青年黨的培訓,這對未來的美國可能是潛在的威脅。另外,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使得美軍中的穆斯林軍人產生‘思想分裂,按照伊斯蘭教義,他們不能開槍打自己的穆斯林兄弟,但在戰場上,他們必須對抗宗教極端分子。”
另一個危險趨勢是在經濟因素、移民因素等影響下,美國國內極右勢力發展迅速。“極右勢力反左翼、反民主黨、反黑人,美國目前是民主黨當政,又是黑人總統,加上政壇上茶黨崛起,將來如果處理不好,可能出現極右恐怖主義浪潮。”
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張國慶在其新作《被折騰的世界——這十年美國攪動世界的背后》中提到,反恐更要反貧窮。他說,“雖然美國財政部的官員一再否認貧富差距與恐怖主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但沒有人可以否認,在很大程度上,貧窮所帶來的絕望與幻滅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而“對大多數國家來說,人們關心的不是伊拉克政權的更換,而是要為恐怖主義以及滋生恐怖主義的世界環境找出答案,因為這種不平等、經濟控制和咄咄逼人的世俗唯物主義的環境顯然是造成發展中國家不穩定的因素。”
他強調,美國發動了伊戰,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放緩了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圍剿,等于是放虎歸山;華爾街貪婪和政府失察導致的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了貧富差距,為恐怖主義送去了更多的“旗幟”……唯獨在加強國際合作、南北對話,以及改變不得人心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方面少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