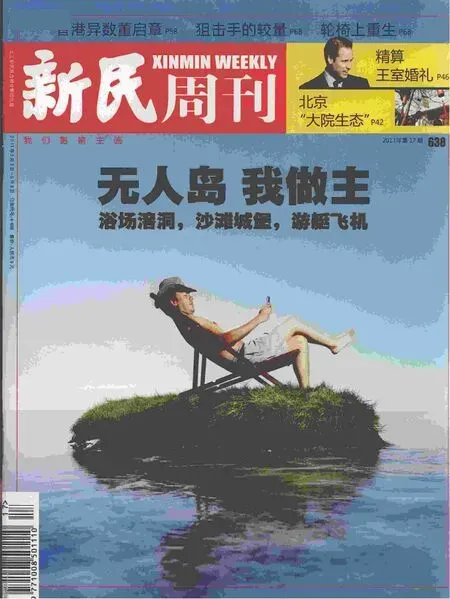一句伏爾泰從未說過的“名言”
鄭若麟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據說這句話是伏爾泰的“名言”。然而最近在法國,伏爾泰的這句“名言”再度被確認是誤傳!伏爾泰從沒說過這樣的話,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思想!
但這句話流傳如此之廣,甚至在伏爾泰的祖國法國也被奉為“至理名言”,因此中國人誤解也是可以諒解和理解的。最早提出這句“名言”的,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引用了這句話。后來又在另一本書《書信中的伏爾泰》中再次引用。但此后霍爾明確表示,她“綜述”了伏爾泰的思想,依據是“愛爾維修事件”。伏爾泰并不喜歡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所寫的《論精神》一書,稱之為“一堆毫無條理的思想”;但當這位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的書出版后倍受教會和當局攻擊之時,伏爾泰又為之辯護。于是霍爾在評論這件事時寫道:‘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從此便成了他的一貫態度。”,她“錯誤”地將這句她自己的評語加上了“引號”,結果使后人以為這是轉引自伏爾泰本人的話。霍爾自己后來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認是她“誤”將這句話放在引號內而導致讀者誤解的。日內瓦伏爾泰博物館館長夏爾·維爾茲曾在1994年在一次電視采訪中重提這件事,以證明伏爾泰確實從沒說過、寫過這句“名言”。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題為《法蘭西名言錄》的書中再次提及這句話。書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國的猶太翻譯家諾爾貝爾·古特曼。古特曼在書中寫道,這句話是伏爾泰在寫給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現的:“教士先生,我討厭您所寫的文字,但我不惜獻出生命,也要使您能繼續寫文章。”問題是,盡管這封信確實在歷史上實有其事,但在伏爾泰的原信中卻并沒有這樣一句話,甚至連這樣的意思也沒有。
法國最近之所以出現對伏爾泰的質疑,是因為這句“名言”近來成為法國許多極右言論、特別是排外、仇外、種族主義等言論的擋箭牌。一些過去不能說的話,今天卻在這句“名言”的掩飾下紛紛出籠,沖擊并影響著法國社會向極右方向急轉。如著名電視記者艾利克·齊姆爾最近就公開表示一個企業主“有權”讓職業介紹所不要推薦黑人和阿拉伯人。好幾家人權組織聯名起訴齊姆爾“種族歧視”。齊姆爾的“粉絲”們正是以伏爾泰的這句“名言”來為其辯護。巴黎極右翼國民陣線新任主席瑪麗娜·勒龐(前主席讓-瑪麗·勒龐的女兒)就是在這種思潮的簇擁下,在民意測驗中得分節節高升,甚至大大超越現任總統薩科齊……正是這股思潮引起的政治動向,導致法國對“絕對言論自由”的反思甚至“反動”,并連帶出現對伏爾泰這句“名言”起源的追究、質疑和否定。
這句捏造的“名言”關鍵在于將言論自由絕對化。實際上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國都是有界線的,這個界線就是法律。在法國有“蓋索法”和“亞美尼亞大種族屠殺法”以及“布雷凡納法”,這些法律都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法律限制。齊姆爾最后被判有罪,根據就是這些法律。由此可窺,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應該存在。你甚至可以批評法律本身,甚至可以認為這是“惡法”。但當法律仍然有效時,你的言論卻不能違反法律。任何人言論一旦違法,法律就必將制裁。任何國家都無例外。
事實上,伏爾泰本人也從來沒有“誓死捍衛”過他人的發言權利。法國研究伏爾泰的專家們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伏爾泰非常討厭巴黎《文學年代》刊物創始人艾利·弗雷龍。此君文字尖刻,常常攻擊當時的文學家和哲學家。伏爾泰對其一直難以忍受,甚至專門寫了一出諷刺劇來挖苦他。該劇如此之刻薄,以至于前來觀劇的弗雷龍夫人當場被氣暈。伏爾泰的朋友們最終動用他們在政府的關系,多方攻擊弗雷龍,甚至一度將其投入巴士底獄。最后弗雷龍的老板、伏爾泰的朋友拉莫永·馬雷謝爾伯決定解雇弗雷龍并讓《文學年代》停刊,伏爾泰這時卻并沒有“誓死捍衛”弗雷龍說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