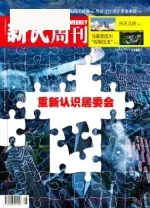穿越海螺迷宮
扭腰客
古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用一根絲線拴住一只準備穿越海螺的螞蟻,而在海螺的出口處用蜂蜜來引誘這只螞蟻,從而很快找到了海螺迷宮的出口。而法國學者雅克·阿達利曾總結:我們這個現代世界的特征正在返回古希臘迷宮時代。誠然,現代各種公路鐵路、空海航線、寬帶光纖甚至人際關系,各種音樂繪畫、文學科學,甚至電視電影,都或多或少呈現出古文明中宗教與神話對海螺、牽牛花、城邦建筑以及女性子宮的探索。而于讀者來說,張大春這一套信息量巨大、隨手一翻就活色生香的《城邦暴力團》,無疑也是一座海螺迷宮。
張大春寫小說的本事,是沒有人懷疑的。可是張大春為什么要寫武俠?我們是不缺武俠的。往前有金庸古龍黃易,現在網絡興起,各種魔幻武俠、穿越武俠又比比皆是。北大有那么幾個教授,松松口研究了一下金庸,已經被罵得狗血淋頭,這“武俠”的水,就更沒幾個人敢趟了。可沉下心來翻看了一兩章,馬上推倒了最初的質疑:我們又是很缺武俠的。起碼張大春這種“武俠”,是我們前所未見的。
總有人拿張大春的小說寫法說事兒,各種批評中頻率最高的一個詞:炫技。這種書袋滿篇、典故遍地的寫法,其實最容易招來非議。叫板的人梗著脖子:他張大春又不是卡爾維諾、艾柯、博爾赫斯,憑什么這么寫?乍一看是挑釁,實則在叫板中將他與大師相比,早已暗含褒揚。
陳丹青就十分贊賞張大春,說他既有傳統又十分現代。確實,看他在書里八卦淞滬抗戰、桐油借款、黃金運臺等近現代秘聞,宣講各種國學典故、江湖段子,實在過癮。他似乎是將《城邦暴力團》當做一部詞典來編纂。你完全可以像查詞典一樣去讀,按次序分門別類來看也好,隨手亂翻顛倒錯亂也好。你讀的次數越多,也就越容易發現其中的樂趣。
以往武俠小說主人公,要么是失意落魄的情種,要么是背井離鄉的異人,歷經苦難與屈辱,機緣巧合,成就傳奇。張大春也沒有刻意跳出這個模式,只是他筆下的一個個人物,無論是孫小六,還是萬老爺子,瞧著實在并不很像“武俠”。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這么寫,反正一番城邦暴力,一番觥籌交錯,讀者接著理所當然要期待一番酣暢淋漓,可是最后卻發現,張大春居然把終結故事的權力還給了讀者。他壓根也不想寫一部五十五萬字的大團圓,他可是職業小說家,太了解讀者了。他知道:只有創傷與失敗的傳奇,才能引起世人窺視時的快感。
王家衛在他的電影里說:人,最大的煩惱就是記性太好。而遺忘過去的途徑無外乎兩種——頓出與漸出。頓出就是與過去一刀兩斷,雖然殘忍,卻干凈利索。漸出則是依靠時間,在漫長的歲月中讓傷口慢慢愈合。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漸出的那種。我們只是偶爾會想起自己過去曾經為之煩躁的童年,為之痛苦的愛情,甚至是為之犧牲的時代。糾結于當下的現在的各種忙碌、欲望和焦慮中,我們就像海螺里迷路的螞蟻。
張大春一定有感于當代人群渾渾噩噩的生活狀態,所以他這樣說:“小說家不是一輩子就寫故事給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幫助我這一代人,撿回被集體糟蹋掉的訓練及教養。”不讀歷史,一個人的知識再豐富也是亂的。身為島上的第二代“外省人”,張大春身上似乎天然地有一種對往事與歷史的尊敬。于是看他在現時代揮舞著一支舊筆,借武俠的外殼淘洗歷史,用滿篇的歷史做主線,用情懷與修養做蜂蜜,悄然撥開茫茫長夜里這一團團繁復的煙霧,將我們引出迷宮。
中國近代有無數偉大和慘痛的事件,有無數悲壯和荒唐的傳奇,卻從沒有一個作家有機會、有能力、有意志,去寫一本完整的、神圣的,可以代表一個民族良知和情懷的巨著。有故事的人再也不愿意動筆,沒故事的人卻在狂吹牛皮。也許這不是文人的錯,更不是文學的錯,只能歸咎于時勢殘酷、人性脆弱。我不能違心地說《城邦暴力團》就是一部中國百年未有過的歷史與人性的巨著,那太虛偽了。可是我很感激張大春,他用五十五萬字做了一次有趣的嘗試。
很高興能夠在《城邦暴力團》的迷宮里做夢、幻想、顛倒、迷失,并且最終成為一只走出海螺的螞蟻,這感覺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