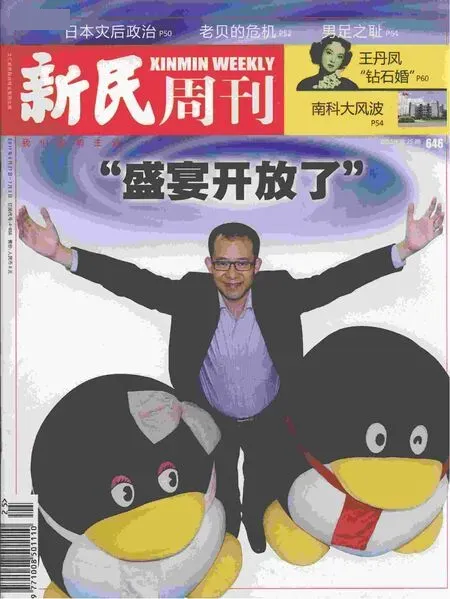晚清“情人”
夏烈
這是一部文藝大片的標題。封面上煽情的男人的側臉與背后天高地闊的中華帝國的宮闕,似乎也明示這是一種大片式的敘事——晚清,跨國,情人——我喜歡這個封面和書名,但暗暗訕笑作者趙柏田和出版方世紀文景也深諳標題黨的策略!這些,都是閱讀之前的揣想。
閱讀,卻顛覆了我膚淺的想象。我開始覺得《赫德的情人》這書名大有深意。它是一個中國套盒,至少嵌合著幾層意思,使“赫德的情人”這一詞匯出現了有趣的象征意味。換言之,赫德明里的情人中國南方船家少女阿瑤——一個仆役,最終為他留下一女二男三個孩子;以及赫德留戀不去,食其俸祿、謹慎伺候建設五十四年的晚清帝國,成為歷史卷帙里頗富聲名的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生命中的雙重“情人”。對一個中國下層女子的始亂終棄和對一個晚年帝國的寄托迷戀,成為趙柏田文學敘事和歷史敘事施展各自手腳的空間。
當赫德體面地成為總稅務司,自然會一步步地抹去自己青春荒唐行徑的斑斑劣跡,回國娶一個端正合體面的英國女人做妻子。所以阿瑤被拋棄,他和她的孩子被秘密地寄養在英國。但對阿瑤的懷想成為他記憶底子里無法抹去的中國故事。趙柏田在這一歷史記載的終止處氤氳出一片小說家的歡娛和柔情,雖然阿瑤在小說中僅縮略成幾個閃回的片段——像極了意識流的鏡頭、一些泛黃卻清晰的老片花,但阿瑤的中國式柔順和南方熱帶式的多汁、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讓小說頓時顯得很有生氣。遺憾,作為小說家的趙柏田確乎是吝嗇的,他刻意地如此節制地讓阿瑤只在高聳無際的歷史宮墻的小道間偶爾閃現,令我們直呼不能過癮!
而另一面,趙柏田如此癡迷于自己這些年的歷史敘事癖。他從費正清、凱瑟琳·弗羅斯特·布魯納和司馬富編的兩冊《赫德日記》、中國第二檔案館等編的九卷本《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赫德自己的著作《這些從秦國來:中國問題論集》等等史料中抽絲剝繭,敘述著赫德在同治末期到光緒末期的遭逢——一個英國人被聘用擔任晚清正二品官員,這在今天都很難發生;他28歲開始領導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掌權長達四十五年,在衰朽的舊帝國制度中,創造出唯一廉潔不貪腐的高效衙門;他執掌海關稅務時期,關稅年年高漲,成為了晚清帝國重要的國家經濟來源,他所實行的正是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認為中國所缺乏的“數目字管理”;他介入了震蕩帝國的八國聯軍和義和拳,思想作為都可圈可點……這些,趙柏田都細致記錄、虔謹呈現。他在《赫德的情人》的創作筆記中說:“馬士想寫一部傳記,卻寫成了一部歷史。我想寫一部歷史,卻寫成了一部小說。”——馬士(Morsee,Ballu,1855-1934)就是赫德在中國海關的重要助手,他寫出了令國際漢學界稱道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他原想寫的是赫德的傳記;而趙柏田如此與之對照,除了說明他其實擅長的還是文學外,毫無疑問是在說,他更鐘情于歷史,他的敘事理想本就是“一部歷史”。
《赫德的情人》令我揮之不去的一個歷史思考和想象在于:“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是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談及中國近代文學時候的很有影響力的觀點。趙柏田在《赫德的情人》中無疑也蘊含了這樣一種史識即思想史關懷。雖然他執著于書寫與赫德有關的晚清政局和外交事件,但赫德的經歷恰好精準地緊扣了“晚清”的時間斷點,也就是說,赫德正是晚清的見證者、參與者,是“改良派”、“洋務派”的同行者和同道人。赫德無論出于私人利益還是帝國公理,都謹慎聰明地適應著中國獨特的人情世故和行事規范,目的是在大清帝國和大英帝國、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之間找到一種平衡,企圖幫助完成中華帝國的現代轉型。在王德威的文學研究中,他提到了“晚清”蘊含著豐富的可能性,但歷史最終選擇“革命”終結了某種豐富的可能性,使中國的現代轉型走向了比較單一的調性。趙柏田在此以文學化的筆墨描摹了殘暮之年赫德離開時內心的落寞,也借此隱喻了對這樣一種歷史調性的悵然感。
他寫道:“1911年9月20日,羅伯特·赫德在英國南部白金漢郡的馬洛去世。二十一天后,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他為之服務了半個世紀的大清王朝耗盡了最后一口元氣,土崩瓦解。”——赫德與他的“情人”,終究是同命同病,于是同時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