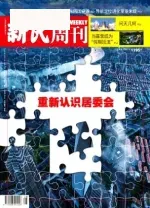阮儀三:我們要有一種保護文化遺產的情懷
劉曉藍

日前,有關恢復重建圓明園的建議頗為引人注目,《新民周刊》就此事專門采訪了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生導師、享有古城衛士美譽的阮儀三教授。
“廢墟之美”
“對于歷史文化遺產,應該原樣留存。一般來講,毀掉的東西不重建!”阮儀三教授開門見山。
自上個世紀80年代,阮儀三就曾努力促成平遙、周莊、麗江等眾多古城古鎮的保護,并獲得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委員會頒發的“2003年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
這次圓明園,究竟意欲推倒重來的“重建”,還是精心保護下的“修復”,尚無最終細節定論。
早在2006年,浙江橫店集團就曾計劃籌資200億元耗時5年,欲復制再造圓明園。這也是阮儀三第一次因為圓明園,與他人“交火”。他對此猛烈抨擊,稱其“完全是為了商業利益,勞民傷財”。
而最終,這起事件也以橫店方面的放棄和“潰敗”而告終。“當時和我爭得厲害,其實我早知道他做不成。”阮儀三說道。
而在本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在關于加強國家文化中心建設提出的九大建議中,又有有關研究論證恢復重建圓明園的建議。
據文化學者吳祚來稱,即使“動議重建圓明園一部分,不超過總建筑的十分之一”,但總占地達五千多畝的圓明園,如果按面積規模來計算,十分之一也將會是一個“巨大的土木工程項目”。
吳祚來以希臘古奧林匹克競賽場如今的荒野之態為例:希臘人沒有選擇重建競賽場,以饗全世界人民對于“古奧運場無限風光”的向往。他們要廢墟,“而非破壞歷史形態的仿造贗品”。
“能夠欣賞廢墟之美,比欣賞實物之美,更能提升一個人或整個社會的審美境界”,通過廢墟,感受煙塵,發思古之幽情。文化情懷和豐富想象力缺一不可。吳祚來評論。
針對重建,阮儀三更加一針見血,“這背后,經常是很大的經濟利益在驅動!”他表示憤慨,“現在就有這么一批人一批城市,尤其喜歡復建。”
“美麗誤會”?
這場論戰中,主張重建圓明園者覺得自己是“被”誤會的。他們苦口婆心,試圖“澄清”自身立場。
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劉陽就表示,自己完全理解為何九成網友反對重建圓明園。他認為,很多人的認識基本停留在僅占圓明三園總面積2%的西洋樓、大水法,對圓明園并無全面了解,“那種認為重建圓明園就是要把那幾塊大石頭重新修復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大水法的形象在公眾心中早已根深蒂固。那是一提到圓明園,腦海中立馬就會浮現的畫面。劉陽也一再強調,圓明園的代表建筑,如西洋樓遠瀛觀、大水法不會重建。
但是,對圓明園如果不及時進行修繕保護,“未來10年內,圓明園至少有5處景觀將倒塌或徹底消失。此外,圓明園還有至少8處景點被一所中學占據,學校逐年擴張對圓明園景觀造成破壞。”劉陽表示擔憂。從這點來看,劉陽之意在“修復”。而非激進的“推倒重建”。
其實,風剝雨蝕所造成的岌岌可危,類似挑戰,全世界都在面對。“文物保護的目的,就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盡力完整留給子孫。”阮儀三說。他去日本太極殿,看到“地面上的廢墟,完整留存”。甚至還有戰爭現場燒成一半的殘柱,坍塌的土層清晰可見。“當然也怕風吹日曬,就搭個棚子保護起來。”
這種修復,是進得了阮儀三心里的。它包含著一個“五原”原則,即:原材料、原工藝、原樣式、原結構、原環境。“對圓明園,如果這個原則不堅持,貼些假東西上去,古代建筑氣息定然消失殆盡。”
與修復不同的是重建,另當別論。阮儀三也沒什么好感,“重建的目的,主要就是商業化運作。”近期,有些城市大張旗鼓地“重現”漢唐風貌、遼代風貌,結果原版的民居被拆個七零八落。留下虛假人為的“東西”,和文化、遺產完全風馬牛不相及。“這和政績大多相關。”
當然阮儀三也并不完全反對對少量標志性建筑仿造,留存部分形態。“但大范圍的整體去恢復,就完全沒必要。”阮儀三信手拈來蘇州的例子,對于這個“本來城市規劃一直不錯”的江南城市,阮對其如今忙于重修古城墻的行為似乎頗有微詞。
對于萬園之園,也有人認為,保持廢墟太絕對,至少對于圓明園的山形水系應該復建。和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張寶章持同樣看法的也不在少數。對此,阮儀三表示,結合地面綠化環境情況,在不破壞生態的條件下,允許加以必要整理。“小面積的做,沒有問題;大面積的話,就得仔細考慮。”
“有拆的錢,沒修的錢”
很多時候,修復遺跡比重建遺跡花費要多。無論建筑還是廢墟,拆除掃平,只是三下五除二;重建時,施工隊高效率現代化作業,成本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修復工程,則必須小心翼翼,謹小慎微,懷揣一顆敬畏之心。
阮儀三說,他跑去歐洲日本看,人家遺跡也一直在修,而且精細認真,對歷史原貌悉心呵護。記錄細節修復時間自不必說,甚至為了加固而放進去的鋼件、鐵件也個個“記錄備案”。
而在我國,“保護”文化遺產經常和發展旅游、發展經濟混為一談。然而,發展旅游文化事業,一旦從經濟出發,文化的本身內容就容易被篡改。歷史文化被旅游和經濟“綁架”。
完整保存歷史信息,這是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原則。“但中國不會這樣。大多推倒重來。”這種只拆不修的怪現狀,也使中國陷入“只有拆的錢,沒有修的錢”怪圈。也不禁引發疑問:那我們手中,到底有錢還是沒錢?
這種純粹的重建危害至深。世紀之初,在孔子的故鄉曲阜,曾拿下其文物景區經營權的華僑城集團,引發“水洗孔廟”事件,一時震驚全國。早在1978年,曲阜欲強行撤掉城墻,阮儀三等人就出面阻止,但“根本沒用”。城墻拆掉后,到2003年,不知為何,政府竟又回心轉意重建城墻。阮嘆氣,“里面是鋼筋鋼筋混凝土架構,外面貼磚頭,根本就是假古董!”
錢要花在刀刃上。“文物遺產的撥款,應該放在修復上。”希臘帕提農神殿,意大利斗獸場,其保護都在本著原貌留存的原則,有一定程度的加固,只是為了防止坍塌。同時,新舊材料也完全分開,“如果后補上去的,必有文字說明,一目了然。”
與其拆掉老祖宗的東西干巴巴模仿,為什么不去創造有現代精神、傳承發揚民族文化的新作品。阮儀三一直困惑不解。他解釋成,當今社會人文化底蘊的淺薄、文化和藝術方面的“無能”。北上廣的很多著名建筑,偏偏更多出自國外設計師之手。
相關技術和法律,也成為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絆腳石。如保鮮技術不到位,導致西安秦始皇陵陶俑出土便會氧化,破壞了本來面目。只能等更高新科技問世,這片沉睡的皇家御林軍方能耀武揚威。西漢馬王堆所涉及的人體保鮮技術,也面臨同樣問題。
另外就是人的問題了。對此,學者吳祚來和阮儀三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北京某城門的重建,一致認為“做得很差”。怎么能不差?據吳祚來介紹,修建歷史遺跡的人員“大多是農民工兄弟”,而真正文化方面的能工巧匠,恐怕不會請,人家“一個月工資就好幾萬”。
加之,“法律也不健全,根本提不到日程上來”。如今國民對于文化遺產的理解和重視根本不夠。姍姍來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剛剛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也才于2006年11月14日起施行。相比之下,法國早在1887年就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護法。
蘇州的城市規劃和發展被阮儀三特別提起,當年他也曾參與城區規劃。現在,蘇州不在老城里建高層,而是新城區在老城外發展,東西南北稱得上涇渭分明。“新就新到底,老就老到家。”阮儀三以此強調城市規劃和保護的觀念問題。
阮儀三也參加過北京古城規劃的高度控制。當時,阮和同行們在北京上空“畫了幾個圈”,指出,圈內建筑高度必須嚴格控制。結果“沒過幾年就推翻了”。故宮保護較好,天壇則沒那么幸運。作為皇帝祭天、祈谷的神圣之地,走在甬道上,本應當“肅穆寧靜,藍天白云,天壇高高聳起”,如今卻“滿眼都是高層了”。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搞清楚:什么叫做重建、什么叫做修復、什么叫做保護、什么叫做為了經濟利益。”談話最后,阮儀三呼吁社會公眾,能夠“留一份重視并保護文化遺產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