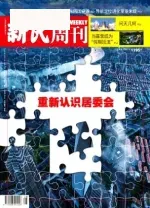法國伉儷中國夢
金姬



明年1月,一本名為《下有戴亮》的中法雙語自傳將在中國發售,書的作者是在上海生活多年的法國音樂人克利斯朵夫·易斯岡(Christophe Hisquin)。他有一個大家更為熟悉的中文名“戴亮”,這個藝名Dantès取自大仲馬的小說《基督山伯爵》主人公唐泰斯。作為第一個創作中文歌曲并在中國發行專輯的外國人,戴亮在上海小有名氣。除了唱歌,他還活躍在中國的電視熒屏和各大活動中,展現了過人的演技和主持功力。
這位33歲的里昂小伙能夠在中國成功擁有自己的演藝事業,小他2歲的妻子美蘭(Mélanie)功不可沒。“我從小就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一直以為自己會娶一個中國妻子,連我的母親都這么認為。”戴亮說,“但10年前,上帝送來了美蘭——她是我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想要娶的女人。”
功夫和崔健
1978年,戴亮出生在法國第三大城市里昂,是家里的長子。他從小就喜歡音樂,8歲開始學管風琴,16歲學吉他。記得12歲時,他偶爾看了一部中國電影,被里面的武術深深吸引,于是開始對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度心馳神往。也正是在這一年,戴亮所在的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附中開設了中文專業。當時,老師要求學生們必須選學一門外語,戴亮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文。這不光是滿足自己的興趣愛好,也因為年少的他覺得學中文可以表現自己與眾不同,比較有個性。就因為個性和有興趣,他一學就是十幾年。12歲時,戴亮所在的班級有30名同學學中文,很多同學認為學中文太難,到大學時只有4個人還在堅持而未放棄,戴亮就是其中之一。
戴亮第一次來中國是17歲。1995年,他和12位同學作為交流生來到北京大學。在一個月的交流時間里,他碰到了第一個讓他難忘的中國人—— 崔健。當時,他們的中文老師(一個法國人)安排他和其他3名同學采訪彩排中的崔健。“我當時并不知道崔健在中國樂壇的地位。但是我依然很緊張,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用中文采訪。”戴亮回憶道,他當時的漢語聽說水平還不行。彩排時,崔健的樂隊用的是電吉他和小號。“由于我們4個學生也是玩音樂的,還現場給崔健表演了一下。”戴亮說當時的崔健禮貌性地送了他一張專輯,他回去仔細地聽了這張專輯,一種奇妙的感覺就油然而生:去中國發展。
戴亮和崔健見面后回到法國,就開始中文歌的創作。他在1999年發表了收錄4首中文歌曲的專輯。2000年,作為法國里昂大學應用外語專業的學生,戴亮再一次來到中國。之后的一年時間里,他開始參加各類適合自己的比賽,接拍廣告和電視劇。2001年回到法國后,他開始了社會音樂學專業的全面學習。
情定日內瓦
回到法國后不久,也和戴亮一起學中文的越南裔法國姑娘邀請他到瑞士日內瓦游玩。“我要介紹一個朋友給你認識,你是中國通,她可是好幾國的專家,尤其擅長俄國文學。”越南裔同學告訴戴亮,那個朋友剛從歐洲最好的翻譯學校——瑞士日內瓦大學(UNIGE)高級翻譯學院(ETI)畢業,精通六國語言(法葡西英德俄)。這就是美蘭,一個知性美麗的葡萄牙裔法國人。
“她并不是第一眼就讓我心動的那種漂亮女孩,但她身上的國際化氣質很吸引我。”戴亮笑稱,當時的自己剛從中國回來,還是一個每月領著300歐元獎學金的學生;而美蘭在日內瓦有一份月薪3000歐元的工作。
兩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因為旅游、外語和音樂等共同語言很快就陷入了熱戀。“我對她是很自然的追求。”戴亮說,他也交往過中國女孩,但可能自己太年輕了,根本沒考慮過結婚。“在法國,30歲以前不要婚姻是很正常的事。”美蘭讓他有了成家的念頭,也許這就是緣分吧。但一開始,美蘭的父母并不看好這個未來的女婿。
美蘭是第二代移民,已經完全法國化,但她的父母卻是典型的葡萄牙人,和傳統的中國父母很相似。戴亮記得第一次去依云小鎮拜見未來丈人丈母娘時,美蘭的父母劈頭蓋臉就問起收入、買房等實際問題。美蘭是三個女兒中最大的一個,也是父母的驕傲,他們不愿自己的寶貝女兒跟著一個沒房沒車且收入只有女兒1/10的里昂小子跑了。“我知道當時的自己在收入和工作穩定性上都不能讓美蘭父母滿意,但是我告訴他們,我今后會去中國發展,所以不需要在法國買房。”戴亮的真誠很快打動了美蘭的父親。“他很羨慕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他當初為了從葡萄牙移民到法國,選了一份自己不喜歡的職業。”
獲得家人首肯后,結婚典禮又成了一個大問題。“葡萄牙人的家庭好面子,希望舉行一個十分盛大和熱鬧的婚禮。”戴亮說,他家是典型的法國中產階級,婚禮注重簡單、溫馨。最后,美蘭說服了自己的父母,她和戴亮2003年1月在里昂的一處城堡舉行婚禮,邀請了200多名賓客參加儀式。隨后的家庭晚宴只邀請了40人,主要是兩家的至親好友,美蘭有很多親戚從葡萄牙和西班牙趕來。
夫唱婦隨
結婚第一年,美蘭為這個家庭付出了很多。兩人租住在里昂,房租600歐一個月。美蘭每周有2天時間坐一個半小時的火車去日內瓦工作。“放棄日內瓦的生活跟我到里昂,就好像上海人去蘇州那樣的感覺。”戴亮說,雖然自己每周打工一天,但也僅夠付房租,妻子的薪水成為小兩口的主要經濟來源。戴亮除了念書和打工,把大多精力都放在錄唱片上面,做音樂是件很燒錢的事。
美蘭一直支持丈夫的事業,雖然她更想去俄羅斯,但還是答應跟著戴亮先到中國發展。“我當時忽悠她,說只去中國一年,然后陪她去俄羅斯。”戴亮說,美蘭后來定居上海后就喜歡上了這座城市,去俄羅斯的事也就不提了。為了更好地在中國生活,美蘭在里昂學了6個月的中文,想不到發音比戴亮還標準,妻子的語言天賦讓戴亮自嘆不如。
2004年,戴亮第三次來到中國,轉投上海音樂學院攻讀社會音樂學博士,師從陶辛。他和美蘭擠在學校的宿舍里,美蘭沒有一句怨言。她給一家瑞士鐘表商在上海做咨詢工作,薪水高而穩定,讓戴亮沒有后顧之憂。
戴亮平時靠拍電視養活自己,他在《恭親王傳奇》中扮演一個叫李泰國的英國商人;在《明天我不是羔羊》中扮演美國商人約翰;在《精武飛鴻》中飾演辰飛;在《曹老板的十八個秘書》中扮演約翰的助手,在《長恨歌》中扮演大使的朋友……
當然,戴亮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音樂上。在這期間,他開始著手計劃如何讓中國人了解他的想法及音樂,如何用中文表達出法國的文化,用音樂表達自已的思路,戴亮希望通過音樂完成一種超越文化的交流。他曾跑過很多音像店,問工作人員是否有外國人寫中文歌的專輯,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戴亮很好奇,有很多中國人專門寫英文歌,也有很多法國人寫英語歌,可是專門寫中文歌的外國人卻沒有。他決定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中國和法國是兩個有著不同文化的國度,作為一個法國人,在堅持原創中文歌曲的時候,戴亮遇到很多的麻煩。最大的困難就是中法兩國人的思維不同。戴亮說,中國和法國人有著共同點,都喜歡藝術,喜歡美的東西。中法兩國人又有著很多不同,法國人的思路比較亂,描述一件事情比較喜歡用長的句子,而中國人則來得更直接,用很短的字句便表達出準確的意思。
2006年后,戴亮在中國發行了雙碟《我記得你》。“我很榮幸自己是唯一一個用中文創作歌曲的外國人。”戴亮說,唱片的法文名字叫Parfums d'Extrêmes(意為“遙遠的香水”)。這張特殊的唱片是他和意大利錄音師羅馬諾在法國錄制的。錄制一張這樣的唱片,起碼需要4萬元人民幣,除去羅馬諾自告奮勇地承擔1萬元,剩下的3萬元就要自掏腰包了。對于沒有穩定收入的戴亮而言,妻子的支持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愛音樂,愛上海
《我記得你》發表后,戴亮受到了中國音樂界及媒體的一致好評與鼓勵。從那以后,戴亮成了各大電臺和電視臺的常客,他還在上海法語培訓中心舉行了個人演唱會。當他的事業蒸蒸日上時,美蘭的事業卻出現了波瀾,她和瑞士鐘表商的合同到期了。
那一階段,夫妻倆時常有些小口角。“美蘭希望周末能夠留給家人,但我的工作性質很可能今天接了電話,明天就要到其他地方去表演或主持。”戴亮說,他們從來沒有為了錢而不開心,但是歐洲人很注重休息時間和家庭觀念,他的這種不固定的工作時間讓美蘭有些難以適應。而且,長相帥氣的戴亮也有許多女粉絲,有時還會發來短信,這讓美蘭產生一絲危機感。
為了和丈夫有更多的時間相處,美蘭曾一度成為戴亮的經紀人。“我太太其實并不勝任這份工作。”戴亮坦言,美蘭是一個性格開朗、朋友遍天下的人,但她做事風格很西化,并不適合和注重關系、言語含蓄的中國人打交道。戴亮后來還是請了更為專業的人士來幫忙。
“我有時主持的時候,活動方也會要一個女主持,我就會推薦美蘭。”戴亮說,像美蘭這樣可以流利說7國語言的人很少,美蘭的形象也不錯。“但她太緊張了,有時會為了某個主持活動好幾天睡不著覺。”后來一段時間,美蘭選擇在家當一個好妻子。
“我們2006年搬到盧灣區的建德坊三室一廳的房子里。美蘭喜歡粉色,她把我們的小屋重新粉刷了一次,這一開始讓上海房東有些困撓,因為中國人的墻面很少使用這種顏色。”戴亮說,幸好他們長租到現在,而且美蘭是一個有潔癖的人,家里一塵不染,這讓房東比較放心。美蘭還做著一手好菜,只要有空,她就會下廚做法國或葡萄牙大餐。她也很會織毛衣,有時穿著自己織的毛衣出門,立刻就會圍上來一些上海阿姨,和她交流編織技法。
戴亮在中國的出鏡率也越來越高。2008年,他多次作為特邀嘉賓在上海外語頻道的節目中獻唱。上海生活時尚頻道也曾邀請他擔任嘉賓主持。同年,東方衛視播放了戴亮的傳記短片《下有戴亮》,介紹了戴亮在中國的學習、生活及工作。與此同時,法國媒體也開始對戴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2008年底,戴亮取得了里昂第三大學的博士學位,被法國音樂界稱為“21世紀初的中國音樂界專家”。
2009年戴亮出版了第二張雙碟專輯《下有戴亮》,打出“上有天堂,下有戴亮”的口號。在這張專輯中,他融匯了從民謠到法國香頌的多種音樂風格。那一年,他在法國里昂舉辦了個人演唱會,這讓美蘭也感到十分驕傲。她也開始公開給丈夫加油助威。2009年8月,戴亮和美蘭參加了《全家都來賽》節目,參賽口號就是“美蘭加戴亮 愛情有力量”。
去年,戴亮出版了單曲《上海》的中文版和法文版,并拍了MV。美蘭也愛上了上海這座城市。
如今,美蘭是在上海一家法語學校教德語。精通七國語言的她,抽空還在學習日語和韓語。她每天6點出門,坐車一個半小時去青浦上班,從未覺得辛苦,因為教語言是她所擅長的事。“幸運的是,她的這份工作是和法國方面簽約的,她可以拿到法國的保險。”戴亮說,之前兩人雖然經濟上不成問題,但是沒有一份法國保險,就好像上海人工作沒有“四金”那樣心里不踏實。美蘭的工作不但解決了她的保險問題,按照法國法律,作為丈夫的戴亮也可以享有同樣的保險。
除了教書,美蘭每年有4個月的假期。戴亮則答應妻子每年抽出2個月的時間陪她回法國,并到世界各地旅游。這樣的生活方式讓中法兩國的親朋好友都很羨慕。“我們努力工作,也能有足夠的時間休息。”戴亮說,明年1月是他和美蘭結婚9周年,他計劃帶她去印尼旅行。“我們還沒有要孩子的打算。現在很享受這種生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