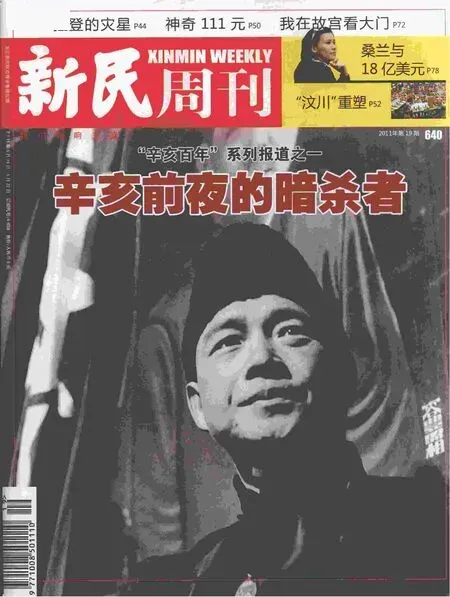拉登之死在歐洲
鄭若麟(巴黎)

本·拉登之死,在歐洲引起的反應(yīng)是非常復(fù)雜的,是世界其他地區(qū)所有“頭腦簡單”者所難以理解的。歐洲本是全球思辨型“哲學(xué)家”叢生之地,思想繁復(fù)不足為奇;更何況歐洲對發(fā)生在歐美大陸的所有宗教事務(wù)極為敏感,反應(yīng)多元當(dāng)屬正常,盡管“政治正確性”的底線是不能突破的。
作為美國反恐戰(zhàn)爭的盟友,歐洲官方反應(yīng)無一例外,都是對奧巴馬的溢美之詞。民間也同樣存在著“無條件親美派”,著名哲學(xué)家、將法國推進利比亞戰(zhàn)爭的亨利·勒維就是代表。他們高度認(rèn)同奧巴馬,但大多數(shù)歐洲輿論則在一致認(rèn)同“本·拉登是罪犯”(這一點與阿拉伯世界截然不同)的前提下,呈現(xiàn)出多樣化趨勢。西班牙一家報刊標(biāo)題是“為了達到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愛爾蘭一家日報的頭條通欄是“烏薩馬(本·拉登)手中沒有武器”,德國一家報刊則寫道:“他們有權(quán)這么做嗎?”顯然,歐洲在總體上支持美國的同時,也對美國的做法提出“歐式”質(zhì)疑。
“正義得到了伸張”?這是嚴(yán)謹(jǐn)?shù)臍W洲人所無法接受的。正如法國著名作家、曾有專著研究9·11事件的馬克-艾多拉爾·納伯所說,擊斃本·拉登,你可以說是重大勝利,可以說是輝煌成功,但就是不能說“正義得到了伸張”。因為在歐洲人眼中,正義只有通過司法審判才能得到伸張。而美國目前的做法是典型的“牛仔”風(fēng)格,拔槍將仇敵干掉就是正義,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所應(yīng)采用的方式。要知道,歐洲與美國一樣,網(wǎng)絡(luò)上盛傳對9·11事件的質(zhì)疑。歐洲部分輿論認(rèn)為,審判本·拉登才能真正解開這個結(jié)。納伯的觀點在歐洲并不孤立。
如何證明拉登之死,這是歐洲提出的另一個疑問。《巴黎人報》寫道:關(guān)于本·拉登死訊的所有信息來源都是一個:美國官方。國際媒體根本無法進行獨立核查,因此無法不引起疑惑。歐洲和美國一樣,不缺“陰謀論”者。歐洲人認(rèn)為,美國人這次的所有做法——殺死而非活捉本·拉登、拋尸大海、拒絕公布照片,甚至連前后說法不一的“多種獵殺版本”,包括“武裝抵抗版”、“人肉盾牌版”、“當(dāng)場處決版”——都似乎在“拼命為陰謀論者提供所有佐料”……鑒于2003年對伊開戰(zhàn)前美國鄭重其事地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向全世界公布其所掌握的薩達姆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所謂“證據(jù)”,最終被證明純屬子虛烏有,歐洲人不得不多一個心眼。
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對美國電視臺播出歡呼人群的畫面時表示,他完全不贊同對一個人的死亡進行歡呼。這不是歐洲的傳統(tǒng)。以世界唯一一個“超”超級大國的地位,慶賀一個仇敵的死亡,令人感到的是心理上的“虛弱”。德維爾潘的看法得到相當(dāng)一部分法國人和歐洲人的認(rèn)同。
在本·拉登與阿拉伯之春的問題上,歐洲輿論更是形成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種認(rèn)為阿拉伯之春標(biāo)志著本·拉登恐怖主義在伊斯蘭思想上的死亡,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再也沒有人呼喊支持“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一個證明。本·拉登之死將徹底埋葬本·拉登恐怖主義。反駁者則認(rèn)為恰恰相反,本·拉登本人就支持阿拉伯之春,因為在推翻阿拉伯親美、親以色列政權(quán)的斗爭中,他找到了“同路人”:反對獨裁的阿拉伯青年。本·拉登支持推翻卡扎菲政權(quán)就是一個佐證,因為利比亞目前是一個民族主義政權(quán),而非本·拉登所向往的純正的伊斯蘭政權(quán)。
拉登之死是否對恐怖主義意識形態(tài)畫上了一個最終的句號?法國一家報刊寫道:本·拉登死了,恐怖主義仍然活著。本·拉登死前最后發(fā)出的恐怖警告,正是針對法國的。就在其死亡前兩天,與法國關(guān)系密切的摩洛哥發(fā)生恐怖襲擊,死者中包括8名法國人。調(diào)查證明這是一個“具有本·拉登思想”的“獨立恐怖分子”所為,這從側(cè)面證明,拉登之死不可能使恐怖主義從此畫上一個最終的句號。法國政治學(xué)博士科斯德利昂甚至寫道,拒絕公布拉登死亡畫面令人奇怪地感覺美國人似乎有種“負(fù)罪感”,或無力控制自己的勝利,甚至好像這一勝利將預(yù)示著一場更為可怕的戰(zhàn)爭的開始……
9·11畢竟發(fā)生在美國,歐洲人多少有些超脫。拿本·拉登死訊搞笑的歐洲輿論也不少。一家法國電視臺就調(diào)侃:被拋入大海的本·拉登,將會成為一個“來自大西洋海底的人”(一部美國上世紀(jì)70年代電視連續(xù)劇)。美國不知會對歐洲人的“幽默”做何反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