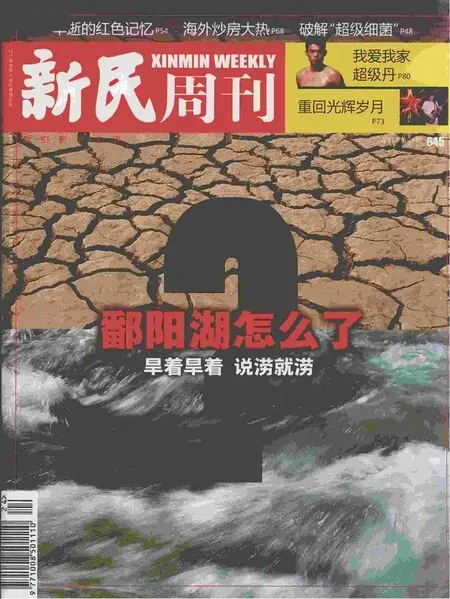年中盤點保障房
聶日明
6月1日,財政部、住建部聯合通知,要求各地切實落實保障性安居工程資金,加快預算執行進度。急切之情,躍然紙上。形勢亦不得不讓人著急起來,溫家寶總理于2月末與網民交流時表態,計劃從2011年起的五年內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萬套,其中2011年將完成1000萬套。但近期的摸底調研卻顯示,今年的建設計劃執行前景堪憂。
政府表態的保障房“民心工程”令人歡欣鼓舞,近兩年顯示躍進狀態的保障房建設提速亦有民意基礎。但現實卻并不一定讓人滿意。1998年的房改文件《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基本思路就是將住宅市場分為兩個部分: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前者刺激供給和改善質量,增加住房市場的效率;后者以政府補貼和政府保障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確保社會公平。但房價高啟數年以來,保障房建設遲遲未能如人意,自然有其不可回避的障礙。就今年的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需要1萬億以上的資金。這相當于全國一年的土地出讓金,盡管政府賣地收入不少,但這些錢要么補虧空,要么用于新項目,年度決算和預算的節余并不多,保障房建設的資金從何而來?
房改啟動以來,土地財政漸成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壟斷的一級土地市場、快速增長需求(購房者的收入增長和住房按揭貸款),使得房價持續上升,亦保證了土地出讓金的增速,也維持源源不斷的房地產稅費收入。換言之,因為沒錢,所以政府才要借高房價汲取收入。現在要政府拿出它們費盡心機收來的錢來建保障房,如何可能?尤其是當前中央地方財政收支格局的失衡,靠中央對地方政府下命令、簽軍令狀的約束來保證保障房的建設,難道是有效的監督機制?并且不管是政府的資本還是市場的資本,在低利潤率的情況下參與到保障房建設中,很可能意味著市場發生了扭曲,借保障房之表,行“富人房”、“官員房”為里,是近幾年保障房建設過程中屢見不鮮的景象。
進一步分析,由于短時間內住房建設的供給是有限的,保障房的大躍進,勢必要和商品房搶奪土地、資金、產業工人、建筑原材料等,對公共服務、城市規劃影響亦很大。保障房與商品房的競爭關系是無法回避的,我們現在真的需要3600萬套保障房嗎?如果壓縮商品房開發來完成保障房任務,將進一步抬升商品房的價格,也有違目前房價調控的初衷,更將嚴重影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與稅費收入,對地方政府來說是不可容忍的沖擊。
就算不考慮保障房建設的資金危機,還有相當多的疑問待解:建什么樣的保障房?誰來住?如果建設的是迎合上意的政績工程,未必能急平民之困、百姓之需。急令之下,會不會出現重數字、不重品質,重生產指標、不問使用人的需求的現象?保障房的品質、公共服務會不會成問題?或許,各地政府還會擴大、扭曲保障房的含義、概念,將動遷房、限價房等都計入保障房,在數據中大面積注水。這些都是以往計劃經濟中慣以為常的現象,前車可鑒。
有必要反思,目前的保障房提速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保障房的本質是財政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雖然有補磚頭和補人頭的效率與公平之爭,但都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而非空口白牙畫大餅。技術和機制設計的改進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以增加供給,但不可能無中生有、創造供給。在方案設計中,更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會一心為民、多快好省地建設保障房。保障房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政府干預就意味著大量轉移支付,在目前的財政收支背景下,是不可能的。
我們始終要回答保障房的兩個問題:要保障哪個群體?我們要為它支付多少錢?這是公共選擇的問題。
從根本上講,改變政府決策與負責機制最為重要,也即:變對上負責為對下負責,增強納稅人在決策、政府行為監督上的權利。其根本是財稅體制的民主問題,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推進財政稅收體制乃至最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完成。只有把這些問題梳理清楚,談建多少套保障房、建什么房、如何籌集資金、降低成本等議題才順理成章。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