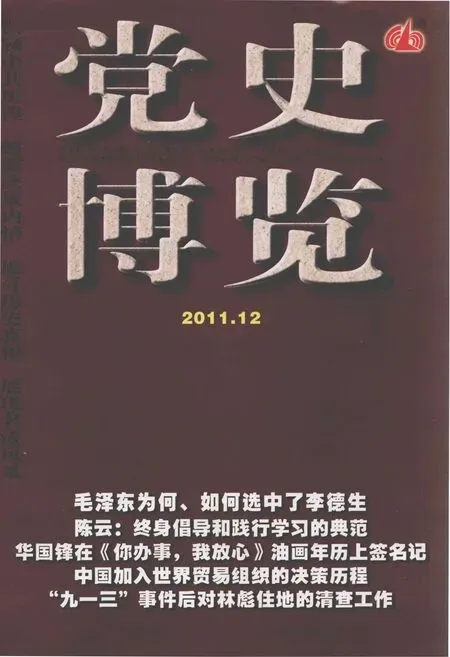“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儒法斗爭史研究
○彭厚文
儒法斗爭史研究的由來
從時間上看,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在“批林批孔”運動正式發動之前就已經開始了。1973年9月,“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市委寫作組以石侖的筆名在《學習與批判》創刊號發表了《論尊儒反法》一文。這篇文章發表后,當年第10期的《紅旗》雜志以及10月25日的《人民日報》相繼全文轉載,由此可以看出“四人幫”對它的重視。
《論尊儒反法》提出了儒法斗爭的概念,認為“儒家是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統治的反動學派,法家是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利益的進步學派”,儒家提倡“禮治”,法家提倡“法治”,儒家主張守舊,法家主張革新,儒家和法家的斗爭不是學術主張之爭,而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在思想政治戰線上一場劇烈的階級斗爭”。儒法斗爭不僅在春秋戰國時期存在,而且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還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進行著”,并且一直持續到現在。文章提出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爭的階級本質,認為這“對于搞好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義的”。這篇文章揭開了儒法斗爭史研究的序幕,并為后來的儒法斗爭史研究定下了基調。
此后,“四人幫”控制的寫作班子及其追隨者又發表了一批研究和宣傳儒法斗爭史的文章。這些文章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上海市委寫作組以羅思鼎的筆名在《紅旗》雜志1973年第11期發表的 《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唐曉文在1974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么?》等。
《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除了以批宰相為名,影射攻擊周恩來外,還在《論尊儒反法》一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儒法斗爭是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認為秦始皇之所以能夠統一中國,就是由于執行了法家路線,因此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巨大勝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勝利”。

山東曲阜地區在孔廟內召開“批林批孔”現場會。
《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么?》則為法家找到了一個先驅——魯國的少正卯。文章認為少正卯主張實行同孔子完全對立的政治路線,即主張用“法治”代替“禮治”,也就是用地主階級專政代替奴隸主階級專政,因而遭到孔子的忌恨,所以后者一在魯國掌權,就殺害了少正卯。文章還認為,少正卯和孔子之間的斗爭,是意識形態領域中革新和保守兩條路線的斗爭,也就是新興封建勢力和沒落奴隸主兩個階級之間尖銳斗爭的表現。他們之間的斗爭“揭開了春秋戰國時期儒法斗爭的序幕”。在“四人幫”倡導的儒法斗爭史的研究中,這篇文章的惡劣作用在于通過渲染少正卯和孔子之間的斗爭,為儒法斗爭找到了一個源頭,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儒法斗爭不是一個虛構的概念,而是在歷史上確有其事,從而進一步論證了研究儒法斗爭史的必要性。
儒法斗爭史研究的演變
儒法斗爭史研究的開展,為“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做了理論上的準備。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正式發動之后,它成為了這一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在“批林批孔”運動的前期,它主要是為了配合對孔子的批判,給孔子及儒家學說樹立一個對立面,以此來進一步說明孔子及其儒家學說的 “反動本性”,參與其中的人數也不多,主要是“四人幫”控制的寫作班子及其追隨者。“批林批孔”運動進行了將近半年之后,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就是從1974年6月開始,研究儒法斗爭史成為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內容。
當時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一是因為“批林批孔”運動出現了混亂。在運動中,一些群眾又成立戰斗隊,搞大串聯,“文革”前期的動亂局面重新出現。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連續發出文件,提出要加強對“批林批孔”運動的領導。這迫使“四人幫”調整斗爭策略,加強“文斗”,以避免“武斗”遭到限制和約束后運動出現冷場的情況。另外,隨著四屆人大的日益臨近,“四人幫”加快了奪權的步伐。為了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中占據有利位置,攫取更大的政治權力,他們需要進一步大造政治輿論,一方面打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另一方面肉麻地吹捧和抬高自己。因此,“批林批孔”運動的這種變化,主要是服務于“四人幫”的政治需要的。
1974年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接見梁效、唐曉文等寫作班子的成員,座談如何使“批林批孔”運動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問題。江青提出儒法斗爭持續到現在的觀點,并要這些寫作班子把儒法斗爭一直弄下來。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批林批孔”座談會上作長篇講話,提出要重視和開展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和宣傳。她說:“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統、普及,必須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爭中來批才能深入。”“單純批儒,沒有對立面,不能從路線高度來看,看不到路線斗爭的規律。”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斗爭中培養理論隊伍》,以培養理論隊伍為由,提出要學習歷史,要讀一點法家的著作,要總結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社論說:“當前,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展,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對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系統化,以推動各條戰線的斗、批、改,用馬克思主義占領哲學、歷史、教育、文學、藝術、法律等在內的整個上層建筑領域。”
社論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培養一支宏大的理論隊伍,“各級黨委要把加強理論隊伍作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為了培養理論隊伍,搞理論工作的同志除了“要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還要學歷史,包括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讀一點法家的著作”。社論根據江青所謂的儒法斗爭持續到現在的觀點,提出:“劉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蘇修也是尊儒反法的,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的事實告訴我們:兩千多年來的儒法斗爭,一直影響到現在,繼續到現在,還會影響到今后。我們要總結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堅持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反對倒退,堅持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復辟資本主義。”這篇社論實際上是開展大規模儒法斗爭史研究的動員令。此后,開展儒法斗爭史的研究,進行評法批儒,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內容。
儒法斗爭史的研究擴大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
由于儒法斗爭史的研究成為了“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內容,因而儒法斗爭史的研究由以前的僅有少數人參與其中而擴大為一場全國性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后來一般被稱為評法批儒運動,但也有人把它稱為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如粉碎“四人幫”后,一位歷史學家寫的批判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1973年黨的十大以后,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展開了‘批林批孔’運動。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運動。可是在‘四人幫’操縱指揮下,這個運動很快被篡改為所謂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應該說,把這場運動稱為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更合適一些,因為從當時報刊上發表的批判文章來看,評法批儒的說法較為少見,更多的是將其稱為“研究儒法斗爭”或“儒法斗爭史的研究”。
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不是在 “批林批孔”之外發動的一場運動,而是在“批林批孔”的旗號下進行的,仍然是“批林批孔”運動的一部分,只不過更多地塞進了 “四人幫”的私貨而已。
研究儒法斗爭史作為一場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不僅理論工作者、史學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而且連黨政干部、工人、農民、解放軍都被卷入其中。當時的報刊上經常可以見到有關黨政干部、工人、農民、解放軍學習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爭史的報道。
1974年7月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 《天津站工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和宣講儒法斗爭史》,對天津站工人研究和宣講儒法斗爭史的情況進行了報道。12月15日的 《人民日報》發表了 《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沒有好下場——陜西省漢中縣建國大隊貧下中農圍繞 “斬韓信”史實研究西漢初期的儒法斗爭》。這篇報道說,陜西省漢中縣漢水公社建國大隊的貧下中農,在西漢初期漢高祖劉邦的“拜將臺”遺址前,聯系現實的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圍繞劉邦“斬韓信”這一歷史事實,研究了西漢初期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

“批林批孔”展覽。
從這些報道來看,研究儒法斗爭史成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群眾的一項政治任務。其實,就當時大多數工人、農民和相當一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來說,根本不具備研究儒法斗爭史的能力。所謂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只不過是借研究之名,在全國各階層人民群眾中灌輸“四人幫”的那一套儒法斗爭的理論,為他們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做輿論準備。
為了推動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四人幫”還組織人員撰文介紹和宣傳歷史上的所謂法家,選編和出版法家著作。1974年7月5日至8月8日,他們以國務院科教組等單位的名義,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會議。法家著作的選編、注釋、出版和研究,是這一時期儒法斗爭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四人幫”建構和宣傳他們那一套儒法斗爭理論的重要途徑。
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同“四人幫”現實的政治需要結合得更加密切
如果說在“批林批孔”運動的前期,儒法斗爭史的研究還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維護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圖,那么在“批林批孔”運動的后期,開展儒法斗爭史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維護 “四人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并為他們進一步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做輿論準備。
1974年,雖然“四人幫”還在黨和國家的權力中樞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他們已經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產生了嚴重的憂慮。當時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毛澤東年歲已高,身體狀況日趨惡化,在世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毛澤東逝世后,如果周恩來還健在,他將是“四人幫”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主要障礙。雖然毛澤東無意讓周恩來接班,但以周恩來在黨內的資歷、地位、威望和影響,他仍有極大的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種情況一旦出現,依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幫”無疑兇多吉少,政治前景不容樂觀。
鑒于此,“四人幫”一方面視周恩來為眼中釘,急欲除之而后快,采取種種手段打擊、排擠周恩來;另一方面,為了能在毛澤東逝世后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他們竭力爭取在黨和國家的權力結構中占據有利位置。當時,四屆人大召開的日期日益臨近,“四人幫”野心勃勃,企圖爭取由他們組閣。這兩個方面,就是當時“四人幫”的政治需要。他們倡導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這種政治需要出發的。
在這一時期的儒法斗爭史研究中,“四人幫”首先是把所謂的儒法斗爭定性為兩種思想、兩種路線的階級斗爭,認為這種斗爭開始于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思想政治領域的一場階級斗爭,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儒法斗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進行著,一直持續到現在,各個歷史朝代、各個歷史時期概莫能外。然后強調要古為今用,把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同現實的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聯系起來,“對儒法兩條路線斗爭和整個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進行科學的研究和總結,更好地為現實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服務”。
“四人幫”通過批判和丑化儒家,把攻擊矛頭幾乎是不加掩飾地指向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的儒法斗爭史研究中,“四人幫”控制的寫作班子竭力渲染秦始皇死后趙高的“復辟”事件。批趙高成為這一時期批判儒家的重點。羅思鼎在《紅旗》雜志1973年第11期發表的 《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中,大批宰相,用江青的話說,就是一口氣點了六七個宰相的名,批判這些宰相是奴隸主貴族的代表,搞復辟,實際上是以此來影射攻擊周恩來,但并沒有提到所謂趙高的“復辟”事件。
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開展以后,羅思鼎在《紅旗》雜志1974年第8期發表了 《論秦漢之際的階級斗爭》,隨后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篇文章煞有介事地構建了一個所謂趙高“復辟”的故事,認為秦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秦始皇對奴隸主復辟派鎮壓得不夠徹底,以致讓“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趙高鉆進了秦王朝的心臟,除擔任掌管車馬乘輿的中車府令外,還兼管皇帝的印璽和起草機要文件。后來,趙高就在秦始皇死后,發動政變,篡奪了秦王朝的政權,并用儒家路線代替了法家路線,從而激發了階級矛盾,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這樣,就把一起封建時代司空見慣的宮廷政變,牽強附會地演繹成儒法斗爭,演繹成儒家的 “復辟”。這篇文章發表后,“四人幫”控制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又先后發表 《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研究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進一步抓住所謂趙高的“復辟”事件大做文章。
綜觀當時對趙高的批判,主要強調如下四點:一、趙高是在秦始皇病重死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乘機發動政變;二、趙高發動政變之時,身居丞相要職的法家李斯本來有可能搞掉趙高,“粉碎復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他“妥協動搖,鑄成大錯”;三、趙高篡權后,便以復辟的儒家路線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并對“秦始皇的法家領導集團進行血腥的階級報復”,“秦始皇時代的法家幾乎一網打盡,無一幸免”;四、趙高篡權,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中央政權的法家路線”,“因此,奪得了政權的革命階級必須把路線問題放在首位,對于反動階級改變革命路線的陰謀詭計,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從上述四點可以看出,批趙高的實質是“四人幫”為了避免在毛澤東逝世后被“一網打盡”,要對可能出現的趙高式的人物發動政變篡權提前敲響警鐘,并預作防范。在當時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層中,誰最有可能成為“四人幫”眼中的趙高呢?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四人幫”批趙高,就是打著維護“革命路線”的幌子,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周恩來。
通過抬高和吹捧所謂的法家,替“四人幫”涂脂抹粉,為他們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制造輿論。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在內容上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批林批孔”的同時,大力宣傳、抬高和吹捧歷史上的所謂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對法家的宣傳、抬高和吹捧,其聲勢甚至超過了對儒家的批判。這一現象,是1974年6月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所不曾有的。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江青有著最為直接的聯系,與她的提倡和誘導是密不可分的。1974年6月14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談會上發表的長篇講話中,除提出要重視和開展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和宣傳外,還提出要大力宣揚法家。她說:“現在要深入批林批孔,必須在批判儒家的同時宣揚法家,這樣才能理解歷史上的路線斗爭。”
“四人幫”對法家的宣傳、抬高和吹捧,是如何服務于其政治需要的
強調儒家和法家兩條路線的對立和斗爭
為了突出儒家和法家兩條路線的對立和斗爭,當時有的文章竟然歪曲歷史,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實際主要是兩家爭鳴,一家是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利益的儒家,一家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其中,法家“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它是進步的力量,有強大的生命力”,儒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是反動的,是腐朽沒落的勢力”。儒法斗爭的實質“是搞‘克己復禮’,維護和復辟奴隸制,還是實行革命,建立和鞏固封建制”。這樣,法家就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眾多學派中脫穎而出,一躍成為進步力量的代表。
有的文章把中國歷史上的階級斗爭,進步與落后的斗爭,革新與守舊的斗爭,愛國與投降的斗爭,都概括為儒法斗爭,并認為儒法斗爭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這樣,法家就進一步成為正確、進步、革命、愛國的代名詞。
有的文章則直接秉承江青的旨意,提出兩千多年的儒法斗爭持續到現在,還會影響到今后的觀點。這樣,“四人幫”就成為了當代的法家。因為當時衡量進步與落后的標準就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按照這樣的標準,“四人幫”自然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當代的法家也就非他們莫屬了。所以,強調儒家和法家兩條路線的對立和斗爭,實際上是為了把“四人幫”打扮成正確路線的代表者。
吹捧呂后和武則天
在這一時期儒法斗爭史的研究中,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吹捧呂后和武則天的文章,呂后被說成是漢高祖劉邦死后法家路線的推行者,武則天則被推崇為歷史上很有作為的女政治家。
在1974年6月19日的 《人民日報》發表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中,對呂后有如下評價:“劉邦死后,呂后掌權。她‘為人剛毅’,曾‘佐高祖定天下’,當政后,繼續推行了法家路線。”羅思鼎在《學習與批判》發表的《論西漢初期的政治和黃老之學》一文中,也吹捧呂后執政“竭力守住劉邦的法家路線不變”,“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于武則天,梁效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4年第4期發表的 《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是一篇吹捧武則天的代表作。這篇文章把武則天稱為 “法家女皇武則天”,認為她“和歷史上許多有作為的法家皇帝一樣”,“有著十分鮮明的反儒色彩”,在其登基做皇帝以后,粉碎了守舊派的陰謀,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都實行了法家革新路線,“是一個順應歷史潮流的杰出人物”。
其實,這些文章都是秉承江青的旨意,借吹捧呂后和武則天來吹捧江青,為其篡權做輿論準備。
強調中央政權中有一個“法家領導集團”的重要性
梁效在1974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研究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中,根據對西漢初年所謂復辟與反復辟斗爭的研究,煞有介事地總結出一條所謂的“歷史經驗”,這就是:為了保證法家路線得到堅持,在中央政權中必須長期保持一個法家領導集團。這實際上是赤裸裸地為維護和鞏固“四人幫”的政治地位,并進而為他們奪取更大的權力制造輿論。
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開展以后,研究儒法斗爭史成為歷史學的中心內容和最重要任務。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政治、學術思想和不同政治、學術派別的斗爭,都被解釋成儒法斗爭。有人甚至提出“必須以儒法斗爭為一條線來重新改寫整個中國史”和中國哲學史;還有人提出“儒法斗爭這條線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國思想史上學派、體系、范疇,都要重新加以研究”。還有文章公然提出,歷史學的研究要向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學習,認為劉知幾“是替武則天推行法家路線制造輿論的一個較突出的代表”。因此,在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中,歷史學完全成為“四人幫”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
在研究儒法斗爭史的運動中,“四人幫”還提出,要通過這一運動,“推動各條戰線的斗、批、改,用馬克思主義占領哲學、歷史、教育、文學、藝術、法律等在內的整個上層建筑領域”。這樣,人文社會學科的各個學術領域,事實上都受到了 “四人幫”那一套研究儒法斗爭的理論和方法的影響。
儒法斗爭史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研究的破壞
“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儒法斗爭史研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是“四人幫”進行現實政治斗爭的工具。它對于文化學術的進步,不僅沒有產生任何的推動作用,相反,對中國傳文化、學術研究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作用。
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其核心和代表是以孔孟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兩千多年來,儒家文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價值觀、風俗禮儀,無不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毋庸置疑,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為維護西周的舊制度而產生的學說,有著保守、消極、落后甚至反動的一面,在封建時代,它曾長期充當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但是,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流傳兩千多年,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代表,除了它長期被封建統治階級當做統治工具,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提倡和推廣這一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不容否認的——這就是在儒家文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都能認可和接受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
這些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有一部分是正面的,積極的,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優良品德的形成,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產生了長久的促進作用。這一部分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繼承和發揚儒家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不僅對于中華民族的維系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對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強盛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儒法斗爭史的研究中,儒家成為了復辟、反動、落后、保守甚至賣國的代名詞,被作為法家的對立面而遭到全面、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儒家文化的這種消極、負面的形象,當時被強制灌輸到了幾乎是所有中國民眾的腦海中,從而使得儒家文化的傳承,出現了一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斷裂。

清華大學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
儒法斗爭史的研究,對中國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歷史學的研究造成了空前的破壞。這種破壞,一是把歷史篡改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歷史研究的極大混亂;二是把學術研究當做政治斗爭的工具,以實用主義代替實事求是,嚴重地敗壞了學風。這方面造成的破壞,在“四人幫”被粉碎后不久,就遭到了人們的口誅筆伐。
著名歷史學家黎澍在1977年第2期《歷史研究》發表的《“四人幫”對中國歷史學的大破壞》中,對“四人幫”開展儒法斗爭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及其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進行了深刻的揭露。這篇文章認為,在儒法斗爭史的研究中,“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把歷史學變成了搞篡黨奪權陰謀的工具。他們虛構歷史公式,拼湊出一個從古到今與儒家相對立的法家陣線,炮制大量所謂總結儒法斗爭歷史經驗的論文,只不過是希望披著學術的外衣,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樣做的結果,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盛行,實用主義代替了一切,對中國的歷史學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壞。
1977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扈世綱的《評“四人幫”的影射史學》一文,認為“四人幫”搞歷史就是為了影射,就是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政治目的。從這一目的出發,他們對歷史任意解釋,想怎么說就怎么說,顛之倒之,翻之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仿佛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為了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而存在。這種“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與古為今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根本對立的。
黎澍、扈世綱等人對“四人幫”的批判說明,“四人幫”對歷史學所造成的破壞不僅是空前嚴重的,而且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