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臥隨心——《短火》后記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寫小說了。到2008年,我忽然發(fā)了一下狠,重拾舊業(yè),又寫起來了。那時候還在工作崗位上,依然是很忙亂,依然是糾結,依然是心累,“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白天、晚上,都無法安靜。寫小說是件需要有整塊時間,又需要靜和心情的事情,不能將就和草率。我只有早晨那段時間,是安靜、干凈,而又整塊的。于是,早晨一到五點鐘就爬起來了。我靜靜地坐在書桌前,點上一支煙,開始寫作。一坐兩三個小時。久不寫作,稍有生澀,思路常受阻隔。有時能寫幾百個字,有時一個字也嘔不出。天天如此,竟有小半年堅持下來了。沒有耽誤工作,也沒有被累垮。
那部中篇小說《短火》就這樣寫出來了。我感到一種噴發(fā)的快樂。然后,接著寫了《中鋒定》、《輕輕一擦》、《縣長搭臺》……
我是在1991年停止寫小說的。那年的上半年我還在湖南省作協(xié)快樂地工作著,突然一道調(diào)令下來,不由分說,讓我到湖南文藝出版社任職。窩了三年。隨后又被拉到廣東花城出版社。在那里的時間真是太長了,一下窩了十六年。兩處相加,將近二十載,我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就揮霍在出版社那把掉了漆而人一坐上去就吱呀亂叫的硬板凳上了。我不可能還有時間和心情寫小說。“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這一對杠桿像兩把強力的彈簧,把社長全身的神經(jīng)繃緊。腦子里裝得滿滿的都是選題、圖書品種、發(fā)行量、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還得周旋承受各種矛盾和污垢。而間常會有的因內(nèi)容而生的檢討轟炸則讓人幾近瘋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落在洪水中的學生崽,稍懂水性卻并不會水,只好隨波逐流,載沉載浮,聽天由命,無暇他顧。我是個有點認命的人。我以為中國有句老話是非常好的:隨遇而安。
最近發(fā)表了幾篇小說后,一些朋友都為我惋惜,說:“老肖如果一直寫下來,完全不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我想了想,得出的結論是:那又能是什么樣子呢?如果我一直在作協(xié)待下去,一直寫,一碗水看到底,以我的資質(zhì),以我的思想,以我的閱歷,大約也不容易寫出多好的作品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什么事情都是很難說的。十幾年光陰,換回來最大的收獲是增加了閱歷,提升了對生活的感悟能力,讓我對社會人情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我在湖南省作協(xié)搞創(chuàng)作的時候,常常到下面采風,有時單獨去,有時組織去,走馬觀花,轉(zhuǎn)一圈回來,筆記本里也會記下好多事情(包括好多精彩的語言)。但那都是聽人家說的,跟自己關系不大,不巴皮不巴肉,不會有痛切之感。而且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事情的生成土壤、背景知之甚少,也就很難作出準確的價值判斷。三十歲時,去做過兩年掛職副縣長。有職務,也管事,但因為是掛職鍛煉,人家還是把我當作客人看待,很多深層次的東西,很多細微之處,并不知曉。我仍然算是半個看客。做了社長,情形就很不一樣了。好多事情需要操心,好多事情需要作主,好多矛盾都集中到了這個點上。好人得做,丑人也得做。什么事都得擔當。出版社是個有點特殊的行業(yè),除了自身的經(jīng)營和發(fā)展,還要跟很多作者打交道。任何一個社會層面,都可能會有(文學)作者。跟這些作者打得幾次交道,自然對他們的工作生活會有些了解。一個作者就是一個生活面。無數(shù)個生活面疊加起來,就是整個社會生活的總和。寫小說的人,需要對一個點深入透徹的了解,也要知曉社會面上的狀況,才有可能形成自己對社會對生活獨有的見解。一個作家,總是需要對社會對生活有獨到的發(fā)現(xiàn)和看法的。拿十九年的時間在一個點上滾打,生活逼著我對周圍的一泥一土一草一木都熟透了,讓我對世道人心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身體力行,趴在一個地方深入體察和道聽途說相比較,終究是大不一樣的。那種體驗,那種痛感,惟有自知。在這十九年中,每年要審讀大量的書稿,這讓我提高了識別作品優(yōu)劣和審美的能力。正是十九年的歷練,讓我改變了很多對生活、對文學的看法。有看法,卻沒有想法,我以為自己這輩子大約是再不會寫小說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最后還是憋不住,又寫起了小說。這讓我想起四十多年前下放到農(nóng)村時,我做得最多的兩樣農(nóng)活,一是打農(nóng)藥,一是出牛欄淤。出牛欄淤真是又苦又臟又難受。牛屎和稻草層積在一起,緊繃繃、厚達幾尺,一釘耙扎下去,一翻,一股漚氣竄出來,那氣勢好足,能把人嗆暈。其實,任何農(nóng)肥層積久了,都會發(fā)酵,都會嗆人。把農(nóng)肥和寫作連在一起作比喻,似乎有點沒來由,沒道理,不衛(wèi)生。真是一種褻瀆。但是,話雖難聽,道理相同,話歪理不歪。
而恰當其時,我榮幸地“退居”到了“二線”。未到退休年齡,卻可以享受退休的輕松了,我真是從內(nèi)心里感謝領導和這項政策的制定者,(雖然有人質(zhì)疑這項政策近人情,不盡人事,但我歡迎)。我有種梅雨天抖落爛蓑衣的感覺,松快無比,輕盈無比。我?guī)е轶w鱗傷又坐回到書桌前,面壁思過,整理心情,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半個月沒有下樓。我需要盡快把自己的心思安妥下來,找到那個屬于自己的精神時空。那是一個安寧、安詳、澄凈、澄明的時空。我心里反復想到的一句話是:終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寫小說了。這才是我的生活。
這本集子里的小說,都是我最近三、四年里寫出來的。除了《六狗》是個短篇,其余皆為中篇。
我的中篇,大多是兩萬字、三萬字,比短篇略長,比通常意義上的中篇要短。這并不是有意為之,只是因為作品中的人物較少,情節(jié)比較簡單,讓它們把作者的意圖表現(xiàn)出來,就完了,就可以結束了。這些作品,完全是遵從自己幾十年的生命體驗和生活感悟,有點匆促地寫出來的,再加上久不寫小說,難免手生,也就難免青澀,留下遺憾。
我的小說的背景大多是我的家鄉(xiāng)——湖南南部的那座山區(qū)縣城。家鄉(xiāng)對一個人,尤其是寫作者,往往有一種特殊的提神醒腦作用。“退居二線”以后,我立即回了兩趟家鄉(xiāng)。我得趕緊回去,把地氣接上。我在那些老街和陋巷上慢慢地走,一趟一趟地走,努力找回那種基調(diào)、氣息、氛圍,還有家鄉(xiāng)的語言特有的韻味。家鄉(xiāng)的一切對我都是新鮮而又熟悉的。我在那些已經(jīng)踩踏得光滑泛亮的石板街道上,找回了很多昔日的感覺,也捕捉到了一些小說創(chuàng)作的觸發(fā)點,但更重要的是,舒緩了身心,讓我覺得生活還是很美好,很值得留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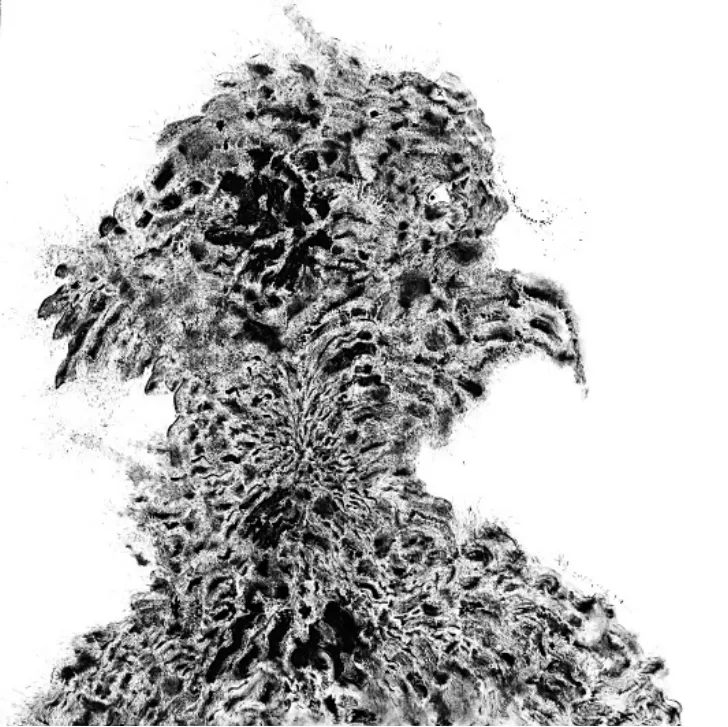
董重作品·肖像NO.1 布上油彩 80×80cm 2010
這批小說里頭的人物大多有原型。有的情節(jié)、細節(jié)、感受,是我自己親身經(jīng)歷過的。好些場景,在我家鄉(xiāng)的縣城里現(xiàn)在還能看到。《短火》是在1 9 9 8年就有了構思,且寫出開頭,卻是在十年以后才重新寫過的。《短火》發(fā)表以后,家鄉(xiāng)一些熟悉作品里頭主要人物潲桶仔的讀者,又給我講了好多這個人物后來的遭遇。《縣長搭臺》直接就是用的我在掛職副縣長時的一段經(jīng)歷。當然沒有照搬生活,里頭有加工,有增刪,有揉和,主要還是加進了現(xiàn)在的眼光,現(xiàn)在的角度,現(xiàn)在的意識。但主要情節(jié)和人物沒有改變。而《嗩吶有靈》則是上次回鄉(xiāng),在縣城正街上聽一位女子述說觸發(fā)的結果。我寫的這些人物,大都是真實的。我寫他們的生活,寫他們的喜怒哀樂,我只是想通過他們的生活,讓人們看到真實的人生。小說不是不需要虛構。相反地,虛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是才華的體現(xiàn)。但虛構總是要有所依托。我想能夠依托的就是社會中活生生的一個一個的人。有真實的人物原型作依托,在刻劃人物、表現(xiàn)人物,生發(fā)開去的時候,更能獲得我們通常喜歡說的“真實感”的效果。
我深深后悔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了,沒有早點拔身出來。這也是性格決定的。性格即命運,這話一點也不假。我現(xiàn)在才重新歸山,似晚了點。我也許還能寫十年,寫二十年,或許更長,但總還是不夠,心里難免有種緊迫感。“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用得很多的毛澤東的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不爭了,我不想太勉強自己。時間還有一大把,還很悠長。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停筆的時候,文學還很熱鬧,很喧囂,二十年過去,文學已經(jīng)很平靜,歸于邊緣化了。平靜,這才是正常的。熱鬧其實很噪人。我的性格,我現(xiàn)在的心態(tài),都很適宜這種平靜的氛圍,它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我不會急著寫(雖然心里好多東西蹦著跳著要表現(xiàn)出來,越這樣,越不能急),我還想“歇”一“歇”,把這大半輩子的經(jīng)歷理一理。把以前那些事情都推遠,再推遠。我現(xiàn)在有時間了,可以慢慢思考,一點一點地沉淀。我倒是有好多書要抓緊讀,前一陣子耽誤了,需要惡補一下。我還想在寫作上有所變化。這就需要不斷地反省自己,補充自己。我明白,到了這種年紀,多寫一篇,少寫一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最想寫的東西,用最合適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我很慶幸,現(xiàn)在有時間了,可以從容地、心無旁騖地去做這些事情,可以從容地寫。坐臥隨心,忙閑皆可。在從容的寫作中享受那份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