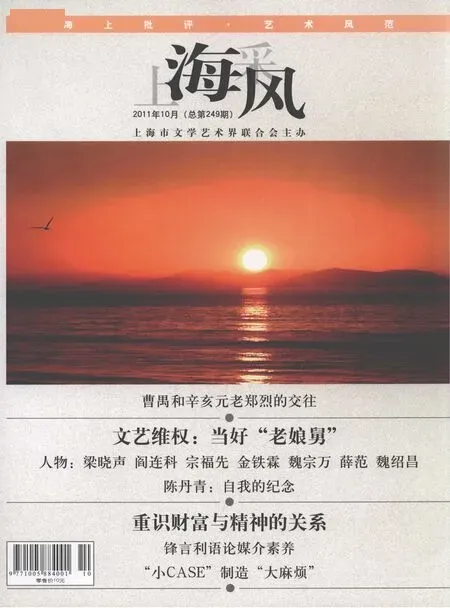《媽媽咪呀!》讓中國人來講會如何
文/影 子
當蘇菲和重逢的女友們尖叫著擁抱蹦跳,當唐娜和重逢的女友們尖叫著擁抱蹦跳,那個時刻我想,全世界的每個女人都會笑起來。因為我們中的每一個都曾那樣尖叫擁抱蹦跳著重逢,在歲月的背面再次重逢。
唐娜女士是希臘某個小島上度假客棧的小老板,她有個不安分不尋常的過去——七十年代的嬉皮,反潮流反主流的嬉皮。二十一年前,唐娜分別與三個年輕人,在小島夏夜的星空下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的結果是小蘇菲不期而至的降生。而小蘇菲在即將與心上人踏上紅地毯的時候非常渴望由她從來不知道從來沒見過的那個父親親手把她交到新郎手里,于是小東西偵察窺探到了母親當年的“星空級秘密”,于是以媽媽的名義斗膽給山姆、比爾、哈瑞三個“老爸嫌疑人”發出請柬,于是三個中年男感慨萬千地、不約而同地、惴惴不安地向著小島進發了!
本人有個男性朋友,年紀不大,閱女不少。公開的女朋友就不下十個。我過去常常恐嚇他,等你結婚那天,前女友們正好抱著孩子開一桌,團團圓圓老酒吃吃倒也是和諧美景圖一幅。這個唐娜跟他很有一拼,不過比他更牛,睡了三個男人生了一個閨女,自己也搞不清孩子他爹是誰。《媽媽咪呀!》的劇情是典型百老匯風格——狂歡化的大團圓結局所遮蔽的,正是歐洲“搖滾一代”年少輕狂放蕩不羈而給自己、給孩子帶來的難以啟齒的傷害——荒誕又滿含著悲哀。
唐娜出場的時候,身著帆布工裝褲,拿著電鉆正準備給自己那個狀況不斷的小客棧干些釘釘子抹膩子之類的粗活兒。雖然現如今,到山上島上水邊林邊當一個哪怕是農家樂的老板也是相當一部分城市賤民的理想,可唐娜說,這營生可不好干,想來那個叫蘇菲亞的姨姥姥只為唐娜付了客棧的首付款,她必須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交銀行“按揭”——讓銀行按倒了揭皮。所以,略顯焦頭爛額的唐娜姐姐甫一出場就高歌一曲“money money”,控訴金錢給她造成的壓力,恨自己不是個有錢人可以翹著蘭花指周游世界。盡管后來她幾乎是本能地當場拒絕了金融才俊“甩頭黨”哈瑞的支票,作為“唐娜”,我可以告訴諸位,支票上的數字是二十萬英鎊,天文數字,可辦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
整出戲里,唐娜換了好幾身衣服,但我自己覺得最性感最牛的就是這身披掛著斧鉞鉤叉刀槍劍戟帶尖兒的帶刃兒的帶刺兒的各種工具的行頭——一個女人的牛逼不在于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或許多個男人心甘情愿俯下身蹲在地上給你系鞋帶、每天在你耳邊至少說一遍“我愛你”,而是當這一切突然失去,你還能hold住自己的生活,hold住自己的人生。唐娜就是這樣一位“hold住姐”。作為一個離經叛道被母親逐出家門的單身母親,作為一個前“搖滾女王”的她獨自養大了自己的閨女,母女倆還照顧另一個連侄子都不搭理她的老太太(這個未予正面表現,走的是“暗場”),勉力經營自己的小生意。
吃得咸魚抵得渴,好漢做事好漢當,唐娜——包括當年 “動力三人組”里另兩位寶里寶氣的姐們兒、包括那三個后來爭當“三分之一爸爸”的男人,都是些這等樣的人物。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們人到中年的狀態,那就是:她們和他們都沒有背叛自己的青春。在年少的時候脫軌張揚,此后選擇又各有不同,但面對昔日的“荒唐”,他們沒有拉下臉假裝自己光榮正確,他們敢面對敢承擔,絕不裝字母。僅僅是這樣的一種氣度和態度,已經足以令小鼻子小眼的世間俗人們瞠目了。
當然,唐娜也有hold不住的時候,當她為女兒梳頭,幫女兒試穿婚紗——作為曾經那樣度過自己青春的唐娜對婚姻總是懷有深刻懷疑的,所以,她會一語雙關地對女兒說:“準備好了?你跳進去吧”——她回想孩子背著書包和她說再見的過去種種,轉眼之間姑娘已經長大,她感慨的不是育子的艱辛而是生命之成熟如此猝不及防。《媽媽咪呀》整出戲都歡快雀躍簡捷爽利,唯此時讓人淚下,無論放到哪一種文化語鏡中,這個女人都有太多不足與外人道的艱辛。
當送親的隊伍向教堂走去,她和昔日落跑的心上人山姆總算有了短暫獨處的機會,她唱了那首著名的“勝者為王”,贏家拿走了一切,而敗者卻只能獨自舔傷口默默愈合。在宿命面前,唐娜多多少少是有一點點的哀怨的,但往往就是如此吧,有大把理由抱怨命運不公的人,渡過生命激流險灘之后,雖然偶爾傷懷,卻往往比那些一路順遂的人更能保持對生活愛的能力,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永遠是Dancing Queen。
乘著音樂劇的東風,可以再去看一遍梅麗爾·斯特里普主演的同名電影,電影里兩人對話的這一段因為兩位戲骨的提煉升華顯得尤為動人。她訴說了自己的失望和自己的委屈,但旋即便如一陣紅色的旋風一樣跑上山頂的小教堂——這個當媽又當爹的女人決定要親手把女兒交給新郎。
說實在的,《媽媽咪呀》的故事并不特別奇異,尤其是當它被綴上那樣一個大團圓的結尾,簡直都有點好萊塢式的“俗”了:皆大歡喜,絕不讓一人向隅。但所謂的“俗”其實是對于歐亞大陸那頭兒以及大洋彼岸的“他們”而言,對于“我們”來說,試著把這故事“中國化”,便無疑就會在內心同時輕微上演著一場心理交戰。
這故事是可以有一百種講法的,但《媽媽咪呀!》的講法最光明最舒展最不陰暗最不齷齪。這個故事如果讓中國人來講會如何?我的另一個朋友說:“這題材給國人做,以當下,不是皇阿瑪和夏雨荷的孽緣,就是后現代的《雷雨》。總之,把歡樂、樂天全部砍掉,情殺悲苦黑道官家青樓私奔一勺燴……”
先不提那些沒出息的編劇家,請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把這種事情當新聞奇聞在微博上“爆料”,情況會怎樣?回想一下興致勃勃圍觀這個人的艷照那個人的視頻時群情振奮群情激憤的猥瑣眾生,哦,你完全可以推測出“跟帖”大致會是些什么內容。想一下都讓人喪氣啊。
還記得《美國派》嗎?面對那些半大小子決意“破處”的種種探索與冒險,他們是持一種多么松弛玩樂戲謔乃至于欣賞的態度啊,無半點貶低,更不要說譴責了。青春沖動來自天然,愛更是天賦人權,對,就是這么的簡單。
還記得《畢業生》嗎?這故事如果發生在我們這里,達斯汀·霍夫曼就是周萍啊,就算是二十啷當歲的曹禺也會讓這個犯了亂倫大罪的孽種去死啊。可是,在“他們”那里,年輕人的錯再荒唐都可以原諒,我們被帶到“他們”的那種邏輯那種氣場中,也只滿心希望手持大棍的霍夫曼橫掃眾人,趕快甩脫老妖婆,和心上人勝利大逃亡。
什么時候,我們面對感情面對別人非主流的人生選擇能這樣坦然、自然,甚至保持一種欣賞的態度呢?至少別少見多怪或視若無睹呢?
即使是已經演過了一百遍《媽媽咪呀!》的我,即使是每天在舞臺上要作為“唐娜”活夠大汗淋漓、涕淚交流的兩小時二十分,當hold住姐攜老姐倆在紫色和亮粉色交替的絢麗交束下,穿著閃亮的貓王服,踩著銀色松糕鞋,拉起彼此的手邊舞邊唱,無拘無束,氣宇軒昂,一到此時,我依然會在故事的結尾處每每大嘆:“我們”和“他們”,竟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