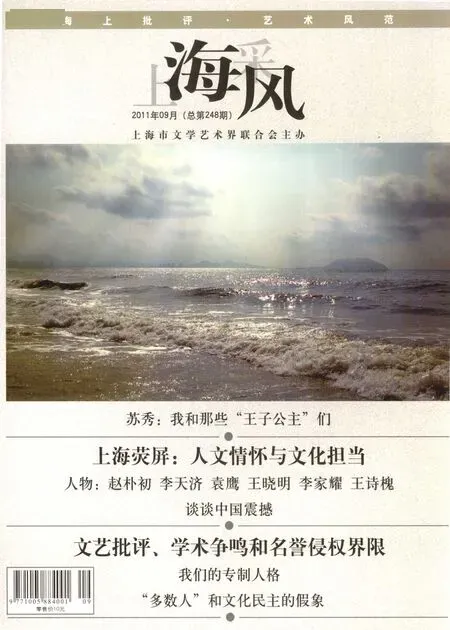王詩槐:做有生命力的“綠葉”
文/胡凌虹

5年前在莘松路的一家咖啡館內曾采訪過王詩槐,那時的他剛演完《茶馬古道》,侃侃而談劇中拉薩巨商尼瑪次仁的角色,并稱“是從事影視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過程”,然而如今,對這個角色他已經不甚滿意,開始神采飛揚地談論起《開天辟地》中個性鮮明、充滿著爆發式激情的陳獨秀、《刑警博客》中縱跨黑白兩道的商界巨頭苗天恒,談到興致處,特地從手機中翻出劇照給筆者看。訪談中,王詩槐很少談及過去的輝煌,無論是電影《漂泊奇遇》《張衡》《日出》《詐騙犯》,電視劇《華羅庚》《在水一方》《幾度夕陽紅》《杜月笙》等中那些讓人過目難忘的經典形象,還是“大陸秦漢”、“上影當家小生”的美譽,他都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這么多年的演戲,真正拿得出手的戲沒幾個。”王詩槐認真地說道,不禁讓人感嘆其自我要求之高。現今,大部分與他同輩的同行已經退隱江湖,而王詩槐依然活躍在熒屏上,不懈地追逐著他的影視夢,他說,“即便是做綠葉,也要做有生命力的綠葉”。只是這份堅守中不乏幾分落寞與諸多無奈,同時,也飽含著對上海影視的深切期望。
懷念過去的嚴謹創作作風
現已50多歲的王詩槐,依然儒雅瀟灑,只是多了幾分歲月的滄桑。若在好萊塢,這個年齡正當是演戲的花樣年華。“演員是靠積淀的,閱歷越豐富對角色的把控能力就越強,所以在好萊塢,五六十歲的年齡正是演戲的黃金年齡。他們會把一個演員用到極致,到不同年齡段為他寫不同的戲。”王詩槐帶著羨慕的口吻說道。然而,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影視演員哪怕演技再爐火純青,只要青春不再,就少有用武之地。“現在國內影視市場大部分以年輕為主,打開電視,10部有9部半電視劇的男女主角都是年輕人,所以我們自然就退居二線,即便在《刑警博客》中我的戲甚至比男主角的分量還要重、還要有戲,但位置還是綠葉。”王詩槐嘆了口氣,轉而又樂觀地說道:“不過這個綠葉還是很有生命力的。所以我想說盡管是當綠葉,在盡可能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做一些有生命力的綠葉。”
記者:從“上影當家小生”到現在的“綠葉”,會不會有心理落差?
王詩槐:這個過程是經常有的,關鍵在于自己怎么調整吧。我年輕時演主角時,沒拿什么錢,但是今天不少演員拍了一部戲就火了,片酬多出我好多倍,而且還演得不怎樣,心里肯定很不平衡。那我只能想,這就是他的命唄,只怪我們當初沒有趕上今天這個時代。再比如作為演員都想演主角,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年齡段在戲中擔任主角的極少,即便有,比如李幼斌,他飾演的這類角色,導演可能不會想到我。我也可能會想,為什么他還在演主角,我怎么不行。那我只好這樣想,你沒這個命,或許哪天知識分子類的戲多了,對你路子的戲多了,你就演主角了。只能這樣自我調節了,要不然太沒意思了。
記者:你是否有生不逢時之感?

《開天辟地》中王詩槐飾演陳獨秀
王詩槐:那倒沒有,其實我更加留戀過去我在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戲時整個劇組的嚴謹的創作作風。過去拍電影,長的話,可能將近一年,現在有幾個老板肯花那么長時間?而且我覺得現在的演員應該多回歸舞臺,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演員演來演去一個樣,這不叫演員。不同風格不同類型的戲,表演方式是不一樣的,古裝戲不能用現代的表演方式去演,演出來不像古人,現代戲不能按古裝戲去演,演出來不生活了。現在的一些影視拍攝中,很多演員更像是道具,包括《建黨偉業》,那么多明星在那里,他們有多少戲呢?更像是一些符號,不太可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創作的快感。可惜,我們過去那個年代一去不復返了,因為不符合市場的需要。
記者:你從藝20多年來,在熒屏上塑造過各式各樣的藝術形象,大元帥、理發師、科學家、工人、校長、土匪……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你接下來希望演些什么樣的角色?
王詩槐:我想演的角色很多,只要有機會,什么角色都愿意去嘗試,不去嘗試都是未知數,我覺得自己應該能勝任很多角色,這方面我還是蠻自信的,比如農民,也可以。不過,我最喜歡飾演智慧型的成熟男人,一個好的人物肯定是很有智慧的,一定是編劇下了功夫的角色,很飽滿,有演頭,過癮。很多時候,觀眾不愿意破壞演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會想你怎么演這種角色。但演員站在自己事業的角度,和觀眾的視角不一樣。有網上的觀眾說,看了王詩槐的戲,怎么感覺沒有共同點,這句話看起來好像有些意見,但是我很高興,實際上也說明了我創作的角色很不雷同,我覺得很好,這就是我追求的東西。
一味“坐等”就意味著被淘汰
雖然在上戲時,王詩槐就樹立了“千面人”的志向,也希望能多演一些喜歡的好角色,但是要實現這個愿望顯然不易。“一直說我要選好的角色,但是很難,演員是很被動的,更多的是等待。”王詩槐的聲音變得有些低沉。如今成為“綠葉”的他為了能繼續在影視圈獲得更多角色的機會,不得不學會忍受。“到了我們這個年齡段,完全坐等,沒有特別滿意的角色我就不拍——這不現實,如今這個市場很殘酷,你丟掉一年、兩年,要想再進入,就很難了,很快大家就把你淡忘了。”
記者:以往上影明星群可謂星光璀璨,但是現今卻有些星光暗淡,老一輩藝術家或故去或身體欠安,而上影廠的中老年實力演員,除了你還在熒屏上頻頻露面,大部分都早早退隱,不禁讓人惋惜。
王詩槐:有人說我們集團有些人不愿意出去,整天呆在上海很滿足。其實是沒辦法,因為這個圈子里的人一旦擱了兩年不去拍戲,就不敢去拍了,機會來了,也不敢去。
記者:都是老戲骨,怎么會不敢呢?
王詩槐:現在的工作狀態跟過去比,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后,港臺影視界的人涌入了大陸,沖擊著大陸影視劇市場。今天的市場,不會給你精細打磨的時間、空間。不少攝制組,本子都不是很完整,甚至在開拍的時候,臺詞現編現改。很多攝制組會集中在兩三天時間內把你三十集的戲拍完,對投資方而言這樣省錢,但對演員而言,沒有與新團隊的磨合期,沒有準備時間,進組就得迅速進入人物狀態,很難很難。再加上現在各個攝制組的工作方式不一,這對演員是很大考驗。老實說,如果隔了很長時間不去做這種嘗試,我也會膽怯。
記者:這樣的工作模式有很多不規范的、不符合創作規律的地方,你不認同卻不得不去適應、忍受,心里會不會感到難受?
王詩槐:會,會,會感到難受,但是沒辦法,現狀就是這樣,逼著你要與時俱進,去鍛煉你的適應力。如果我在家等劇本,不去接觸我們圈里的人,或者休息個一兩年,過后馬上就會手忙腳亂。而演員這個職業恰恰需要一個良好的心態,一定要很自信,你的心態不好你怎么演戲啊,你會發虛。所以平常不斷磨練,經常接觸不同的創作氛圍,可能會練就一點應對的本領,但是這是非常傷神的,需要充足的精力、體力。所以我提出來,在劇組每天只工作12個小時,不希望身體被弄垮。
記者:有沒有實在氣不過,不想干的時候?
王詩槐:有,常常會有這樣的時刻,一旦碰到有攝制組很不規范地拍戲,會很生氣,覺得很煎熬,沒有藝術可言,想著自己這部戲拍完了就不拍算了。很多時候我都是充滿了創作激情進入劇組,結果往往是失望而歸。很多組是趕緊拍完糊弄完了之后,播出,拿錢走人,很難遇到一個讓你覺得可以全身心投入進去的組。所幸我今年碰到的《刑警博客》很不錯,可以算是我十年來碰到的最好的一個組,其中的角色我也很喜歡,所以即便辛苦點累點,我也拍得很高興,工作12個小時后,我會愿意再送他們2個小時,大家都為了創作,并沒有浪費時間,我覺得很難得。之前90%多的組,我都是喊“時間要到了啊”( 敲敲桌子,不耐煩的口氣)。作為演員就是希望碰到這樣的戲,這樣的劇組,但是碰到的機遇很少,演員確實很被動,你碰到了一個好角色,未必能碰上一個好班子。我在看本子的時候,看不到這個組,導演、合作者怎樣,答應接某個戲有點像打賭一樣。我希望爭取每年能夠接上自己真正喜歡的戲,哪怕拿的錢很少,在我退休之前,要保晚節,真的去選擇一些好的角色。

《茶馬古道》劇照
記者:打算拍到什么時候退休呢?
王詩槐:我的想法一直不穩定,我跟很多人說一直拍到60歲,但是有時演員并不是能完全自主的,碰到好的角色、劇本,還是愿意去拍的。如果我在60歲之前每年能演幾個好角色,就可能把這個界限往后推。
記者:一直讓你堅持下來的動力是什么?
王詩槐:畢竟我是學這個專業的,從骨子里,還是覺得創作的樂趣是無止盡的,盡管碰到這個樂趣的機會越來越少,但是還是不死心,像釣魚一樣,老是有盼頭。第二,也是生活所迫,我得養家糊口啊,但是除了拍戲掙錢養家,其他我干不了。
記者:養家糊口應該沒問題吧?
王詩槐:盡管我是國家一級演員,是特殊津貼獲得者,但我現在拿的是上海市最低生活標準的工資,1200來塊錢,這是因為我們事業改制了,除了辦公室人員,全廠創作人員大都是這樣,到了退休年齡才能拿到我的檔案工資。你說1000多塊錢我能夠養家糊口嗎?現在物價是一天一個樣,這是很殘酷、很現實的問題。
上海演員“物美價廉”很可悲
王詩槐是安徽人,1977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自此開始了與上海的一段深厚情緣,在王詩槐的履歷表里,80%的作品都是上影的片子,之前有不少機會去北京,他從不曾想到離開。可是,這個讓王詩槐一直割舍不了的上海,昔日作為影視重鎮實現了他的影視夢的上海,到了更為繁華的今天,卻開始讓他面臨四處奔波拍戲的無奈。“現在上海的戲少,多半需要在外地拍,所以事業和家庭是一個一直難以平衡的問題。今年算是比較幸運的,碰上了三個戲《開天辟地》《心術》《新兒女情長》,都在上海拍,所以可以多一些時間來陪家人。”只是這份幸運等待了很多年,而今后如何無法預測。
記者:最近在熱播的《開天辟地》里,你演的陳獨秀很精彩,這個形象也是影視作品中少有的表現得比較完整的陳獨秀形象,也得到了專家、觀眾的一致認可。不過據說剛開始接這個戲時,你還有些猶豫,是什么讓你決定演這個人物的?
王詩槐:起初是有些猶豫,對演這個角色我心中沒數,尤其對陳獨秀這樣舉足輕重的而且有爭議的人物,我感覺如果功課不做好,是要出洋相的,我要為他負責任的。后來決定接這個戲的很大一個原因是,我了解到《開天辟地》和上海有著緊密的聯系,是上影集團出品,上海上影英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制作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很重視,而且這個戲里上影廠演員就我一個人,我再不參加,上海作品里上海演員就寥寥無幾了,太可悲了。
記者:現在很普遍的一個現象是,上海的戲大都不是上海演員演的。
王詩槐:可能用投資者的眼光看,上海演員沒有賣點。今天這個社會跟過去不一樣,很多名氣是靠炒作、作秀獲得的,但是上海的演員好像犯同樣的“毛病”:都特別的低調,一到宣傳場合就縮到邊上。上海演員也比較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進入攝制組,很看不慣攝制組不成文的規定:演員請大家吃冰棍、買水、晚上出去吃喝玩等等,上海演員不太能融入進去,更愿意一進組就呆在自己房間,干好自己的事。說句好聽的話,就是比較清高,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沒出息,因為這個行業的現狀就是這樣的。我知道如果我也隨大流,可能完全改變現狀,但我做不到不斷推銷自己,我覺得挖空心思地炒作自己,不是藝術家的所為。現在我還是蠻自豪的,我在圈里口碑一直不錯,規規矩矩演戲,老老實實做人。我這個人就喜歡說實話,最多你不找我拍戲,但是我不說違心的話。
記者:在你看來,現在上海的表演人才是真的斷檔了,還是挖掘不夠?
王詩槐:還是挖掘不夠。制片方不要還沒挖就覺得不行,這樣就會出現惡性循環,現在上海年輕演員大都是科班出身,需要的是經驗,可能沒有多大名氣,但是一旦遇到好戲,兩三部戲就出來,但是這種機會很少。
記者:在你看來,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王詩槐:這座城市如果沒有文化作品,永遠別想打這個翻身仗。過去上影的輝煌就說明這個問題,因為上影有無數部好片子,才造就了無數明星、藝術家。如果我們把這個陣地弄丟了,會帶來一連串的文化問題,包括上海的藝術工作者,自信給扼殺了,然后地位也就消失了,這個“地位”指很多,包括在這個圈里的地位,演員的經濟地位等。現在圈里很多人會說上海演員很敬業,很認真,也很便宜,可謂“物美價廉”。聽到這樣的對上海演員的評價,我很難受。人家說,一分價錢一分貨,便宜沒好貨。敬業又能演戲,為何價格上不去?所以說只有上海有了戲,自己當主人,才能說我主角要用上海的演員。上海的城市建設是飛快的,硬件的東西是一流的,但是文化要跟上。過去我在市政協做政協委員的時候,也提過這個提案,希望能多給上海文藝工作者機會,而機會要靠得到領導的重視,領導要給他們創造條件和機會。我覺得上海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把平臺鋪好,上海不是沒有人,是人才濟濟,要更多地給他們機會。
記者:這兩年一些地方電視臺興起了一種自制劇,不斷地推出新人。
王詩槐:湖南、江蘇、安徽他們都在走這個路,這樣不愁資金,不愁播出平臺,不愁我這個戲賣不出去,可以大膽啟用新人,這個路子將來走通了之后,會對很多制作公司產生影響。現在很多電影上海投資,只是參股,沒有發言權,還有市場壓力。上海可以借鑒自制劇這條路。現在上海的城市發展日新月異,我們希望文化也是這樣就好了……